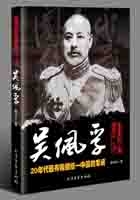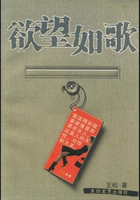一
我刚到鲁乡,参加的第一个党委会,书记和乡长为了砍树的事儿竟干了起来。
党委会,严格地说,叫党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是乡党委委员和副乡长以上的干部,因为副乡长都不是党委委员。主持会议的自然是乡党委书记。鲁乡的党委书记叫钱顺,人们偷偷地叫他大舌头。大舌头肚子滚圆,一米七五,四方脸,高鼻梁,体重起码在一百八十斤以上,看面孔,五十有余,听说年龄才四十出头,说话略带口吃。这次党委扩大会的议题是要砍掉杨村和柳村之间那五百多亩大片林。这五百多亩大片林是十几年前全乡的劳力栽下的。钱顺要把它砍掉,他说有一家投资商选准了那块地。在向县林业局呈报之前开个党委会,目的是统一大家的思想。钱顺把目的、意义、远景规划讲了又讲,多数党委成员是附和的。谁知乡长石敢竟提出了不同意见。石敢,三十七八岁年纪,脸上平滑的线条描绘出十分清晰的轮廓,那两撇细细的胡子显得他非常精干,他言语不多,但眨眼的频率好像比别人快一点。因此,钱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圪眨眼。圪眨眼讲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投资商不可能一下就占那么大一块地,再说,是真投资还是假投资,现在好像并不清楚;
第二点,这块土地的权属是杨村和柳村的,乡里把这块土地拿回来,这两个村的群众工作不一定好做,且这两个村的权属还存在纠纷;
第三点,现在是柱材,有点可惜,若再过五六年,它不就是檩材了吗?
钱顺听了这话,突然冒出一句:
“再过五、五六年,你当了书记再打?”他那舌头显得很大很大。
石敢一眨眼,也给了一句:
“我是那意思吗?”
钱顺自然不会示弱:
“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
石敢再眨眨眼,慢悠悠地说:
“党委会上,不允许乡长讲自己的意见?”
钱顺怒斥道:
“别忘了,你是党……党委副……副书记,你就不……不支持我的……工作!”
党委其他人一看不对劲了,立即劝架。
钱顺当机立断,就这一问题进行举手表决。请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先举手,自己首先举起了手,举得老高老高。之后,恶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
有的迅速,有的迟缓,举手者显然已经过了半数。钱顺的目光好像逼到了我的脸上。我认为石乡长的话也不无道理,便说:
“钱书记,我是挂职的,又刚来,不算数吧。”
钱顺没有回答我的话。
最后,石敢举起了手,他那只手分明是在微微颤抖。
很快,县林业局来了两个人,实地查看那五百多亩大片林。那天石敢在乡,但拒绝陪客,骑着摩托独自走了。有钱顺在,啥都有了。酒足饭饱之后,三缺一。钱顺打发公务员张亚来叫我,我也拒绝了。我对麻将略知一二,更要紧的是,我身上一共才三百三十二元钱,鲁乡又没我的工资,输掉之后,我连回家的路费也没了。谁知,钱顺亲自来了,硬把我拉到麻将桌上。一圈下来算账,钱顺输了一百六,我输了二百五,那两位都赢。钱顺首先掏出了钱,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过了账。钱顺看我为难,顺手给我扔过五张百元大钞。我真想拒绝,但又不好拒绝。再说,我那二百五就这么白给了他,实在也气不过。那两位见赢了钱,又加了牛。第二圈下来,我身上的钱仅剩下两块了,我借钱顺那五百块只剩下了三百。到此结束吧,说什么我也不耍了。便把三百元还了钱顺,并许诺欠下二百,过几天还上,扭身离开了麻将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实在是无法控制……
这不大的一会儿,五百块钱就没了,窝囊!吃一堑长一智吧。我在心里发誓:以后再打麻将,我便是猪便是狗,便是连猪狗都不如的东西!这五百块钱实在是心疼。我刚考完大学,父亲便病倒了,那时家里仅有五百块钱,父亲要供我上学,连一颗去痛片都舍不得买,当时医生诊断为胆囊炎,疼起来父亲满炕滚,大滴大滴地流眼泪,但决不哼一声……那五百块钱,母亲为我缝衣服,买铺盖用去了二百多,剩下的钱全部给了我,我临走,只给父亲买了一瓶去痛片……
大一,我回家过春节,我在省城给母亲扯了点布,要她老人家做身衣裳,那才花了三十来块钱,竟被母亲数说一夜,嫌我花了不该花的钱,还硬要我把布退掉……
为使自己不再成为猪,不再成为狗,不再成为连猪狗都不如的东西,我要向母亲发誓。因此,便要给母亲写一封信,信纸一铺开,刚刚写了妈妈两个字,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这时,钱顺跑进来了,一推门便是哈哈大笑,我急忙擦泪。钱顺见我不禁一愣:
“小刘,你这是咋啦,哭啥呀?”
“没有呀。”幸好,我办公桌上放了本小说便搪塞道,“我感情比较脆弱,这本小说主人公的遭遇使我伤心,每逢看到这些,我都要哭的。”
钱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我当输了点钱,输哭了。”
“哪能呢。”我强打起了精神。
钱顺嘻嘻哈哈地说:
“你刚从学校出来,慢慢锻炼吧。什么也得学会,尤其是打麻将,有个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今天特别感谢你,今天要不是你,那事儿可就黄了。”
这是我到鲁乡后,钱顺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接着,钱顺给我扔下三百块钱并说那两百也不要了。我能输人家乡党委书记的钱吗?简直是开玩笑。钱顺见我硬是不要,便说今天是乡政府做东。
这个谜我没有解开,但又想解开,便悄悄地向石敢请教。石敢笑着说:“书呆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接着给了我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那五百多亩大片林,乡政府给林业局打的报告是小老树,面积是五十亩。下来落实小老树砍伐面积的官儿们能不敲它一杠子?
原来这一杠子还是我帮他们敲的。
至于输的钱,石敢告诉我,他已经给签字处理了五千多。可那天无论如何也没有输那么多呀。石敢说那是良心钱,钱书记说多少就是多少。我问那怎么处理了,石敢说:“钱书记请林业局的人,我只好签字就是了。”石敢说完之后显然后悔了,几次叮咛,不敢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他娘的,我还给他贴进三十块钱哩!
二
在我参加鲁乡的第二个党委会议上,钱顺通报,那五百亩大片林已经批复了。
钱顺在党委会上宣布,党委委员、副乡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去杨村或柳村分十棵树,白给。究竟谁去杨村谁去柳村,为了方便起见,会上把党委委员、副乡长以上的干部都分到了村。钱顺非常大气,专门点到了我,并把我定在了柳村。但我不知怎么去分树,何况我不可能把树拉回老家去呀。
一个漆黑的夜里,柳村的支书酒气汹汹地跑到我的宿舍,硬要给我五百块钱,我拒绝接收。这位支书反复申辩说他没有喝醉,并说不要嫌少,这五百块钱是正份,是我应得、应分、应有、应拿的。这大概是乡里给我那十棵树钱吧。我便向这位支书打听,柳村一共卖了多少钱。
这位支书似醉非醉,这会儿的头脑似乎还挺清醒:
“给我们村留了不到二百亩,还能卖多少钱,四五万块。”
我立即说:“趁有钱了,把你们那学校拾掇拾掇,孩子们上学实在是寒心。”
“嗯,对,对,对!”这位支书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话。谁知他紧接着来了一句:“可惜呀,没钱了!”
“刚刚卖了咋就没了?”
“打饥荒了!”
“什么饥荒?”
“还能有什么饥荒,肉钱、烟钱、酒钱、豆腐钱。刚刚又输了五千!”
“啊,你把卖树的钱输了?这还了得,那得给人家补上呀,快把你那五百块钱拿去!”
“刘书记,补不上来了,钱都输给了大舌头。”
……
我语塞了。
送走了这位支书,也送走了那五百块钱,我敲开了石敢的门。闲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才问石敢,杨村和柳村那树乡里卖了多少钱。
石敢说:“你操这心干什么?树是钱书记卖的,我也不敢过问。谁知道,卖多少算多少吧。钱书记这个人很有心机。”
“他有屁的个心机?”我反驳道,“鲁乡的书记应该你当!”“这话可不敢说。钱书记是很有心机,我佩服。”
这简直是鬼话,我根本不信:“你佩服他?”
“真佩服。”石敢眨眼的频率显然加快了,回答得十分肯定。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如果说钱顺佩服石敢还差不多。
石敢看我如坠雾里烟云,便道:
“就拿这次卖树来说吧,决定卖树那是党委会集体研究的,有了责任集体负。树咋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为了避免矛盾和群众告状,杨村、柳村每户给了一棵树,副乡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得了十棵树。每个支部书记分了两棵树,这两棵树可把支书们分苦了,领着人刨树根去吧。挑菜老婆蛇咬X,蛋疼不能说了。”
“你是乡长,这事儿就不能和上级反映反映吗?”
石敢那双眼睛睁大了,几句话浇灭了我的怒火……
三
我已经记不住,这是我在鲁乡参加的第几个党委会了。
这次党委会的核心内容是为钱顺提拔的事儿召开的。地委组织部很快就要来考察钱顺了。考察的目的很清楚:提拔。为了开好这次党委会,县委专门派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一位副部长列席会议。会议决定,由我给钱顺写述职报告。到这时,我才知道,钱顺原来是个木匠,在县修建队当过包工头、副队长、队长,来鲁乡之前,在县工程公司当经理。
钱顺在写作方面可以说一窍不通,不得不把石敢叫来。我们三个人关住门研究了两天。我不多说话,只作为一个记录员,整个报告的思路、素材基本上是石敢敲定的。这几天,炊事员魏柱给我们单开小灶并且送饭,这显然是钱顺的旨意。
初稿出来之后,钱顺听了一遍把我说成了一朵花,说我是天底下第一流的笔杆子,放到鲁乡实在是埋没人才。
我把这话告诉石敢之后,石敢说:
“钱书记满意就行了,稿子就那么定吧。”
“他满意了,可我非常不满意!”我太憋气了,没有的写成有的,没做的写成做啦,石敢做的好事都放到了钱顺的头上,连我的成绩也归到了钱顺的名下……
杨村和柳村被砍掉的那五百多亩树地,钱顺贷款盖了几间房,房子并没有完工,很大一笔贷款变成了麻雀的乐园。今年,我取得了石敢的支持引进了花生品种。这么大的事儿,我自然不能不向钱书记请示。第一次去请示,钱顺在他的办公室正和一个女人不知在干什么,我红着脸出来了。第二次去请示,钱顺正在麻将桌上碰“发”字,根本听不进去……当花生成熟后,大舌头几乎乐疯了。花生收获后,大舌头将五万多斤花生趸卖了,据说卖花生的钱还没有要回来。我不敢向钱顺过问卖花生的收入,但我问过石敢。石敢说:
“钱书记需要钱嘛,这钱可派上大用场了,钱书记的钱有用。”
现在,这五百多亩花生,竟成了鲁乡改革开放、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杰作了。谁听了或看了钱顺的述职报告,谁都会说:这么好的乡党委书记不提拔,还等什么?
石敢听了我的牢骚,眨动着那双眼睛,极其认真地说:
“成绩都是书记领导的嘛,失误才是乡长执行的。这些事儿,可不能叫考察组的人知道。不过,钱书记已经把工作做好了。”
考察组的人他哪里会知道这些。
钱顺在大庭广众之下,念那篇述职报告之时,虽然有些口吃,可脸不变色心不跳。
他那内心深处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四
钱顺很快就要离开鲁乡了,也许是县委常委,也许是副县长。离开前怎么也还应再开一次党委会吧。可谁知,这次党委会钱顺竟缺席了。主持会议的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石敢。石敢说:
“你们不少人劝我跑跑书记,也希望我在鲁乡当书记,我感谢大家。跑书记对我来说,那是骑自行车上月亮——没路,我当书记那是墙上挂帘子——没门。鲁乡的党委书记人选已经有了,是靳乡的乡长。今天的党委会主要是告诉大家,请把你们个人手里的外债梳理一下,然后统一汇总到一起,让钱书记签字后交给新的党委书记,乡长在这其中要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大家伙儿便围绕会议的内容纷纷汇报。到这时我才知道:为了批杨村和柳村的大片林,县城还有不少请客的饭钱哩,都赊着。还有卖树用的雇车工钱,种花生耕地的钱,雇农民的工钱等等。
党委会选择在了星期五,会议结束后,晚上打扑克的人也凑不起来了,晚饭过后,我独自躺在床上,琢磨着石敢的那三句歇后语。
“咚咚咚”清脆的敲门声送来了话务员高蕾甜甜的声音:
“刘书记,钱书记的电话。”
钱顺那大舌头伴上电话的杂音显得话语更结巴了。我在电话上只说知道了。钱顺说了两遍:你办事,我放心。放下电话,我让高蕾把炊事员魏柱和公务员张亚叫到话务室。乡政府大院今晚就剩这三员大将了,我传达了钱顺的电话指示,先征求这三员大将的意见。
魏柱听完我的话后,狠狠地冲出三个字:
“日他妈!”
这事儿,我也不情愿。可在钱顺的电话里,既不能说不要办,又不能说办不了,既然答应下来了,那就办吧。于是,我向这三员大将下达了命令:
“小高守好电话,魏师傅磨刀,小张和我出发。”
星星闪烁着,好似静静地观察着地面上的一切。这乡村的夜晚是那么地温顺和幽美。柳村静静地躺在乡政府的左边,睡在公路的一侧,像孩子那样安宁香甜。我和张亚借助着淡淡的星光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柳村支书的门前。还没有敲门,支书的狗便狂吠起来,那一声紧似一声的狗叫简直就像撕你的心肝五脏……
大门开了,狗不咬了。那支书见是我,表示出了热烈的欢迎。倒水、找烟、还端出了一盘饼干,并吩咐女人去小卖部买肉、买酒。我制止了他的一切接待议程,开门见山,点出了正题。
那支书盘腿坐在炕上,点了一支烟,吸溜着舌头:
“刘书记,对不起,我得把话说清,你拿主意。羊,不要说十个,二十个也有,不要说三十斤以上的,四十斤以上的也有。关键说钱哇,乡里出还是村里出,现给还是赊账?”
我便进行了一番询问。若买活羊,给现钱,毛重每斤两块左右,赊账,三块左右。若光要肉,现给,每斤三块左右;赊账,每斤四块左右。我算了算账,觉得光要肉省钱,便向那支书说:
“价格和钱你等钱书记回来和他说嘛,先把羊肉弄上。”
那支书不答应。
我以为那支书不相信我,便说:
“你给钱书记打个电话问一问嘛。”
那支书说:“这电话我不打。”
说了半天白磨嘴皮。
这电话只有我打了。
星星仍在天穹深处闪烁。我和张亚只好再往乡政府返。深一脚浅一脚,张亚也骂开了大舌头。
这是个很少说话的孩子。
一进乡政府的大门,张亚惊喜道:
“刘书记,石乡长回来了。”
我一抬头,看到了石敢窗上的灯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救星——总算找到救星了。我直奔石敢办公室。
石敢正在洗脚,招呼我坐下后如释重负:
“刘书记,杨村和柳村的矛盾总算解决了。”
杨村和柳村为了那五百亩土地的事儿争得不可开交,闹得乌烟瘴气。因钱顺答应过村干部和群众,花生乡里只收一年,明年把土地交给杨村和柳村,部分群众竟先下手为强在地里有的做标记,有的已经耕过了,两村的干部一说到地界便吵架。钱顺多次召开党委会,搞了几次现场办公都无济于事。石敢一个人就给解决了。但我现在顾不上听这个,便把钱顺的电话指示以及我去柳村的碰壁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石敢进行了汇报。
“哎,十只羊,不就是二三千块钱嘛。”石敢擦了脚,“钱书记既然委托给你了,你办去就是了。”他竟说得那么轻松。
“我的石乡长呀,你看我能办了吗?”
“办不了就算了。”石敢眨了眨眼,“这件事真应该拉倒。”
我急问:“那怎么向大舌头交账呢?”
“你咋和我说就咋和他说,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石敢笑了。“对。”我扭头走到话务室,轻轻敲了两下门。
“谁?”高蕾问。
“小高,是我。”
“哦,刘书记,进吧。”
“你……你,没有睡觉吧?”
“睡觉怕啥,进吧。”
我的心“咚咚”地跳开了,我敢进吗?
我只好扭头再找石敢。
我刚走出几步,高蕾开了门,并喊住了我:“刘书记,和你开个玩笑。”
我再一扭头,借助着淡淡的星光一看,高蕾没有半点裸露,两只羊角辫甩来摆去,好似怒放着的一朵牡丹花。
高蕾老老实实地给我摇电话,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摇啊摇,摇啊摇,那黑色的辘辘把儿摇了半天也没有摇出一个字来,交换台无人值班。
高蕾有什么办法呢?
还得找石敢。
石敢给写了个条子,让我骑上他的摩托车带上张亚去杨村,可不要说大舌头要羊。
找到了杨村支书,我只淡淡地说:“石乡长让我把这个条子给你。”
那支书看完条子,只是皱皱眉说,“这么迟了。”随即点了头,“办哇,能行。”
我补充道:“那上面可有时间限制啊。”
“保证不误。”那支书回答得十分肯定。
石敢的条子竟有这么大的威力。回来的路上,我苦苦地思索,也没有思索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似睡非睡,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敲门。杨村那支书来了——十个羊肉提前到位。
天穹深处的星星逐渐隐退,东方已放出了鱼肚白。
高蕾也跑了过来,说钱书记的电话又在叫我。
他一定是问羊肉之事。这回我百分之百地猜对了。
我拿起电话,只听大舌头说:
“刘书记哇,你……你,辛……苦了,拉羊肉的车……八……八点就能……能到,车……车……车牌号码……号码,记……记,住,三七……二一……”
高蕾就在我的旁边,大舌头电话里的话她可能听到了。我向她眨了眨眼,说:
“钱书记哇,实在不好向你交账。我跑一夜,只搞来五个羊,怎么也没办法了。你能原谅我吗?你看这,哎。”
钱顺听了这话,他那大舌头里只嘣出一个字:
“这、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