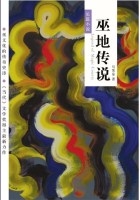盛家老寿星的丧事是在鬼子撤退后的第三天举办的,同时埋殡的还有离石“盛德荣”商号的王掌柜。
水旱码头碛口眼下最兴旺最发达的盛、李、程三大家一时都被牵动了。要不是国民政府有令,非常时期不准长时间聚众操办婚丧之事,这事宴还不知要弄得如何铺张呢。
在老寿星停尸床前哭出第一声的是盛如荣的小孙子盛慧长。
盛慧长的娘爱看戏,盛慧长是被他娘生在戏场的。也不知是不是给人挤的,这小家伙长着一条细而长的脖子,一天到晚都像在抻着脖子看戏。于是盛家上下就把他叫作“蛇丝二吊子”。“蛇丝子”即孵化不久的小蛇,“脖子”长。所以把这小爷叫作“蛇丝子”倒是没有冤枉他。至于说他是个“二吊子”、七成成、傻瓜蛋,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盛家这位小爷四五岁就能将《三字经》《百家姓》倒背如流。他娘带他到黑龙庙看戏,戏一散他就能将大段大段的戏文学唱下来。大人们当他面说话,他听上一遍就能连神情带腔调学说个八九不离十。你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二吊子”、“七成成”、“傻瓜蛋”呀!
在水旱码头碛口,“奶奶”不叫“奶奶”,叫“牛牛”。盛家小爷盛慧长听说躺在床上的“老老老牛牛”死了,就哇哇大哭起来。他的老姑盛如蕙红肿着两眼朝他喝道:二吊子,住嘴!
盛慧长不明白“老老老牛牛”死了,为甚不许哭,就哭得更伤心了。盛如蕙弯腰摸摸慧长头顶上的朝天小辫,用软软的声音道:二吊子,听话啊!“老老老牛牛”现在正动身要往天堂去,你这一哭,她老人家还不迷了路?待会烧过“倒头纸”,咱大家一道哭。到那时,我们二吊子想怎哭就怎哭。
如此,盛家这位小爷只好闭了嘴、屏了声,两眼滴溜溜转动着看大人们都在忙些什么。只见他老姑盛如蕙朝屋子里的男人们挥挥手,男人们便很听话地退出屋门去了。老姑瞅瞅站在炕边的他,皱了眉头道:二吊子,你也出去。
盛慧长却倔倔地站着,就是不挪窝。老姑盛如蕙叹口气只好作罢,回头命女佣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香汤,又让秀兰、秀芝两位姑姑帮忙,想把老寿星已经上身的寿衣脱下来,重新为她老人家沐浴净身。可老人家僵得像根木棍儿,根本无法脱衣,只好将就着把能够探得着的地方再擦洗一回。老姑一边动作一边慢声细语说:老老牛牛啊,您老人家洁洁净净一辈子,到头来却要邋邋遢遢走了,这让我们做小辈的如何过意得去啊!说着眼里便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来。秀兰和秀芝两位姑姑也无声地哭了。于是便让男人们进来,先找了一枚干净的铜钱款款塞入老寿星半张着的嘴巴里,麻纸一张盖脸,又将七个铜钱大的小面饼穿上一截干草塞入手心。盛慧长看见那干草的一端拴着一根细麻绳,听老姑说那叫打狗鞭,是让老老老牛牛一路驱赶野狗顺利升入天堂的。爷爷他们将老老老牛牛横着摆在炕头,炕下放个大铁盆,便将一摞纸烧着了。火光一起,屋里屋外跪下黑压压一片人。盛慧长也被如蕙老姑拉了爬在地下,粗粗细细的恸哭声轰然爆响。
在一片呜呜哇哇的哭声中,慧长听得女人们咿咿呀呀载泣载诉的哭声特别中听,只有珂珂、璐璐和几个未出阁的小姐丫头在哽哽咽咽抽泣,听上去活像一群吃坏肚子的小狗在打嗝。男人们只知呜呜,声音低沉而喑哑。爷爷一边哭一边擤鼻涕,慧长看见有一团鼻涕照直甩在了伯母额头上。听着看着这一切,他一点儿都哭不出来了。突然腿上一阵剧痛,侧转身一看,原来是母亲故意拧了他一把。他摸着大腿哇的一声哭了。这时,身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叫道:大家节哀顺变吧。老太太高寿,是喜丧,哭多了不吉利!四周哭声顿止。一片衣裾窸窣声中,人们纷纷起立。
王掌柜的灵棚搭在三槐堂“人门”之外,人已进了棺木。王家、盛家的人一拨拨进去行祭奠之礼,有七八个和尚绕着灵堂转圈儿。他们的秃头亮光光的,脖颈间都挂着一串油汪汪的紫檀木珠子,两只手交合着举于颌下,口中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当日子夜时分,盛家老寿星被装进棺木,置于灵堂。灵堂设在待月庐正面抱厦下,用三十丈青布结挽而成。两侧用白纸剪成长长的挽联。左金童、右玉女,宝马、香车成双结对。棺木前置香案,上点“水灯”(当地风俗,灵棚点掺了水的油灯)一盏,还有四荤四素八碗供献。盛家男女这时都换穿孝服,依班辈前来祭奠。在和尚们打坐念动超度亡灵经的同时,白日剪好的悬塔挂到了三槐堂天门外。老寿星的悬塔好气派!偌高偌大的天门一侧居然挂不下来,只好在半人高处连拐两个弯爬高后再让它悬垂而下。王掌柜的悬塔已先一步挂在了人门旁。三槐堂外这并排挂着的两副悬塔,以及镶嵌于白色剪花之中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仇敌忾驱逐倭寇”的大字吸引了古镇碛口及附近村子的许多人前来观看。人们指点着,忆及老寿星、王掌柜生前的种种事迹,众口一声诅咒狗日的日本鬼子出门都撞枪子儿。
崔鸿志来到三槐堂前,他好像刚刚赶了好长的路,带着一身尘土、汗水走来了。见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他就劝众人快快回家。有几个年轻人说要参加游击队,崔鸿志说让到游击队队部报名。
“正事宴”举办的日子定在第二天。
第二日一早,盛慧长还在被窝赖着,忽听天门外“呜呜哇”一声大号鸣过,盛家雇用的三班吹鼓手一齐奏响哀乐。慧长被母亲提溜着爬起来匆匆穿了孝服跑出门外,只见盛家的男人女人白花花一片已恭立待月庐大门一侧,鼓乐班子在孝男孝女们的恸哭声中被迎进院门。四个“礼生”出现在正屋外的高圪台上,“通赞”宣布“开奠”,于是鸣炮奏乐,全天的奠仪正式启动。接下来是“祭风神”、“祭菩萨”、“拜榜”。“引赞”像应声虫似的附和、复诵“通赞”的口令。“文赞”用唱歌似的调子诵读一篇篇祭文。“哑赞”则一声不吭地点拨那些呆头呆脑不能正确领会“通赞”口令的男女。
各种仪式按部就班进行。
盛慧长听大人们说,全部奠仪中最数午奠隆重。在水旱码头碛口,丧祭中本来就有“笑奠”的习俗,即借奠仪开各类外戚们的玩笑。而李莺莺高寿过百,是“喜丧”,所以那些礼生是必要生着法儿逗乐子的。这倒有趣。盛慧长便老等着午奠的到来。
可是,待到午奠真的到来时,竟也索然无味。他被母亲挟持着按“通赞”、“引赞”发出的口令一会儿“序立”,一会儿“俯伏”,一会儿“跪拜”,一会儿“平身”,一会儿“出列”,一会儿“复位”,一会儿“上香”,一会儿“献馔”,弄得昏头胀脑,疲惫不堪。春日的阳光热烘烘悬在头顶,白茫茫一片中,有人发出短促的鼾声。他听得一只蜂子嗡嗡着从他的耳边飞过又飞来,飞来又飞过。嗡嗡声持续不断,忽然化作黄河滩头奔腾的浪涌,而他浑身赤裸正在浪涌间腾挪翻滚……忽然听得有人咿咿呀呀唱起小曲曲来。盛慧长强撑着眼皮朝高处看去,原来是“礼生”们在唱“主吊挽歌”,竟将老老老牛牛一辈子瓜长蔓短的往事编成曲子唱得合辙押韵、荡气回肠。那时,四“赞”主从换位,“文赞”主唱,“通”、“引”作配。“哑赞”也不“哑”了,时不时插科打诨,将人们逗得一会哭一会笑。慧长的精神为之一振,正要仔细听去,那歌儿却已接近尾声:
风摧杨柳雨打蓬,
百花凋残在严冬。
可怜纤纤兰花指,
一朝化作血玲珑。
天啊天,
天若有情天雷震,
灭绝倭寇小日本!
地啊地,
地若有情地火腾,
灭绝倭寇小日本!
神啊神,
神若有情神圣出,
灭绝倭寇小日本!
鬼啊鬼,
鬼若有情鬼魅生,
灭绝倭寇小日本!
那“灭绝倭寇小日本”一句,由“四赞”和声唱出,听上去如呼唤,如吁请,如呐喊,如恸哭,如梦乡中炸响的惊雷,如传说里黄河发出的龙吟。之后,“四赞”突然沉默了,沉默着眼望虚空久久伫立。盛慧长只听得黄河滩头浪涌飞溅传来的哗哗声、众人喘息响起的呼呼声和无数颗捏紧的拳头发出的咯咯声。蓦地,那“文赞”一甩散落在额前的碎发,发出一声曲里拐弯的“咦——”接着唱道:
日子好比一盆火,
再苦也得笑着过。
想当年老寿星芳名莺莺,
她本是李家山豪门千金。
她的父李运旺大名鼎鼎,
李家山扛伞头远近闻名。
李伞头他还是梨园功臣,
斥巨资建班社娱乐民众。
道情、梆子、小花戏,
你想看甚就演甚。
李小姐她从小拜师学艺,
更比那“咳咳旦”伶俐聪明。
李小姐风流俊俏人人爱,
佳人绝色又偏是顽蛮任性。
倾倒了古镇碛口万千男女,
迷住了盛家小爷景涛后生。
黄河滩头乾隆石,
卧虎山后猫圪洞,
他二人偷情偷得烈烈轰轰。
现如今李小姐喜得传人,
盛秀芝她本是莺莺重孙。
你别看秀芝她外表实诚,
自小就学会了日哄男人。
游击队长崔鸿志,
古镇碛口一英雄。
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
崔队长剜苦菜迷上了狐狸精。
……
盛秀芝近年来身子骨一直不大好,这时,她正靠着丈夫崔鸿志跪在灵棚下一片孝男孝女中,倾斜着半个身子一副气力不支的样子。猛可里听得那“文赞”七拐八绕编排开了自己,盛秀芝做一副着恼的行状顺手脱了一只孝鞋就冲“文赞”砸去。“文赞”像是早有防备,头一偏,那鞋子恰好扣到了“通赞”亮瓦瓦的光头上。
一院子孝男孝女亲戚朋友,以及重新攒集过来看热闹的邻里都笑了。笑着叫:剜苦菜迷上了狐狸精,好,好,好!
原来盛秀芝早年做姑娘时竟是个能歌善舞的。正月里各村的秧歌队在黑龙庙唱小花戏,她曾扮过一个狐狸精。小戏演完后,又被观众吆喝上台和那时还不是丈夫的崔鸿志对唱过一回小曲儿。这两码事本来是“卖瓜籽的碰上耍把戏的——两无瓜葛”,可后来又出了一件事,却把二人连到一起了。那一年崔鸿志被学校开除回来,李子发将他请到天成居做了二把刀(方言,二掌柜)。有外地客商朝他建议,弄些苦菜凉拌,清淡可口,最是山外人爱吃的。崔鸿志一想,可不,这苦菜命贱,遍生吕梁山的沟渠路畔荒坡野洼,富人极少问津,穷人却将它们当做半年的口粮。那东西可是有多种多样吃法的,如果仔细泡制,确是清淡可口。于是有一天,崔鸿志就独自上山去剜苦菜,想着先做点试验。当他正钻进一条小沟埋头一片鲜嫩的甜苣时,背上猛地被一颗青杏打了一下,抬头一看,见山包上长着一棵杏树,却不见人。崔鸿志的心头突然响起本地流行最广的小曲曲《掐蒜薹》的旋律,因将词儿稍作改动,信口唱道:
我在这沟里剜苦菜,
头顶扔下青杏来,
这事儿好奇怪!
崔鸿志唱罢,埋头继续剜菜,没想到山包上杏树后有人却接了腔:
春风刮得树枝枝摆,
青杏打了狗脊背,
休得将我怪!
崔鸿志抬头一瞧,乐了,原来接他腔的是盛秀芝,那个和他对唱过曲儿的盛家小姐。她也是来剜苦菜的(看起来,富家人也爱吃这一口呢)。崔鸿志略加思索,正要来个“以牙还牙”,却见那盛秀芝风摆杨柳似的早走远了。
如果这以后二人之间没有阴差阳错,又在原地聚首的事发生,大约这一对冤家就不会有后边的故事了。当时,崔鸿志明明看见盛秀芝是朝北山走去的,心里对她“骂”了自己却转身逃走很不满意。因为但凡唱“对嘴曲子”的都得遵守一个规则:要么你不要先捡便宜“骂”人,既“骂”了就得恭候别人回敬。别人回敬了,你还可以再答,总之是要奉陪到底。如果你“骂”完别人回头就走,那就太不仗义了。岂止是不仗义,内里还有怠慢人的意思。所以当时崔鸿志就想,这盛秀芝是凭着自家出身豪门小瞧人,因自语道:有什么了不起!你瞧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呢。便转身向南山走去。没想到过了两个时辰,他发现自个儿又转回了先前那条小沟。最不可思议的是,当他偶一抬头时,发现那盛秀芝竟也出现在了那棵杏树下。在崔鸿志和盛秀芝对视的一刹那,二人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字:缘。崔鸿志早将先前的不快忘得一干二净,张口唱开了《摇三摆》(当地民歌曲牌,亦可用作谣曲中之衬词用):
天上的乌背(方言,即苍鹰)哟依哟,
地下的个鸡,
绕来绕去摇三摆,
撂不下个你。
山包上久久没有回应,盛秀芝仿佛在用心斟酌着什么。终于,她也开口了:
黄雀雀钻在了哟依哟,
圪针针林,
听见狗叫摇三摆,
不想见你的人。
原曲曲后头一句是“听见你的声音不见你的人”,是女的思念男的,想快快见到他。现在盛秀芝将它改了,分明又是在生着法儿“骂”对方了。可这一回,崔鸿志并未生气,反倒乐得大嘴咧咧的,就放开胆子接着唱下去:
大槐树上吧哟依哟,
金鸡鸡跳,
想约你见面摇三摆,
学狗儿叫。
崔鸿志也把原曲曲后头一句词儿改了,改得倒巧。这样一来,等于把“窗户纸儿”捅破了。
山包上又是一阵沉默,盛秀芝再开口时,用手半捂了嘴,声音变得有些期期艾艾:
水道壕起了哟依哟,
倒跌子(方言,即蚊子幼虫),
心里头有话摇三摆,
你就唱曲子。
盛秀芝又把原曲曲后头一句淡话改了,加了一匙糖,却并不浓。甜咝咝的恰到好处。盛秀芝满以为有了她这暗含情意的话,崔鸿志该心满意足地走了,没想到那崔鸿志却得寸进尺,接着唱道:
你在山顶上哟依哟,
我在这沟,
探不着亲嘴摇三摆,
招一招手。
崔鸿志嘴到手到,果真朝山包上的盛秀芝招了招手,还一脸坏笑地啧了一下嘴。
盛秀芝慌不择路地跑下山去了。
这段故事是崔鸿志在同盛秀芝成亲后,自个朝他那些狐朋狗友谝出口的。
盛秀芝的一只鞋打在了“通赞”亮瓦瓦的光头上,灵棚内外一片哗然。要说这盛秀芝,虽然出身大家小姐,可这些年跟着崔鸿志整天同四乡的农民、镇街的工友混在一起,受苦人都把她当自家姐妹看,彼此嬉笑怒骂全没一点规矩,惯了。就如眼下,那“通赞”吃了亏,也不生气,反而大嘴咧得红鞋也似,继续朝着盛秀芝和崔鸿志张牙舞爪:
“怎么,你们俩是‘夜壶捣了嘴子——不敢亮家伙了’?”
崔鸿志被他一激,头一扬,就开唱了:
苋子红来韭菜青,
日怪不过人迷人。
好比秤砣迷秤杆,
好比金线迷银针。
小姐她本是一朵花,
被咱迷得丢了魂。
做饭忘了生火炉,
生火忘了寻“取灯”(方言,即火柴)。
茶不思,饭不吃,
活活得了“时令症”(方言,即伤寒)。
你说日怪也不怪,
谁叫咱是百里挑一的好后生!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盛秀芝反唇相讥:
狗戴帽子充人样,
猪鼻子栽葱装大象。
女人生来心肠软,
三盘两绕上了当。
要不是看你可怜样,
成了亲也不上你的炕。
“四赞”不约而同拍手叫好,崔鸿志正要再唱什么,忽听得远处传来隐隐的隆隆声。崔鸿志脸色骤变,大叫道:
“敌机!大家快快疏散隐蔽……”
院内院外当即大乱,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许多游击队的人。盛慧长看见他们和姑父崔鸿志、小姨璐璐等冲进人群搀扶年老体弱的人。秀芝姑姑也像换了一个人,在人群中连跑带跳又叫喊,俨然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成了姑父崔鸿志的好帮手。盛慧长看见她一人就来来回回搀走几个老妇人。
两架敌机在头顶盘旋了几遭,看看没多少油水好捞,隆隆响着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