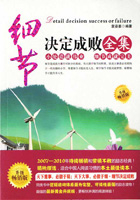“你呀!就是太老实好欺负了!”刘嫂一屁股重重的坐下,那张破木板床都晃了几晃,“要换了我,敢欺负到老娘头上,老娘把他老刘家整得求爷爷告奶奶你信不!”
陈氏只是低了头,颓自抹着泪。
刘嫂见陈氏哭的可怜,连连摇头道:“上个月我抱桂花回娘家,还碰到你娘,你娘还问我你咋样来,我能咋说,我说好啊!你娘要知道你这样,还不心疼死啊!”
“刘嫂,你可千万别跟我娘说啊……”陈氏抬起头,哀求道。
“放心吧你就。把心给我稳稳的踹肚子里,”刘嫂拍拍她的手背道:“我刘嫂是那不知分寸的人么?”
“说句实在的,我家老刘是个杀猪的,当然比不上你家男人拿笔杆子的,可是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男人干啥的重要不?不重要!吃饱饭不饿着冻着才是正经!这吃都吃不饱了,这拿笔杆子还比不上咱杀猪的呢!哎,我话丑,可理正,所谓话糙理不糙,你可别怪我说的难听呦。正经为了你好。”
陈氏叹口气,道:“不怕你笑话,刘嫂,你也看到了,家里这些事儿,哪轮的到我来做主。”
刘嫂想想也是,说这些也是徒惹陈氏伤心,自己到底不是海家的人,哪能管的那么宽,就轻轻的把话头转开去,指着陈氏身边的香菜笑道:“这是你生的娃儿?叫啥名儿?”
“叫香菜。”果然,说到女儿,陈氏凄苦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意。
“哎呦,真水灵。长大肯定是个俊俏的闺女!”刘嫂抱起小香菜,逗着她,“来,姨抱抱,给姨笑一个!”
香菜不失时机的亮出她的招牌笑容,“咯咯”的笑的格外的甜。
“哎,真乖,回头姨给你弄好吃的!”刘嫂大喜,捏捏香菜红扑扑的小脸蛋道:“汝贤媳妇,你这女儿是个鬼灵精呢。你可有福了。”
“可不是,从生下来就乖巧的很,一点也不哭闹。”陈氏面上毫无血色的嘴角勾起幸福的笑。
“比我那闺女可聪明多了!”刘嫂凄苦的叹一声,说着说着,就红了眼,最后索性捂着脸嚎哭起来,“呜呜……我家桂花咋就是个傻子哟!我那苦命的闺女哟!”
陈氏好一阵劝,刘嫂才收了泪,大袖子利落的抹一把眼泪鼻涕,坚决道:“我不哭!我还生,我就不信我生不着个聪明娃儿!我就生!我生出来为止!我就生个给村里那些背后嚼舌根子的烂货看看,堵那帮烂货的嘴!”
陈氏又安慰几句,六嫂才转悲为喜,她那神气的眼珠子在陈氏单薄的身子和平平的胸上打了几个转,直接说道:“我说汝贤媳妇,你咋看起来那么虚呢?你有奶喂香菜不?”
陈氏脸微红,惭愧道:“就是为这个事儿头疼哩。我奶水不足,没奶水喂香菜啊!”
刘嫂一拍大腿,道:“我就知道!我一瞧你那胸就啥都知道了。这可不行,刚出生的娃儿没奶喝可咋整啊?”
刘嫂精光四射的眼在屋里溜一圈,停在屋里唯一的一张矮桌子上,皱眉道:“上面的那篮子鸡蛋和红糖上哪去了?你都吃了不?我前几天儿来给你送猪下水,还瞧见来着。”
“咳,家里穷,拿不出钱给接生婆,那些……叫我婆婆拎了给接生婆了。”陈氏轻声道。
“王八羔子!哼,这个老东西!真是不干人事儿!”刘嫂怒道:“你刚生了娃子,就这么对你,要不是你拦着,我早就……哎……”
刘嫂放下香菜,拎起地上的篮子,在陈氏面前笑嘻嘻的晃晃,贼笑道:“送了就送了罢。不还有我么?瞧我给你带啥好东西了?”她说着,一把抽掉篮子上盖着的蓝布头,露出大半篮东西来,“嘿嘿,瞧,鸡蛋!还有呐……红枣子,自家晒干的,补血好着呐!恩……还有些花生。都是煮熟了的,香的很,我家老刘没事就能磕一地儿花生壳!”
陈氏瞧瞧那些鸡蛋红枣,鸡蛋都是又圆又大,估摸着有十几个,红枣花生散在其中,诱人极了。好久没吃到这些了,早上喝的那碗稀粥早消化的干干净净,她一下就觉得饿的不行,真想伸手捞上一把。当着刘嫂的面,又实在不好意思。
刘嫂听到陈氏肚皮“咕噜”作响,随手捞了一大把红枣花生,塞到陈氏手中,道:“吃!客气个啥!”
陈氏的眼再次湿润了,六嫂的话让她觉得暖心窝子。
“哎呀,我跟你说,我坐月子那阵,吃的老好了!”刘嫂眉飞色舞的炫耀,手舞足蹈的比划,“瞧,像这么大的老母鸡,连着宰了三个哩。吃的我看到鸡肉就吃不下。吃的好,奶水就足足的,管够,还吃不完,胀的我不行,就挤出来倒掉,可惜现在没了,不然正好喂你家香菜了!”
陈氏听着,一阵心酸。一旁的香菜听了,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自己的娘自打生了自己,别说一块鸡肉了,就连鸡毛,也没见着一根啊?这人和人,咋差距那么大呢。
“这女人做月子,可马虎不得,我那时生我家桂花妞,我婆婆可跟前跟后的伺候了我好几个月的月子,那叫一个暖心,”刘嫂语重心长道:“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月子做的不好,可是要落下病根的!咱女人,自个不晓得对自个好,还指望丈夫婆婆疼?”
陈氏抹着泪点头。
“得,我就说这么多了,家里还有事,也该回了,”刘嫂帮陈氏把被子掖掖好,坤直了卷起的被角,才站起身告辞。
刘嫂骨架子大,身量也大,高大丰满的身板和瘦弱的陈氏形成鲜明的对比,瞧着特别瓷实,她临出门想了想又转身叮嘱道:“那老太太要刻薄你,回头你告儿我,我替你出头,别人怕她,我陈翠花可不怕他!我男人我都敢打的他围着村子跑三圈儿咧!”
陈氏躺了一会,把那把大红枣吃了,顿觉满口枣香,身子也有了些气力,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唇角,起身仍旧把那蓝布头盖在那篮子东西上,想了想,又把篮子塞到床底下。
陈氏哄着香菜睡了,就起身去外头院子里,开始磨米粉。她本就是庄稼女人,躺着闲不住,又怕婆婆指鼻子骂自个躲懒偷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