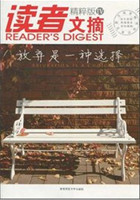高中生活索然无趣,形单影只的苏娅如同离群的孤雁,郁郁寡欢,孤独就像潜入她身体的蝼蚁,深入骨髓地噬咬着她。
那时候,桐城有电话的人家不算多,有钱人家也未必装电话,有资格安装电话的,多是有职位的官员之家。公用电话倒是有的,可偏偏学校到家的这段路不容易碰到。所以,苏娅虽然记下了贾方方家的电话,却苦于没有机会打给她。
学校的传达室有电话,可看门老头把它当成宝,除了对教职工表现还算大方,若是有学生想借电话一用,比登天还难。他能盘问你祖宗十八代,打给谁,给谁打,对方和你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得打电话?不打电话不行吗?你以为这是你家的电话吗?这是公家的电话,公家的电话就不花钱吗?公家的电话也得花钱。终了,就算你统统回答了他的问题,他也未见得就会恩准你打这个电话。同学们背地里管他叫死老头,死老头这日竟破天荒为苏娅开了绿灯。
那天中午,因老师生气故意拖堂,放学迟了,出校门时苏娅不经意朝传达室扫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钟表指针竟然指向十二点四十分了。她心里一顿,暗忖这时候贾方方应该在家。她早听说过门房老头出了名的难说话,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推开了传达室的门。老头正端着饭盒埋头吃饭,看到苏娅进来,警惕地问:“你有什么事?”
苏娅没说话,她毕恭毕敬给老头鞠了个九十度的躬,腰弯得头都贴到膝盖骨了,这个礼行得够大了。老头诧异道:“你,你这是做什么?”
“大爷,我想给亲戚打个电话,有点事。”苏娅终于直起腰来。
“什么亲戚?”老头果然询问起来。
苏娅随口胡谄:“姨妈。”心里忍不住恶作剧地补充为大姨妈,这么一想,脸上就笑开了花。
她打定主意,如果老头继续滔滔不绝追问下去,她就放弃打电话的念头。没想到,老头竟然点头了,也许是苏娅一脸灿烂的笑容打动了她,也许是苏娅刚才的躬鞠令他心软了,或者他的嘴巴正忙着咀嚼饭菜,顾不上多说话,总之,他没有像传言中那样,黄河长江绵延不绝地追问下去。
电话打通了,不巧的是贾东东接的电话,盘问半天她是谁,得知她是苏娅,口气冷淡地说,“贾方方不在家。”
“她去哪儿了?”
“她还没有回来,”不等苏娅再问些什么,贾东东“啪”地挂断了电话。
苏娅愣怔了半天,才把话筒放回原位。转身离开传达室的时候,忘了和老头说声再见。出了校门走出一段路了,方想起,适才应该和老头打声招呼的,老头一定恼恨她没有礼貌,以后若想再打电话,只怕是更难了。但是……她想,她大概不需要打电话了,是的,不需要了。
自花溪公园一别后,除了那个夭折的电话,苏娅与贾方方之间连一封信也没有通过。贾方方没有给苏娅来过信,苏娅也没有给贾方方去过信。既然贾方方不喜欢写信,她又何必讨个无趣呢?写信就像下棋,棋逢对手,旗鼓相当,才会有持久的兴趣,实力悬殊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在这方面,常秀丽才是她的对手,常秀丽真是具有一双慧眼呐,一眼就瞄准了苏娅。她启蒙了苏娅,开发了苏娅,如今却把她无情地丢在一边。苏娅不能多想常秀丽,每次想到她,她都会想起发生在厕所的那一幕,似乎满世界又都是厕所的气味。她努力想赶走这种气味,但是,没用,这特殊的气味总是在关键的时分,挥之即来,然而,却挥之不去。她曾给常秀丽写过一封信,写好了,封口用桨糊封好了,甚至连邮票都贴好了,却苦于没有地址邮寄。她想过把信送到常秀丽家里去,可是,也只是想一想,终究没有行动。以她对常秀丽的了解,常秀丽一定不想与过去的一切再有联系,那么心高气傲的姑娘,沦落在乡村小镇做保姆,光景黯淡,前途不明。还是,就这样吧,顺其自然,随着时间,相忘于江湖。她见识过常秀丽的狠心,这个狠心肠的姑娘,不止对别人狠,对自己也一样狠。她与常秀丽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对自己比对别人还狠的孩子,她们是同类人。
第二年夏天,苏曼考取了远在江南的一所师范大学,专业是物理。
苏娅暗暗替他惋惜,如此乏味的专业,将来只能在讲台上吸粉笔灰了。苏叔朋却十分高兴,儿子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他喜眉笑眼,都快把眼睛挤成一条缝了。苏娅甚至听到父亲说,他从前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当教师多好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父亲的表情看,这倒像是他的真心话呢。苏娅从不觉得当教师有什么好,如果让她选择,她断不肯做这行的。当然,她也没有远大的抱负,一想到未来,她的思维就断线了,仿佛联接处是一片汪洋大海,无路可走。年龄越大,就越懂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遥不可及。小学的时候,因为迷恋日剧,她幻想去日本留学。后来,又幻想去巴黎,那是某次在电视里看到塞纳河畔的美丽风光后滋生出的愿望。到了现在,她知道,出国对于她这样资质平庸的女生,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
徐静雅给儿子准备好了被褥行李,还特意给他买了一身崭新的运动服。苏叔朋则送给苏曼一只皮箱。苏娅没什么好送哥哥的,思来想去,去商店买了一支英雄牌钢笔,深红色的。苏曼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满怀憧憬,那个暑假与妹妹的关系也格外好,兄妹俩甚至还相约看了一场电影,看的是国产片《驿路人生》。这部电影曾经在收音机的午间时段播出过,苏娅刚看了开头,就想起自己曾听过广播,预先知道了结尾。苏曼问她怎么知道的,她佯装自己猜想的。影片结束,果然和她说的一样。苏曼赞扬她逻辑能力强,适合编故事。苏娅也不说破,暗自得意。
兄妹俩从电影院出来,苏曼要妹妹和他一道去一个同学家里拿本书,是古龙的小说《萧十一郎》,他说那本书是同学跟他借的,他想要回来。去的路上,经过一家商店。苏娅记起自己曾和常秀丽一起逛过这家商店,里面有好闻的酱醋味。她拉着哥哥进了商店,却惊奇地发现,商店完全变样了,变成了土产日杂店。没有食品,没有文具,也没有了先前的小百货,更没有弥漫的浓郁醋香了。柜台里只有锅碗瓢盆,笤帚簸箕,还有一捆一捆的粗麻绳,堆积如山,天知道这么多的麻绳要卖给谁。望着完全陌生的商店,苏娅很失望,她讨厌这样的变化,她对生活中所有的变化都怀有天然的敌意。
她对哥哥说:“你一个人去你同学家吧,我在这里等你。”
苏曼答应了。
苏娅绕着这间商店转了一圈,把每一样商品都审视了半天。她想,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什么都要变,连商店都要变。自己周围的一切已经变得够多了,现在,居然连一间商店也不能保持原样。这么想着,她就问售货员:“原来的商店挺好的,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售贷员说:“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吗?那我可不知道。”连售货员也是新来的,一问三不知。
苏娅在角落的陶瓷用品中发现了一只储钱罐,是个泥娃娃,仰着头,扎着小辫,嘴巴抿得紧紧的,眼睛就是两个小圆点,脸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雀斑。这个娃娃不同于平日里司空见惯的大眼小嘴的美女娃娃,它不仅不美,还有点丑。它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恍惚,无助,一副凄凄然的样子,仿佛对某件事物充满希望,又心知肚明那希望是不能实现的。它努力抬起头,仰起脸,想要抓住什么,确定什么,然而,脸上的神情终究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惘然。
苏娅被这个瓷娃娃吸引了,她让售货员从柜台里拿出来。她端详着它,心里升起几丝悲伤,她觉得自己就像这只娃娃,对一切改变生活的事物束手无策,想要抓住什么,却也只能听天由命。“多少钱?”她问。售货员说,“五块。”
价钱有点贵,超出了她的预想,她只好把娃娃交回售货员手里。苏曼返回来了,在商店门口喊她走。她问:“哥,你有五块钱吗?”明知苏曼不可能装这么多钱,她还是问了问。
苏曼果然摇了摇头,“我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几块钱,除去看电影,还给你买了冰糕瓜子爆米花,差不多都花光了,你想买什么东西?”
“没带钱就算了。”临走,苏娅回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丑娃娃。
开学以后,苏曼离家去外地读大学,家里只剩下苏娅与父母三个人。家里忽然少了一个人,房间显得空荡荡的。苏娅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待在阳台上抽烟,之前,父亲很少抽烟的。他心里在想什么呢?难道他在想念苏曼吗?苏娅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父亲会多愁善感地想念儿子,这可不像个男人。母亲还没有这样魂不守舍想念儿子呐。她觉得自己越发不了解父亲了,越发不了解这个男人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觉得她再一次被他伤害了,他对眼前的女儿视若无睹,对刚刚离开的儿子牵肠挂肚。而且,苏娅还发现,热衷厨艺的父亲在苏曼离开以后很少下厨了,偶一为之,也做得马马虎虎,仿佛他从前的烹饪热情都只是为了儿子的嘴巴。儿子一走,把他的魂都带走了,留下一个躯壳,这真是令苏娅感到万分的懊恼和怨愤。我究竟哪里不好,仅仅因为我是个女儿而不是儿子,就无法获得他的关爱吗?
苏娅对自己在日杂土产店看到的丑娃娃念念不忘,这一天,她从母亲手里诓骗到几块零用钱,放学后,赶紧去了商店,结果出人意料,丑娃娃不见了。售货员换了一个人,苏娅一再地讲述瓷娃娃的模样,可售货员说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娃娃。她信誓旦旦,没有,我们没有卖过脸上有雀斑的丑娃娃。苏娅疑惑,难道我那天看错了?不可能呀!售货员极力推荐她买另外的储钱罐,也是瓷娃娃,有男有女,还有小动物,个个俏皮可爱。可是,它们怎么能跟丑娃娃比,它们无法打动她的心。
贾方方曾在某个周日午后乘车来看苏娅,她没有提前写信告诉她,她想偷偷给苏娅一个惊喜。不巧的是徐静雅带着苏娅去商店买鞋了,苏娅的鞋子显小了,脚指头夹起了泡。本来还有一双方口布鞋合脚能穿,那是徐静雅自作主张给她买的,可苏娅讨厌它的颜色,猪血一样的红色,死活不穿。无奈,徐静雅只好带着她去买。
苏叔朋也不在家,不知是单位加班,还是去哪里了。
贾方方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桐城的市中心到了西北角,却没能敲开苏娅家的门。她郁闷地在门口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又去楼前楼后传悠了一圈,还去她家从前住的房子看了看,里面有了新的住户,门罅着一道缝,她站在门口朝里面探视。传出两个人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她伸手想敲门,可是又不知该和人家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呢?以前在这儿住过,想进来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只不过换了家具换了主人而已。换了家俱换了主人的房子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你就是进去看了,又有什么意思?能获得什么,也许只能徒增伤感。伤感,这是个令贾方方厌恶的词语。她喜欢明亮的事物,厌恶萎顿,颓废,青春期流行的那种动不动就心头涌起莫名其妙的忧伤,她觉得可笑极了,没意思透了。想到这儿,她转身离开了。她是阳光灿烂的如花少女,和苏娅不同,虽然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物理课上讲阴阳正负,异性相吸。她和苏娅大概就是这样的异性相吸吧。这个异性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别之分,而是另外一种,她也说不清,反正就是类似异性相吸的原理。
楼下碰到认识的邻居,纳罕地打问她回来做什么,她说是来找旧同学的。按说,除了苏娅,附近也有与她同龄相识的女孩,可是,她与她们实在没多少交情。她的童年和少年都和苏娅扭在一块,像扭麻花一样,扭得紧紧的,没有留出空余。苏娅也是这样,记忆里,她们几乎没有和其他的女孩子有过密切的交往,其实也和小朋友玩过耍过,跳皮筋,丢沙包,捉迷藏,一群一伙的厮混在一起,浩浩荡荡,吆喝着,奔跑着,汗流浃背。可玩过之后,“哗”一下就散了,总是剩下她们俩,所有的记忆里只有她们俩,黎明,午后,黄昏,夜晚,春夏秋冬,总是只有她们俩。她们就像一种游戏里的伙伴,两个人各自的一条腿与对方绑在一起,要走一起走,要停一起停,配合不好,就会摔跟头。她们一直配合得很好,很默契,尽管有过短暂的分歧,但是很快合好如初。
贾方方曾幻想过,如果自己是个男孩子,或者苏娅是个男孩子,那该多好,她们可以谈情说爱,长大了,名正言顺结婚,住在一起。可她们偏偏是同性,她倒是听说过同性恋,觉得这个词蛮新鲜,蛮好,可是有一次,她在报纸上看了这方面的报道,说同性恋是变态的情感,它是见不得人的,丢脸的。那可不好,她就此打住这个念头。她在新的学校交到了新的朋友,她是个大方,慷慨,乐于助人,受欢迎的女生。可是,交再多的朋友,她的心里也似乎缺了一角,当她和某个女生过往甚密的时候,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对不起苏娅。
哦,她知道苏娅之前和常秀丽好过一阵,在贾方方眼里,常秀丽有点不正常,她们天天见面,还互相写信,神经兮兮,这令她一度心生嫉妒。搬家转学后,每次收到苏娅写给她的信,她就会由此想到常秀丽,想到她们之间就是这样吟风弄月,酸文假醋的,什么梨花雨纷纷落下,只有我独坐树下;什么春风吹绿了小草,吹皱了我的一池心湖……酸不酸啊,她讨厌这些,她也不喜欢苏娅这样,她不大给苏娅回信就是因为这个。她喜欢就事说事,有一说有,有二说二,言简意赅,那种文艺青年的腔调不适合她。她看流行小说,也绝不看琼瑶那种哭哭啼啼的,她看亦舒,看岑凯伦,看梁凤仪,看这些冷静,真实,客观,像生活本身的作品。
在苏娅与常秀丽关系交好的那段日子,她正陷在一场似是而非的早恋中,无暇顾及苏娅的感受,所以,她原谅了苏娅对她的疏远。回过头看,她挺感谢那场恋爱,青春期的女孩最好能够谈一次恋爱,它具有免疫作用,就像打预防针,它会使你在以后的情感道路上免受磨折。现在,在新的学校,新的环境,经常有男生对她示爱,她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一点也不慌张,不激动,不沾沾自喜,她不接受他们,也不去拒绝,她知道怎样保持分寸。她能够这么从容,老练,全都得益于她与崔浩的那场早恋。崔浩,那个细高个子的男生,她除了记得他送自己的那对仿银镯子,几乎把他的样子都忘了。她想自己大概是个没良心的人,她从来也没有觉得初恋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情感。它来得快,去得快,像雾像雨又像风,一闪而过。想要记起什么的时候,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她能想到苏娅目前的状况,她一定很想念自己,但是见了面,还会装得若无其事。她太了解苏娅了,苏娅就是一个对什么最在乎,就偏做出对什么无所谓的人。有时候,她会替她担心,她这个样子,将来是要吃亏的。不过,将来太远了,远得看不见,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楼前楼后转悠够了,贾方方又重新去敲苏娅家的门,敲了无数遍,里面仍然寂无声息。敲门声惊动了苏娅家的对门,女主人探出头。贾方方早从苏娅的描述中熟悉了这是一户怎样的人家,这家人是轻易不同外人搭话的。她连忙道歉:“对不起,我的敲门声是不是打扰您了?”
“家里没人,你就是敲破了天,也没用。”
“他们都去哪里了?”
“我哪儿知道。”说完,女主人“砰”地关上了房门。果然有性格,贾方方冷哼一声。
这女人说得对,家里没人,敲破天也没用。眼看时间不早了,她不能一直等下去,谁知道苏娅去哪里了,没准儿晚饭后才回来呢。这么一想,她决计不再等,赶紧下楼走了。
她就那样走了,有些失望,有些埋怨,有些不甘。临街的杂货店,小卖铺,熟食店,裁缝铺,理发店,烧饼摊依然如故,这是她无比熟悉的地方。她一家挨一家进去转转,也不买东西,就是东看看,西瞅瞅。这条街的气味,这些店铺的主人,都是她从小就熟悉到无感觉的好象自身的一部分。就在她在裁缝铺打量墙上挂着的一条勾脚裤的时候,门外经过了一对母女,正是苏娅与徐静雅。
这对少年密友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苏娅才知道贾方方曾经来找过她的消息。
那天,她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出了家门,楼道里碰到出来倒垃圾的对门。那女人先是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走在前边,女人跟在后面,下了几级台阶,女人忽然开口:“那天,你们家没人,有人找你来着。”
“找我?”苏娅转身,疑惑地问。
“是的,找你,敲门敲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是找我的?谁找我?”
“那个总在楼下喊你的姑娘,后来她家搬走了。”别看对门女人足不出户,对于苏娅家的情形蛮了解。
“贾方方。”苏娅脱口而出,“哪天的事?她什么时候来找的我?”
女人慢悠悠地说:“快一个月了,是个礼拜天的下午。”
“你怎么才告诉我?”苏娅有些愤怒了。
那女人觉察到苏娅不悦的口吻,反问道:“我有义务非得告诉你吗?她也没有托我转告你。”
苏娅顿了顿,没再吱声,继续下楼。心想,可恶的老女人,你还不如不告诉我呢。
得知贾方方曾经找过自己,苏娅决定再给贾方方打一次电话,这次她没再打学校传达室老头的主意,而是找了一家公用电话。当她拿起话筒拔号的时候,自以为熟稔的那串号码却一下子变得模棱两可。她试着拔了一个,对方说,打错了。她又拔了一个,对方仍然说,打错了。这串号码她一直依靠大脑储存的,没有在任何地方记录过,她以为它们早就刻在了她的心里,永远不会遗忘,没想到,记忆是如此不可靠的东西,她竟然把它们忘记了。
自那以后,她同贾方方的联络日渐式微。后来,她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话:最好的友谊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它不可能延续一生,能够延续一生的友谊,那就一定不是最好的。苏娅盯着这句话看了良久。再后来,苏娅和贾方方的联系就只剩下新年元旦时一张薄薄的贺卡,高中毕业后,贾方方一家随父亲的再次升迁搬离了桐城,去了省城青州。那之后,她们之间就彻底断了音讯,这段影响苏娅一生的友谊划上了句号。
很多年以后,不,不是很多年以后,应该是多年以后,贾方方的姐姐贾东东辗转找到了苏娅。贾东东出现在苏娅面前的时候,苏娅正埋头清理办公桌上的杂物。同事带着一个高挑白晰的女人走进来,对她说:“小苏,有人找你。”她抬头看着面前的女人,疑惑不解:“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她压根没有认出这个女人是贾东东。贾东东戴着茶色太阳镜,身穿米黄色羊毛衫,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正是春天,桐城春天的风沙总是铺天盖地而来。贾东东摘下太阳镜说:“苏娅你好,我是贾东东。”
“贾东东?”苏娅失声叫道,她站起来,掩饰不住满脸的意外和惊讶,“你……你怎么来了?”她立刻联想到贾方方,“你们家不是搬到青州去了吗?贾方方现在怎么样了?我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她还好吗?她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吗?快,快请坐,我给你泡杯茶。”她慌乱地转身寻找水杯和茶叶筒,张罗给贾东东泡茶。
贾东东客气道:“苏娅,我不渴,你不用忙的。”
“天气这么干燥,怎么能不喝点水呢,你可是稀客,算一算,我们多少年没有见过了,有十几年了吧,自从你们家搬走,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苏娅有些激动,语无伦次,她早就忘记了少年时代与贾东东的不睦。她拖过一把折叠椅,把贾东东请到椅子上。茶叶筒和茶杯找到了,却发现暖壶空了一大半,倒出来的水,飘着白色残渣。她尴尬地解释,“哎哟,你先坐,我下楼打水去。”
贾东东忙阻止道:“苏娅,我说过了,我不渴,你就不要忙活了。”
苏娅仍旧拎着空暖壶执意去打水,贾东东说:“别去打水了,真的,我来找你是说方方的事,我们还是先谈事吧。”
“方方?贾方方?贾方方怎么了?”苏娅正要迈出门的腿停住了,转过身。
贾东东还未开口,忽然哽咽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纸巾,擦了一下眼角。
“怎么了?”苏娅心头一沉,贾东东好端端哭什么?
“方方得了病,是癌症,已经扩散了,没多少时间了。她对我说,她很想见你,我就回桐城找你了。先是去了你家,幸亏你们一直没搬家,可是房门锁着,里面没人,邻居告诉我,你母亲去北戴河疗养去了,她把你的单位告诉了我,我这才找到你……”
苏娅没有听清楚贾东东后面说了一堆什么话,她的脑子一下子懵住了,她只听明白贾方方得了病,是癌症,快死了。她呆呆地站在门口,手中拎着红色的铁皮暖壶,走廊旁经过的同事跟她打招呼,好像问了句什么,没听清。她返回办公桌前,把暖水壶搁在墙角。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贾东东,试图从她的脸上窥出些什么,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贾东东是不是在和她开玩笑?可是,贾东东始终低着头,似乎被巨大的悲痛压得抬不起头。
不知道过了多久,苏娅终于开口说道:“你刚才说癌症,什么癌?”
“子宫癌。”贾东东低声啜泣道。
苏娅心里一紧,问:“贾方方,贾方方她结婚了吗?”
“一年前结的婚。”
“有孩子吗?”
“如果不是怀孕,也许还不会得这个病,怀孕两个月的时候高烧不退,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这个病。”
“那就赶紧把孩子做掉,摘除子宫,我听说有人也得了这个病,摘掉子宫就好了,真的!不骗你。”苏娅几乎迫切喊出了声。
“孩子也流产了,子宫也摘了,可是,还是不行,癌细胞转移了。”
苏娅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两个女人表情沉痛,相对无言。同事走进来,看着这奇怪的场面,纳闷地问,“你们怎么了?”
苏娅说:“呃,没什么。”她起身收拾桌上的杂物,“我得请两天假,去一趟青州。”
苏娅与贾方方在青州一所医院见了最后一面。
春天的阳光很好,从窗外照进来,给房间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颜色。床头柜上放着一束鲜艳的康乃馨,那是苏娅来之前在花店买的。苏娅坐在病床前,努力做出平静的表情,看着贾方方。
贾方方背倚床头,她已经数日未进食,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她吃力地说:“苏娅,谢谢你来看我。”
“对我还要这么客气吗?”
“苏娅,你没有变,和以前一样漂亮。我变了吧,我变得很丑了吧。”贾方方自嘲地笑一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捋头发。她忘记了,她的头发已经剪成小寸头,而且还戴着顶薄帽。
“不,你不丑,你和从前一样好看。”苏娅说的是真心话,除了瘦,贾方方并没有被病魔折磨得太过难堪,她依然眉清目秀,她是一个病美人。“贾方方,你知道吗?我经常梦到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梦到你。在梦里,你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扎着两只小辫,在我家楼下喊我的名字,苏娅,苏娅,一直不停地叫,我答应着,连忙跑下楼。这个时候,我就醒了。每次醒来,都很恼火,恼火梦太短,为什么要醒呢。我就闭着眼,使劲闭着眼,想再回到梦里。有时候,真得又回去了,继续梦下去,我梦到我们在山上摘桃花,采红叶,你还记得我们用红叶做的书签吗?我们在红叶上写诗句,我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雁归来’。你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一枚……”
贾方方静静地听着苏娅的讲述,她微笑着,思绪跟着记忆回到了少年,回到了童年。“苏娅,你知道吗?我一直都惦记着你,桐城有我们家的亲戚,我每年都要回去的,可是却从没有去找你。时间越久,我越怕见到你,我怕我们无话可说,我怕见面会破坏从前的回忆。如果那样,我宁愿不见你。”
“我知道,我明白。”苏娅忍不住哽咽了,她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呢。她是懂她的,正如她也懂得她一样。
贾方方说:“苏娅,你不要为我难过,命运是个强大的东西,谁也打不到它,一切都得听命于它。”
苏娅忽然失声哭了出来,“你不听话,这几天,我总是想起你小时候。你不听话,来例假还吃冰激凌,还有,你还记得那次越野赛吗?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阻止你,你带着例假还去参加长跑,每次想起来,我就特别恨自己。”
“傻,你真傻,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的病真的是因为这些招惹来的,那也是我自找的,是我活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大学的时候我做过一次人流,是在一家私人诊所做的。我不知道我的病和那次粗糙的手术有没有关系。也许有,也许没有。别人也做过人流,别人怎么没得呢?所以,这是我的命,命该如此。
“苏娅,我们中间隔着一大段的空白,这么些年,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些什么,结婚了么?有孩子了没有?苏曼呢?你的母亲呢?他们都好吗?”
苏娅避实就虚地答:“我结婚了,有个孩子,苏曼他们,父母他们都好。”
贾方方欣慰地笑了,“苏娅,你知道吗?我一直对你充满担忧,你和我不一样,假如我们俩都是液体的话,我落进油里会变成油,落进水里会变成水,而你恰恰相反,你进了水里就是一滴油,进了油里反而会变成水。”
苏娅说:“你这个比喻很新鲜,也很形象,不过,你放心,无论是水还是油,无论我与这个世界如何格格不入,我都会闭着眼睛,很好地生活下去,你不用为我担心。”
夜幕降临,苏娅与贾方方告别了,从青州开往桐城的火车有一趟是八点四十的,贾东东给她买的正是这趟车的车票。第二天还要上班,她必须当晚赶回去。
从病房出来,苏娅的眼泪就落个没完,一路走,一路流,像干涸了多年的泉眼,突然一下子源源不断地倾流而出。进了火车站的侯车大厅,手里拿着车票,排队进站。她的眼泪仍在淌个不停,她任由它们流下来,象一串串水珠,打湿嘴角,打湿衣襟。有人纳闷好奇地看着她--这个女人究竟含了多大的哀伤,眼泪会落得如此悲恸。
哭过这一场,苏娅知道,她终于彻底地失去贾方方了。这是和过去的一次突然遭际,一次重逢,也是最后一次的告别。苏娅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