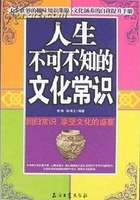2008年7月8日,下午8点36分,我坐上了从成都开往拉萨的T22次列车。
7月9日这天,列车翻过秦岭之后,又经过了宝鸡、天水、兰州、西宁等站点。晚7点过,开始在广阔的草原上行驶。这时候,收到朋友色波发来的一个短信,问我们过青海湖没有?我回复说,还没有,但可能快了。晚8点,果然就看见了青海湖。但火车距离湖面很远,连湖的形状都显示不出来,只看见天际一线发光的湖水。
从成都到西宁这一段是不能算作青藏铁路的。青藏铁路的起始点在西宁。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才算是真正迈上了青藏铁路的旅程。
2008年7月10日凌晨两点半,火车在格尔木站停留了数分钟,然后驶入黑暗中的荒原,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无人区。尽管我知道,火车的目的地是拉萨;我也毫不怀疑,火车的行驶是安全的。但是,当我撩开车窗的窗帘,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原野,尤其原野之上那些由星星组合而成的怪异、阴森的图案,心里竟然隐隐的感受到一丝恐惧。这样的景象我没敢看得太久。放下窗帘,躺在卧铺上,想了一些混乱而抽象的问题(其中多次回想起年初就开始阅读的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之书》),于不知不觉中睡去。
又是同车厢的几个中老年妇女的说话声将我吵醒。我一看时间,又是凌晨7点过一点。吵嚷声中,频繁出现的就是“藏羚羊”三个字。不用说,火车已进入著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虽是第一次走青藏线,但我对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并不陌生。许多年前,我就看过一部名叫《平衡》的纪录片。该片编导名叫彭辉,是我的朋友。他为了拍摄这部围绕可可西里盗猎和反盗猎藏羚羊的故事,几年中多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与前后两任反盗猎的“野牦牛队”队长成为了朋友。我也是通过这部片子,第一次知道了可可西里这个地方,第一次了解到藏羚羊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整部影片的调子是悲壮的。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是耐人寻味的。后来一位名叫陆川的电影导演受到这部纪录片的启发,拍了一部故事片,片名就叫《可可西里》。影片中的那个记者,就有彭辉的影子。这部故事片我也看了,在近年来的国产片中算是不错的。但我总觉得,故事片给人的震撼,还是不如纪录片。我想,可能还不是因为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而是两者思考的角度不一样。毫无疑问,我更倾向于彭辉的角度。所谓“平衡”,让我们感受到的则是现实之中有太多难以平衡的矛盾。
也许是我们这趟列车的乘客太幸运?也许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真的多了起来?总之,我们确实在广袤的原野上看见了藏羚羊。有时是几只,有时甚至成群结队。车厢里的男女老少挤在窗户边,神情均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还有多人拿出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我知道拍摄者不过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为距离那么远,火车的速度又那么快,依我的摄影经验,这样的拍摄注定是徒劳的。
在我的邻铺,是一位带着外孙女的农村妇女。小女孩只有两岁。她们坐上这趟列车,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探亲。小女孩的母亲在西藏那曲,父亲是驻那曲的一名军人。小女孩有点感冒,时不时咳嗽,并喜欢哭闹,在车厢里很不安分。农村妇女显得有点心烦,对女孩的哭闹除了呵斥,似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刚在成都上车的时候,车厢里很热。过后开了冷气,就凉了起来。我们告诉她,应该给小女孩换上长衣长裤(当时小女孩还穿着一条露手露脚的裙子)。农村妇女便拖出一只旅行包,在里面寻找替换的衣裤。旅行包十分陈旧,甚至还有些破烂,是那种十多元钱的廉价货。旅行包里面的衣物,其质地和成色也是比较粗糙和陈旧的。到吃饭的时候,她拿出自带的一盒方便泡饭冲了开水,喂给女孩吃。女孩吃了几口,显然对这方便泡饭没什么胃口,开始哭闹。然后,她又拿出一只奶瓶和一包奶粉,将奶粉倒进奶瓶,冲了开水,待冷却一下之后,让女孩自己抱着奶瓶吸。她的表情疲惫而木讷。她显然也没出过远门,并且不识字。当列车员来验车票和索要一份旅客必填的健康说明书的时候,她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零碎物品,不知道哪一样东西是列车员需要的。在将要到那曲的时候,她请我们送她下车。因为,她除了一只旅行包,一只方便袋,还有一口沉重的人造革的旅行箱。我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她。为此,我们错过了去餐车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坐在卧铺车厢里,和她一道等候着那曲站的到来。但是火车晚点了,预计中午12点15分到达那曲站,结果延迟到中午一点半才到达。我帮着她将旅行箱提下火车的时候,感觉站台上的气温要比火车上低十多度,吹在身上的风有点刺骨,呼吸也显得困难了一些(那曲站站牌显示,其海拔为4513米)。目送她们走出站台,我担心着小女孩的病是否会因为高原的气候而加重?
火车过了那曲,车厢里的乘客明显地少了一些。车厢外的风景较之以前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是那么荒无人烟的了,不时有村落从眼前一晃而过,树木也开始多了起来。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我们离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拉萨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