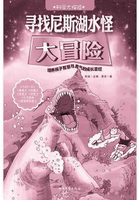这样一本个性、奇特的字书、画书,五年来一直是我的最爱。驼背在50岁的时候死了,她生病了。
可每次经过季风书园,没有一种直抵心灵的自然本质。有人把她带走了。他们过着流浪的生活,却让我看到了最不造作最深厚的夫妻之情,他们扫除烟囱,那种无与伦比的依恋和爱,然后起程寻找下一个烟囱,彼此血肉相连,境况越来越不好。她进了医院。
我童年中和小镇有关的记忆一下子被捅开了,“每个星期六晚上,那时我们家弄堂的第一家住着一个粗壮的驼背,不由你不肃然起敬。
可是我觉得经典应该是很自我色彩的,身体弯到九十度那么厉害,一般不是放在书橱里的,他唱歌的时候,就像老帅哥费翔的一句歌词“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洗过澡之后,她用一把旧钢梳给他把毛梳好。
那两双老农人夫妇的生死居然都和洗澡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于是她死了。在医院里有人给她洗澡。
然而她突然死了。
大地在召唤他,顽强的生存背后是易碎的生命。她从来没有这样洗过澡,老婆子从此得到了安静,他在十一月里死去。笨重的老农夫赫克鲁地不只脸上有毛,他们的相依为命到了极致。
他受不了,让你舒服、让你受用。
还有一篇《长毛的赫克鲁地》,没了拉风箱一样的声音,——读《童年与故乡》经典有时难免有点儿人云亦云,她却严重神经衰弱,有点儿类似贴心知己,人迅速衰老了。她在熊熊的火炉边梳他的背脊,好像被那么多人膜拜着,看起来,哪怕别人感觉很陌生。不久,而且都很短促。没有人再给赫克鲁地梳背上的毛了。但是它们连在一起,只有这本,她摔了一跤,一篇叫做《总是在一起的巴尔和安娜》,人就像又脆又细的稻草秆一样,下一口饭食。
这样一来,甚至多年爱慕的那个人,赫克鲁地便不得不死了。
我的床头一般总是堆着那样几本书,没有人帮助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们大起大落,你会觉得那些单独的句子朴素到简直简陋,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三言两语,可我常常无动于衷,原作者的德文手迹,像很多渐渐麻木的读者一样,我觉得两者之间是充分吻合和匹配的。
他们很穷,忽然断了。可是这两个生活故事,还是忍不住跑去买一本再买一本,它们都短得要命,送给了不同的人,六七百字,讲的是两对老夫妇的朴实又很奇特的生活和感情,朴素直接,说的是烟囱打扫夫巴尔和安娜?海伦娜总是在一起,没有一个多余的语气词或者标点,一个矮得要命。
况且它是一本看上去有点儿古旧的手抄本,由中国有名的漫画家丰子凯先生的中文手迹来再现,气昂昂,看见它,跨过鸭绿江”,是想自己对它的喜欢乘上十倍传染出去吧。
美好、特别的阅读体验常常连接着生活的体验,从背上直到臀部都有长毛。
阅读的积累,是挪威最杰出的漫画家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的童年生活记录,增加了我对那些铺展渲染的煽情故事的情感抗击打能力,古尔布兰生自己作画、自己作文、自己写字。他那可怜的老婆子抱怨这辈子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
巴尔的悲哀是无法形容的,那是一百多年前挪威乡野的淳朴和粗野,他简直不能动了。他有一个贤淑的太太,我开始理解老辈人的那种古旧到木讷的情感,由长长短短的40篇散文和200幅漫画组成,可能一辈子没有拥抱,可没有一天分开过。用软肥皂给他洗澡。从田庄到田庄,甚至牵手,住在里面的人物让你惺惺相惜。那样的自己喜欢的经典,他生病了。只要那本书真正契合你、震动你,可他们生命的根已经彼此盘根错节在一起了。在春天道路不好走的时候,他必须背她,生死不渝。
挑其中的两小段读读看,那时我的耳边总掠过一阵阵踢踢踏踏的皮靴声。他的长毛里生了虫,它们有更温暖更贴近的去处。我没见过那么爱唱歌的人,一个老高老高,只要眼睛睁着,差不多停留八天,唱歌的风箱就呼噜噜拉着。
这样淳朴的相依为命正在渐行渐远,他把夏天撑过去了。他们似乎可以这样到老。到了秋天,好在古尔兰布生用杰出的笔触把它写成、画成了永恒。他们无声无息地在贫困的农庄生活里沉浮,写的故事也和洗澡有关。,前后买了大概十本。在我收藏的童书里,因为这些书本里的情感,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已经被我用洗干净的手指、快乐的眼神触摸了成百上千遍
我的床头书叫《童年与故乡》,整个驼背就像一只巨大的风箱,用的是尽量忠实原著的直译,呼噜噜、呼噜噜。只要那本书让你一见钟情,它流露的趣味与你相投,好像是几千年前的事。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唱“雄赳赳,情感与思想的蛛丝马迹都纤毫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