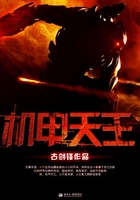除开三毛,又有几个女孩真正能独自浪迹天涯,千山万水都行遍呢?
不用遗憾的,有些一直渴慕仰望却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不求形似但求神似,来个不谋而合、默默契合。有那一份精神的自由和底质,一个人,在内心里也可以走遍天涯的。
这样一种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走的梦想和快乐,该有一个最好的去处——城市的铁轨,它们与无穷和无数的远方连接着,互相渗透着。
人在黄昏里动,我爱在锃亮的、长长的铁轨上,在微冷的尚有余温的光线里走。
铁轨是这样一个无限延伸的场景,只要愿意,仿佛可以走向任何一个想要到达的地方。
很多年以前,一个男孩走在铁轨上。
男孩家里几间矮矮的平房,离铁轨很近。火车开过,男孩的床就一阵阵摇晃,像地震一样。十几岁的男孩有时会在黑夜里,在摇晃中突然睁开眼睛,很郑重地思索起将来。听着火车车轮咔嗒咔嗒辗过铁轨的声音,听着在夜空中显得无比清远的汽笛声,男孩一阵阵激动,好像自己上了火车,正驶向某一个还不甚清晰的神秘的地方。男孩知道自己肯定不会一辈子住在这几间旧平房里,他的未来在远方。
在木板床上咯吱咯吱地翻身,男孩的脑子转啊转,这一列火车会开到哪里去?会开到深山老林里去吗?会开到冰天雪地里去吗?会开到北京、广州还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有多远啊,远在天边吗?
那时,城市里流行着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男孩和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男孩一样,整天哼着电影里的歌——“阿巴拉布,到处流浪。哦——到处流浪…
…”放学后,沿着铁轨,一路滚着铁环,一路哼着“阿巴拉布,到处流浪”,一路小跑回家。滚铁环是当时男孩们的游戏,用一根长铁钩一路有技巧地拨着铁环向前推进。
男孩是滚铁环的好手,圆圆的铁环滚动在窄窄的铁轨面上,当当当,当当当,不大掉得下来。男孩拨着这个“小轮子”欢快地前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司机,坐在火车头里,驾着长长、长长的一列车,到达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远远的红红的夕阳就挂在林梢。
有时,远远的,听到火车声,男孩灵巧地一跳,跳到铁轨边的菜地里。火车呼啸而来,呼呼生风,刮起了男孩的发和衣襟。男孩看不清车厢里一张张一闪而过的面容,心中只掠过一阵模模糊糊的激动。
上学、放学,男孩无数次走在铁轨上,他多么熟悉每一根枕木、每一块基石,他可以闭着眼睛,在一格格基石上疾步行走。铁轨上一个人也没有,早上的太阳送他走,傍晚的太阳迎向他。铁轨锃锃发亮,无限地向前延伸。男孩张开双臂,学着飞机超低空飞行的样子,唔——唔——,孤单、欢腾地向前飞奔。
长大后,男孩考取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地理系。毕业后,他来到一所郊县的古老中学做老师。他无数次地回想起一个男孩走在铁轨上的场景,回想起自己就是这样长大的,走在铁轨上,心里装满梦想和激情,向前健步如飞。
他一直住在这座县城里,很少出门,最远的,到了海南岛。做地理老师的他说:
“我到过‘天涯’和‘海角’了。”底下坐着的一个女学生不以为然,三毛的妙笔生花,让她目眩神迷地向往远方,向往一直走到整个世界的天涯海角。她留长发,喝凉水,赤脚穿跑鞋……她跑去问他撒哈拉沙漠、加纳利群岛、古斯、玻利维亚等等一大串地名,求他讲得越详细越好,包括去的路线和航班,仿佛她已经下好了最坚定的决心,出发的日子指日可待。
一个个地,他讲给她听,尽他所能和所知,有的地方他说:“我也不大知道,不过我可以回去替你查查。航班和路线,我不知道,你那么急着要出发吗?”“大概,会很可能……很快的。”女生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检讨自己把航向定得太不可知。“不过,沙漠一定要去的!”想到三毛坐在汽车轮胎做成的圈椅里,像个印第安女王,女生就渴望得要命。
“一个人,在内心里也是可以走遍天涯的。”他半靠在讲台上,地球仪在手边,轻轻一拨,整个地球就在他手心里转来转去。
那个女生当然没有去成撒哈拉,希望的可能性实在渺茫。那个走在铁轨上的男孩,那个长大后做了地理老师的男孩,讲的那句话,却一直一直留在她心里——一个人,在内心里也是可以走遍天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