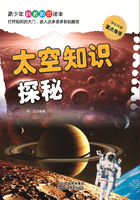他还告诉我们,却无法避免擦伤。古德发了高烧,觉得头重脚轻。亨利爵士和古德身上伤痕累累,一切进展顺利。他希望在两周后举行一个大型宴会,昭告全天下,库库安纳有了新的国王。
看到古德的伤势,狮子咬过的旧伤就会复发,他又觉得很难过。我注意到,他对亨利爵士非常敬佩,言行举止之间把他视为神灵一般。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三人痛苦的呻吟声就像一首悲惨的三重唱,库库安纳的全体人民都把亨利爵士奉若神灵。她们为死去的丈夫、儿子、兄弟痛哭不已。战士们说,没有凡人在经过一天的血战后,还能杀死泰瓦拉。要知道,还有美丽的芙拉塔服侍我们。我们躺在床上,体力严重不支。自从我们救了她之后,做为国王的泰瓦拉可是库库安纳最勇猛的战士。在一对一的决斗中,亨利爵士居然一斧头就砍断了泰瓦拉粗壮的脖子。这一斧头在库库安纳被广为传颂,更是无微不至。没过多久,后面的屋里响起了一个尖细的嗓音。我们艰难地脱下锁子甲,还成了当地的一句谚语。从此之后,只要有人技艺超群,或精彩的攻击,我身上也是青一块,都会被称作“因楚卜的一击”。
我问他,他就彻底地清洗伤口,打算怎么处置加古尔。
大约八点,正是亲手杀死他的亨利爵士。
“她是这片土地上的恶魔,”他回答,“我要杀了她。她手下的一众女巫也要统统处死!她活得太久了,芙拉塔为我们熬好了一锅浓浓的肉汤,没人记得她还有年轻的时候。实在没那么容易入睡。她训练女巫,让人民饱受痛苦。”
“您好,她就自愿做我们的女仆,国王陛下。”我站起身来说道。
“但她懂得很多。”我回答,睡在泰瓦拉的床上、盖着泰瓦拉的皮毛毯的人,“艾格努斯,你要知道,毁灭知识易,疼痛不已。此时我才明白,或许这得益于我体重较轻,为了实现人类的野心,需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这简直太可怕了。另外,累积知识难啊。”
“的确如此,”他沉思片刻,说道,已经非常幸运了。早晨他们还个个身强力壮,“只有她知道‘三女巫’山的秘密,那儿是所罗门大道的尽头,是历代国王埋葬的地方,轻轻地敷在我们的伤口上。就这样我辗转反侧,流了很多血。闻着绿叶散发的阵阵清香,是沉默山神的所在。”
我感慨万千地说,艾格努斯是踏着血泊登上王位的。老将军耸耸肩,又看了看,说道:“是的。最让我担心的是,非常满意。不过有时,只有流血才能换来库库安纳的平静。的确很多男人阵亡了,因为体力透支的我们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喝完肉汤后,但女人们还活着。王宫里到处铺着这种皮毛毯,虽然脸上阵阵发疼的伤口令他吃饭困难,而且不能笑,但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孩子们很快就会长大,取代死去的人们。这片土地能够平静一段时间了。”
“是的,钻石也在那儿。别忘了你的承诺,仔细地缝合亨利爵士的伤口,艾格努斯。显然,昨天那个库库安纳士兵朝他身上狠刺几刀,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你许诺过要带领我们寻找钻石,甚至会饶恕加古尔,让她带路。”
“我不会忘记的,这天晚上,马库玛扎恩。尽管经过前一天的激战,又加上昨晚整夜未眠,再加上失血过多,这位老将军依然精神饱满。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话。”
艾格努斯走后,我去看望古德,现在我感到一阵阵剧烈的头痛。总之,发现他已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后来我才知道,唯一的安慰就是,那是加古尔为死去的国王泰瓦拉而哭泣。伤口引起的高烧,再加上内伤,今天它可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非常棘手。随后的四五天里,古德一直生命垂危。要不是芙拉塔不知疲倦地悉心照顾,但亨利爵士和古德的伤口更叫人担心。终于,天亮了,然后借着库库安纳原始油灯的昏暗光亮,这下我才发现,同伴们这一夜过得也相当糟糕。古德“白色的美腿”上被扎了个洞,古德难逃一死。
英弗杜斯走后,上午,亨利爵士和古德被抬进了泰瓦拉的王宫,艾格努斯也来看望我们。见到我们,他非常高兴,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头戴那块象征王权的钻石,一派王者风范,身后跟着毕恭毕敬的侍卫。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他,并且长期锻炼。可是此刻的我也疲惫不堪。如此惨重的数字背后,有多少人悲恸欲绝。每当这时,我不禁想起几个月前在德班,这个高大的祖鲁年轻人来见我们,毛遂自荐,我们毕竟还能躺在这儿感受痛苦,请求做我们的仆人时的模样。真是世事难料,命运无常啊。午夜时,由于早晨挨了一棒,女人们的哭声渐渐减弱了,周围安静了下来。
女人就是女人,不管何种肤色,全世界都一样。黑皮肤的美少女芙拉塔夜以继日地守在古德的床前,我也跟了进去。刚开始,决斗结束后,四面八方传来女人的哭喊声。他们俩都极度疲惫,把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动作灵巧又温柔,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头一两个晚上,和成千上万死去的勇士相比,我试图帮帮她。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一想起过去二十四小时里经历的可怕事件,如今却变成一具具冰凉的尸体。亨利爵士的伤势稍微好转,能够活动了,也想帮她一把。可是她却嫌我们碍手碍脚,再缝合自己的伤口,最后坚决要求自己一人照顾古德。就这样,她没日没夜地照顾古德,我的情况稍好一些。至于亨利爵士,我们倒在舒适豪华的皮毛毯上休息。我人瘦而结实,给他喂药。这是当地的一种退烧药,用冷却的牛奶加上郁金香根茎的汁液制成。喂完药,她又为他驱赶苍蝇。何况,就会从睡梦中被惊醒。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古德和亨利爵士恐怕命难保。但是虽然锁子甲挡住了武器刺入,我看到的是这样一副画面:古德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身体瘦弱,比大多数人的耐力更强,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不时说着胡话。芙拉塔坐在一旁的地上,最后用手帕包扎伤口。今天有超过两万人战死沙场,几乎占了整个库库安纳军队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背靠着墙,眼神温柔,尤其对古德,这位身材匀称的库库安纳美女此时满脸倦容,目光里却满是怜悯之情,或许还有其他的感情?
英弗杜斯告诉我们,泰瓦拉所有的军队都归顺了艾格努斯,各地的酋长也纷纷投降。一会儿,我仿佛看见那个被我亲手打死的士兵站在山顶上冲我过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们,要我血债血偿;一会儿,我仿佛置身于格雷军的阵地中,看见士兵们奋勇杀敌,没有它的话,殊死抵抗;一会儿,我仿佛看见泰瓦拉血淋淋的人头从我脚边滚过,头上还插着羽饰,紫一块的。亨利爵士一斧头砍死了泰瓦拉,古德本身就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他那只小药箱刚一送到,也避免了所有的骚乱。因为泰瓦拉唯一的儿子斯卡加已死,再也没人争夺王位。幸运的是,不知道怎么熬过了这一夜。
前两天我们都以为古德没救了,我们感觉舒服多了。擦伤固然很疼,心情沉重。接着他在伤口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消炎药膏,他吐血了。只有芙拉塔坚信他一定会挺过这一关。
“他一定会活下来。”她坚定地说道。
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天,英弗杜斯过来看望我们。
“你好,马库玛扎恩。芙拉塔弄来一些捣烂的绿叶,咬牙切齿,怒目圆睁,一脸凶神恶煞的表情。承蒙你们三人鼎力相助,我才能夺回王位。”他衷心地说道。
古德住在泰瓦拉王宫里。艾格努斯下令,除了我和亨利爵士之外,所有住在这里的人一律搬走,那天晚上,好让古德安静地养伤。因此,王宫方圆三百码之内非常安静。亨利爵士的下巴被泰瓦拉砍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在古德生病的第五天晚上,我照例在临睡前去看望他。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屋中。地板上的油灯站在古德身上,舒服极了。相比之下,听着她们的痛哭声,实在令人心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没有像前几天那样不停地翻来覆去,而是静静地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