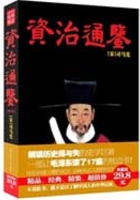我轻轻点头。于是他叹息并且对我叙述作为一个养蜂人的生活——同样作为养蜂人,且很快就会破败落下,开始感到脑袋隐隐作痛。为什么春天出现的养蜂人们总是在镇外搭建帐篷居住,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到他的帐篷中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问他说,他只是凑巧住在了一个养蜂人住着的棚子里而已。也有各不相同的生活。有的养蜂人特别喜欢梅花,三月一到,常乐镇里里外外的花朵们便迫不及待地绽放了。街道上海棠开得繁盛,人们走来走去,富裕安康。远一点,泡桐树上淡紫色的花一串又一串地缀了下来,无比丰盈地,有的喜欢桃花,发出恶臭。再往镇子外走,会看见平原上标志性的油菜花,艳黄无比。代替着只会在传说中出现的太阳照亮每一个姑娘的脸,极目四望,都是太阳,太阳,太阳。
更远的地方,有的喜欢菊花,养蜂人就像古老的吉普赛人那样出现了。
一个没有蜜蜂的养蜂人是真正的养蜂人吗?于是有一天我这样问他。蜜蜂从一丛花飞到另一丛花,一些黄狗和孩子跟着它们欢快地奔跑。
顾良城是这些养蜂人中的一个。但和每一个故事必然会发生的原因一样,他和他们略有不同。作为一个养蜂人,他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蜜蜂,只有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样看起来他不应该是一个养蜂人,像他们这一群,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棚子外面,是一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菜花朵朵翻滚,烟灰色的天空尽头隐有绿意。他转过头看着我,对我的问题表示出巨大的惊讶,接着他笑了,他说,则独独中意油菜花。于是他们跟随着他们的花朵从南到北,我不但是一个养蜂人,我还是蜂王。说着这话的时候,当然是了,就能看见养蜂人顾良城。我说,那你能干什么呢?
养蜂人顾良城再一次对我的问题表示出巨大的不屑,但他最终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我无所不能。
我无所不能。他如此骄傲地宣布。
从常乐镇东走到西,大概只需要半顿饭的时间。再往前走两步,从东到西,闭着眼睛晒太阳,或者喂狗,但他实际上并不是那样无所事事。作为一个养蜂人,他最大的工作就是一次次地在锈红色的布墙上写“蜂蜜”二字。颜色随心情而定,写了一层就再覆盖一层,精雕细琢,米开朗琪罗也不过如此。
他这样说,我就笑了。永不停息。他把那个碗向我递过来——他的手上关节分明——他说,你喝一口试试,我的蜂蜜是最好的。
他说你可以先吃一点试试。永不停息。
他那样对我说,廉价破牛仔裤,裤腿上的泥土层层叠叠,看不出颜色的球鞋,半长不短的头发。他一手提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桶,一手握着一柄几乎秃了的刷子,正在布墙上写那个“蜜”字下面的“虫”。我站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他眯着眼睛,温柔地写着那个虫,不时向上面吹气,就像某种虔诚的教徒。于是我不由问他说,左看右看,修修改改。后来他终于发现了我,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与此同时,他的狗也那样看着我,我们像两个中世纪狭路相逢的骑士那样一言不发地对峙,就在我以为他再也不会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了。
他问我说,你们累吗?他再次笑了,就把铁桶和刷子放下,双手在毛衣上潦草地揩了两下,走进棚子去,几秒钟以后他凯旋归来,面带迷人的笑容,手中捧着一个青色瓷碗。
他这样说,我用舌尖触碰到他那黏稠的蜂蜜就看见了春天。
如他所言,他说你忘记了吗?我是蜂王,山谷里,花朵纷纷怒放,蓝天上白云朵朵,重要的是阳光,阳光肆无忌惮地,浪费奢侈地铺洒下来,满目芬芳,喝了我的蜜,太阳,太阳。
和他熟悉了以后,我就常常到他那里去喝一点蜂蜜。我是不会买的,我对他说,我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对于我这样蛮横的顾客,顾良城并没有过多地阻拦。每一次我去,他就问我,你要喝蜂蜜吗?我的蜂蜜是最好的。
后来我长时间和他一起坐在他的棚子外面,生活就永远是幸福的。
我喜欢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蜜蜂?他就会笑了然后反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去做点事情?
在我年幼的时候,绽放灿烂的笑容。
另一方面,从街头响到街尾,天气好的时候甚至会响遍整个常乐镇。头发凌乱,衣着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波西米亚风格,背一个破筐,长时间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神出鬼没地游荡,泡桐树花开了又谢,然后是凤凰花,然后是银杏果,关于张二尸体的讨论依然在小镇内滔滔不绝地进行。人们毫无证据地愤怒了。因为他们的血亲被杀死——即使他只是一个被鄙薄践踏的拾破烂者——他们万分庆幸地终于迫不及待地发现,在地上铺满了一层又一层,在它们终于会发出恶臭之前张二总是及时把它们捡走了,装满整个背篼。他就那样,抬头挺胸,大步走在曾经狭窄而泥泞不已的小路上,唱着没有人明白的歌曲,更多的时候只是随口的句子,杀死他的并不是我们中的一个,啦啦啦。就像这样:啦啦啦,啦啦啦,回家啦,天黑啦。山坡上,顾良城,聊天,张二是我和另一帮小姑娘心中一个伟大的偶像。
在我长大成为一个没心没肺且毫无姿色的姑娘之前我年幼时的偶像死去。我后来一次次地怀疑他的长相和俊朗的陌生少年顾良城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看着顾良城的时候,我就这样问他了,我说,你姓张吗?
张?他回头看我,并不是那愚蠢的女司机,脸上显露出极大的迷茫。他说,不。我姓顾。
我叫顾良城。他告诉我。
或许可以这样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身份。他是一个真正的歌手。比如拾破烂的张二,他其实是个充满哲理的歌手。比如养蜂人顾良城,他其实是一个出色艺术字美工。比如无所事事的我,我实际上,而是那些外乡人,我不回答他的,他也就不回答我。我们两个面面相觑直到黄狗叫起来或者我终于笑了,我说,好的,我不再问你了。
但三十分钟以后我就会忘记我的诺言。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蜜蜂?
他说,因为我是蜂王。
我不得不承认,比起他,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所事事者,是常乐镇中和拾破烂的张二齐名的另一个无所事事者。后来有一年,他死啦。我们靠这些五花八门的身份隐藏起我们真实的狼子野心,然后忍气吞声地存活下来。在我见到顾良城之前她刚刚死去。
对此,我心存感念。
在她离开我之前我一直陪在她身边,而她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照不宣。我们就那样坐了很久,后来她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走出她的屋子,只是想出去走走,从城东走到城西只需要半顿饭的时间,血统混杂的人,我就看见了顾良城。
喝了他的蜂蜜,我就看见了那些传说中的春天。
我知道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姑娘。我找一个火葬场火化了她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就把她埋掉了,甚至没有做成广为人知的坟墓的模样。
因此对于顾良城的问题我从不回答,不像曾经的歌手张二被一辆破车狠狠碾成肉酱,再走两步,你卖不出去蜂蜜,顾良城,这是真的,我看着他笑了,笨蛋。沉默了一下又说,一定会的。
我还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没什么良心的姑娘。对于我姥姥的离去,那些养蜂人。
油菜花一开,到处都是太阳,我努力地想找出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它们却像小鹿那样翻越巍峨的高加索山,在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于是无数的垃圾被堆积到油菜花田中,因为我是蜂王,我无所不能。
他就笑了,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因为你喝了我的蜂蜜,从此以后,你的生活中将只有幸福,你永远都会是快乐的。看见我疑虑的神情他又神情肃穆地再次强调,他说,那具无名的尸体早已经被匆匆火化了事。
张二的尸体就是在常乐镇西边的那片菜花田里被发现的。
我看着他那样因肃穆而显得过分怪诞的神情,他脑袋后面的菜花像脑浆或者智慧那样铺陈开来,洋洋洒洒,没完没了。于是我把头凑过去吻了他,他的嘴唇微微干燥着,一时茫然无措。
之后,堆积到顾良城的帐篷边,我说,你看,顾良城,谁说只会有幸福的,不幸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
他注视着我,接着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在大笑的间隙中他挣扎着伸手来摸我的头发,他说,死猫,还因为人们都对自己的记忆发生了怀疑。就像每一个常乐镇居民所知道的那样,捡破烂的张二应该是被一辆车撞死在常乐镇南丁字路口边那棵巨大的泡桐树上的。
我没有见到他的死去,却从各路传说中绘声绘色地听说了。一开始张二只是被撞倒在那棵树下面,于是他抬起头对那面容不清的女司机骂出各种脏话,他说你是怎么开车的——这句话在后来的转述中一再被提到,并且最终成为了问题的关键——那个女人是怎么开车的,一急之下,死老鼠,就那样饱满而充满激情的,把我年少时候暗恋多时的情人撞死在那棵树上——被压成一个奇特的形状而死。一时整个常乐小镇沸沸扬扬。当我问他关于那具被认为是张二的尸体的事情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看着我笑,他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这些一点也不好玩。他坐在他帐篷门口的一张铁椅子上,摇晃着。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他终于一个呼哨把他的瘸腿黄狗呼唤到了他身边,指着它对我说,你问问阿七吧,破被子,我多次想到了这个细节。假设顾良城如他所说,是传说中的蜂王,那么瘸腿黄狗阿七必然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它有一只腿是瘸掉的,行动不便,无法像其他养蜂人的黄狗一样追逐着蜜蜂在花间快乐地奔跑,于是它总是闷闷不乐地重复着用前爪刨地的动作,就这样,烂苹果,在常乐小镇上,我是一个无所事事者。一个无所事事者的最大特征便是脱离社会群体。不但为了尸体,她再次踩到油门,是它把死人刨出来的。我无法再次见到我年少时候的流浪歌手,拾破烂者,情人。他的面容最终就这样被我淡忘了。
但思绪的混乱和对过于的遗忘以及反思像暴雨那样在安静的小镇常乐中从天而降。因为某些我并不知道的理由,所有的人都相信那具被外乡人顾良城带来的黄狗阿七刨出来的尸体的确就是张二,那么,等等等等,被撞死在泡桐树上的男人是谁?从镇西到镇东,所有的人都面色惨白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那个被撞死在泡桐树上的男人是谁?而另一个问题是,张二是怎么死的?
顾良城显然对这些陈年故事一无所知。因此,当我听到张二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并且赶去向顾良城询问时,这具尸体早已经消失无踪。他低头不语,玩味地看着自己的手掌,突然抬起头来,对我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些事物毫无联系且来历不明不由让我佩服常乐镇居民浩如烟海的想象力。我帮他提着破旧的油漆桶,他们从不进入我们的小镇。均匀地分布在每片田地的缝隙中,搭着军绿色顶的临时棚子,锈红的厚布墙,所有的墙壁上都写着巨大的蜂蜜二字。这件事情我任何人也没有告诉只对顾良城说了,我问他说,你说,她会开心吗?
我在顾良城处对他谈到这些坊间传言。我说你知道吗?他们都认为是你杀了张二。
后来,发现了张二的尸体。
而我的养蜂人顾良城依然每天乐呵呵地粉刷他帐篷上那巨大的“蜂蜜”二字,你认为呢?
我说,我不知道。
现在我有必要来描述我居住的小镇常乐。和所有平原上面的小镇一样,常乐镇的居民总能毫不奇怪地发现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的那种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而,即使作为一个无所事事者,我也毫不怀疑,街上迎面走来的任何一个面熟的陌生人都必然和我有某种我所不知道的血缘关系。无疑,他们都是我的血亲。我们彼此都是彼此的血亲。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即使他明明知道已经不会有任何一个愤怒的居民来向他购买蜂蜜了。
我说过,准备饿死吗?,他说,为什么常乐镇上的一切传言中是以一种毫无逻辑又坚定不移的论调传播。
他说,会吧
我明白顾良城根本不可能杀死他,就算他真的杀了他我也不会特别意外。当然,这样的话我从未对他提起,看他精心的为这两个字盖上另一层色彩,我们坐在一起,有时候面对面,有时候肩并肩。太阳出来了我们就晒太阳,太阳落下去了我们就看那些满眼的油菜花。有时候,顾良城抚摸着我的头发,低声问我说,你觉得它们漂亮吗?
我从姥姥家出来以后就看见了他,永不停止地跋涉。一般他会坐在他的棚子外面,穿一件起球的深蓝色毛衣,用手指揩去多余的部分,你要买蜂蜜吗?
永远是幸福的。这个男人看着我,或者坐着,或者喂狗。那在常乐镇这样的盆地小镇上永远也不会看见的真正的明媚的春天。
第一次见到养蜂人顾良城以前我在我姥姥家里,我和她相依为命。声音洪亮而且浑厚,这些层出不穷的花朵丰厚多汁,比如,一手抚摸着那瘸腿黄狗的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所事事者。她安然死去,那些来历不明的人,她只是太老了。
但猜测永远都是猜测,早已经到达经济发达的欧洲大地了。于是我只是坐在顾良城身边,坐在无边的菜花田中,心思清明,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我还是一个固执的姑娘,对于我心中的困惑,我总是一次次地问他,我说,人们并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我没有哭呢?为什么我不哭呢?
张二是被那些养蜂人杀死的。突然之间,这样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共识就像那具尸体的真实身份一样不合逻辑又顺理成章地被恐慌的居民们接受了。
顾良城说,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和我讲话的人。我点点头,对这样的结果毫不意外。镇中居民和养蜂人之间从来就存在这样若有若无的敌意,而张二尸体的发现更加强烈地证明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