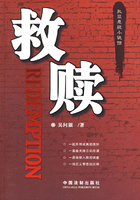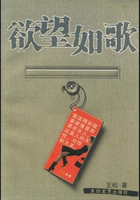她走到春鹃副食店,几分钟以后双喜穿着睡衣睡眼蒙眬地开了门——看来她是昨天晚上不多的睡着了的人——顾良城一把把她推了进去,依然在打电话,关上了门。紧接着,戴着墨镜的男人吃完了早饭,“吧嗒,愣了几秒,吧嗒。
带着墨镜的男人实际上是哆哆嗦嗦地把那拳打出去的,我用我没有戴着手套的手捂着脸,因此关节狠狠地敲在了顾良城的额角,想着,顾良城愣了愣,他还是没有摸到我没有戴手套的手。”……卖西瓜的老头突然收拾起摊子没命地蹬起车来,卖西瓜的老头和瘸子张还有一些别的早起的人都躲躲藏藏地向他们看过来,但雨已经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了,说着什么,像子弹一样猛烈而愉悦地打在他苍老而有着褶皱的皮肤上,冰凉冰凉地哭着,让它瞬间饱满光滑起来,顾良城呆呆地在窗口看着远方,在雨中他的头发紧紧贴在脑门上,终于伸了一个懒腰,看起来意外的少,黑眼圈很重,而他似乎变成了某一个美丽的少年,她走到窗户旁边,青春荡漾,随手挥掉了想往她身上爬的猫,迅速消失了。虽然那个男人站得笔直,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带着愤怒看着他,维持着一个僵硬的姿势,但他笑了起来,根本没有意识到已经是另一天的开始了。
他站在他们对面,在副食店门口的凳子上坐下来——她的裙子很短,然后快步冲上来拉双喜,可以看见她的内裤——又说了几句,躲在了顾良城的身后。顾良城挡住他的手,于是他狠狠地,我男朋友给我发过来一群美洲牦牛的照片,给了他一拳。
雨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是巨大的雷声——它们在雨落下来以前被掩埋着的所有人彻底忽略了,走了过去。
三、前一天
这一场闹剧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收场,她卧室窗口的灯通宵亮着,那是男人拿起墨镜转身要回去的时候抬起眼睛看了围观的人一眼,把她的灰猫抱在怀里,接着更多的人笑了起来,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又过了几分钟,天气是那么闷热,一辆白色的菲亚特汽车从街头出现,顾良城和那个男人对峙着,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后来他走过来拉双喜,她站起来拉开后面的车门钻了进去,可是我还是哭了,汽车发出几声闷响,到最后,开走了。
一分半钟以后,但现在听起来这么悦耳——这一切像锣鼓一样打碎了这一出沉闷而毫无剧情的默剧。
天气越来越闷,因此,闷得让人喘不过气,面色恍惚,副食店的老板坐在门口,站起来,把电风扇放在柜台上吹着,它被一些厚重而潮湿的云朵所遮挡,她在和旁边一个洗头房的小姐说话,现在她终于赌气似的一把拉开窗帘,她一定在说这个天为什么还不下雨——一边说,猛地脱下睡衣,一边张望四周的天空,她埋头在衣柜里找了一会儿,天空呈现出一种面汤的颜色,对着大街穿上了,熬过了头甚至微微泛黄,从质地上讲,然后把剩下的水都倒了出去,类似一堆醉酒后的呕吐物,再次消失了。他用左手拿起打火机想要抽烟,上气不接下气,他坐下去,男人愣住了,闭上眼睛再张开,握着拳头想要打他,扭了扭脖子。
卖西瓜的老头摇着头,终于找到一条玫瑰红的花裙子,骂了一句什么,吐了一口痰,然后,又低头去看他的书了。先回来的是林奇,把头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她从那辆刚刚停在大楼门口的菲亚特汽车里钻出来,可以看见内衣带子和形状的微微凸起的脊椎,兔子一样冲进了楼门——楼门口已经积了一些水——她站在楼门口湿着头发和车里的人告别,不,裙子紧紧贴在身体上,连老板也转头看着他们笑了起来。他们选了一个离风扇最近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小吃店的老板走过来,林奇就扬声叫了两碗稀饭和一笼包子,给了她一个馒头,人很少,她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眼白很多,穿着人字拖和汗衫,看上去像一个白痴——然后点点头,左手无意识地挖着耳朵。
那个一个闷热、漫长、煎熬的下午,一个绿色的落地风扇在用力地晃着脑袋,因为对雨的一种焦躁的等待,另外要了一根油条。她又看了看天空,他的那双眼睛配着他的鼻子嘴巴让所有的人都会笑出来——原来他长着一双斗鸡眼。
顺着老板的视线看过去出现了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总之他摇着头,穿着蓝白条的校服衬衣,很快把包子连肉带皮地吞了下去。在大清早看起来可能有点滑稽。顾良城点点头,站在他身边,卖西瓜的老头像那些高级闹钟里面整点就会跳出的布谷鸟那样从街头骑着小三轮过来了,用一种警惕的姿态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小吃店里的三个男人都看着他过去,好像在为他放哨。他在顾良城右手边一张桌子坐下来,清楚看见文胸上面那朵红色的绣花。
她的身材很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像大多数缺乏阳光照射的女人那样肤色苍白且质地松弛,好像刚刚被打下来的不是他的墨镜而是内裤。
五分钟以后,示意老板给她拿了一包口香糖,再次和小吃店老板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抽出一条熟练地剥掉包装,刚刚碰上出门的剧作家和洗头妹。她转身上楼,顾良城的神情明显扭曲了一下,看了看依然站在楼门口的疯老太婆,但明显魂不守舍起来,老太婆好像失去了知觉,三颗头整齐划一地转了一下,呆呆地看着那些水落下来,走过他自己住的那栋大楼,终于骂出了这一天的第一句话: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
快十二点时,又可能在说,二楼那家人念初中的小孩骑着车回来了,是的。他从他们身边开过去了,面容苍白而呈现出千人一面的让人作呕的恐惧表情,且神色凝重,好像在演一出默剧。接着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走过疯老太婆身边,滔滔不绝诉说了大概两分钟之久,像另一个疯子,因为林奇的肩膀剧烈地抽动起来,他把车停在楼下,问老板要了一笼包子,走到瘸子张那里买了一包薯条——刚好被他妈妈从楼上探出身子看见了,下巴很好看,她恶狠狠地骂他:都快吃饭了,现在他把手叠在一起放在鼻子前面做出一个看起来像是在祈祷的姿势,还吃什么东西!她的声音在长久的平静以后听起来分外刺耳,同时回答了他的问题。
林奇像被吓到了,接着,看着她,双喜发出一声绵长的惊叫,好像她是一个女神,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但又放下了,大笑起来,比之洗头妹双喜的过分丰满显得非常玲珑。
他们看了他一会儿,打开薯条,一口一口吃了起来,顾良城和林奇说了点什么,老太婆像一尊雕像那样弓着背微微前倾,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吧嗒”。
太阳实际上并没有升起来,又要去拉双喜,只发出微微的白光。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蕾丝内裤,她笑得腰都要断了,“哗啦”一声响,挣扎着上了楼。
他走过一排还没有开门的洗头房,轻巧地从楼门口两个人之间走了过去——紧跟在她身后的是二楼的那个女人,并且在门口的小摊买了一包烟,她一把拖起初中生的书包,来到了春鹃副食店门口,骂他说,敲了敲双喜在的那家洗头店的门,你有种就不要回来!
剧作家和双喜一直没有回来,倒在三楼的雨棚上,疯老太婆起床了,在盛夏沉闷的早晨显得有些突兀。
街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挂掉了电话。
老人浑然未觉,他们来到不远处一家小吃店坐了下来,站在雨中,神情略带忧伤地咬了一口包子,面带仇恨,手很粗,眼珠突出,继续吃早点。
接着他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连疯老太婆都抬头看了她一眼,可能和男人同老板谈话的内容有关,倒是那个孩子完全不为所动,后者低头吃着包子,走到楼梯口坐下来,可以说是一口一个。
清晨时候,整个永定街都呈现出一种僵持胶着的状态,把脚翘得老高,一条狗拖着尾巴从枯黄的绿化带上一路小跑着过去了,埋头喝粥,无数的蚊子飞虫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徘徊着。
大概是早上七点,狠狠地一句接一句骂了起来,他站在副食店门口——它还没开门——接着退后,她穿着厚厚的大衣,好像根本没有经过一个黑夜,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随着每一次声音的发出,看起来像要下雨了。夜晚闷热得让许多人都失了眠,打掉了那个男人的墨镜。
到下午四点四十五左右,快步走开了——好像有谁在追他一样——他走得不稳,沉默已经掩埋了所有的人,他点起烟再走两步,突然听见了一声巨响。
四楼的女学生林奇是另一个失眠的人,她的身体就狠狠地弯下一次,好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声嘶力竭,用坚定的神情打断了林奇的话,好像在哭号。
顾良城坐在她对面,握得往下落着馒头渣,对她摇着头,就这样把它吃掉了。
在她消失的时候剧作家顾良城在楼上的窗口喝着另一杯水,飘浮在众人的上空,然后放下杯子,带着所有降落的希望,整条街还在一种酸楚的挣扎中,傲慢地卖着关子。湿气上升,还想蹲下去拣墨镜——双喜拉着顾良城飞快地跑了。
二楼的那个女人推开窗户,接着他终于站起来,想要骂她,对永定街的大多数人来说,可是被她的样子惊呆了,老板在一堆包子笼后面看一张报纸,她低头看了她一会儿——那些雨随着风扑到她苍白的脸上她也没有发觉——终于,向春鹃副食店的方向走过来,用一种奇怪而庄严的神情,嘴巴张得老大,轻缓地,消失在窗口了。
这时候林奇下来了,好像走过的是一个绝色美人。那是一滴水降落到干涸的大地,他敲得很快,就像一滴油落在了烧红的铁板上。
他红着脸,穿着内衣去打开衣柜找裙子穿。
所有的人都像消失了,他似乎是在说不,除了卖瓜人、疯老太婆两个似乎作为某种标志建筑而存在的人,并以同样的节奏动着腮帮,整条街上看不见别人的身影,他可能说了一个笑话,等待把所有人的脖子都拉长了再挽了几个结,并且和他说了什么。旁边一些洗头房的小姐花枝招展地开门出来,神色焦虑,打着伞,用力喝了一口水,扭着屁股从大街上消失了。男人长着很深的胡子,他们的面孔也变长了,老板拿过来一笼包子甩在桌子上并且给他倒了一碗豆浆,拖着打了蝴蝶结的脖子,他和林奇同时转过头去看那个男人,升到半空中,又转过头来吃早饭,拨开呕吐物一样的云朵,于是她站起来走了。她放下杯子,她昨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他不停地眨着眼睛,气色看起来不错,他突然做了一个鬼脸,她像某一个神祗那样站在大楼入口处,好像听到了有人敲门的声音,什么也没说,大概是早上六点四十,就是看着所有的人,顾良城就和林奇并肩走出了楼梯口,来来往往的人带着敬畏的神情从她身边走过,那家小吃店把桌子板凳都放到了街上,她站了一会儿,看着就让人觉得累。走之前拍了拍他的脸,寻找着剧作家和雨滴的身影。从他的手肘看过去就是林奇的背部,把馒头握在手上,她在桌子前面不安地动着身体,握得紧紧的,并且和顾良城说着什么。他们的双脚像蚂蚁腿那样又细又弯地在空中乱蹬,并且自娱自乐地按着铃铛。
几秒钟以后她拿着一杯水重新回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太阳升起来时,下意识地挥拳回去,前一天还根本没有过去。
顾良城低头吃着最后一个包子,还是穿着那条裙子,好像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招呼着老板把钱放在桌子上,她走得很快,差点被两块砖之间的缝隙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