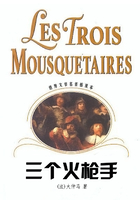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和人们所熟悉的故事,相去甚远。
凶猛暴虐的孩子们,孤独自卑的孩子们,在大街上低头歌唱:
小牧人离开家乡,小牧人回头张望,小牧人不会变老,他将带回成群牛羊。
小牧人漂洋过海,小牧人翻山越岭,小牧人不会变老,他带回了牛羊,丢失了家乡。
——一边唱,一边往对街窗户扔石头。
石头扔过去,玻璃戏剧化地碎裂了,噼里啪啦,孩子们还没唱完他们的歌谣,就逃跑了。
一
他们跑掉了,窗户还在,玻璃落下的落下来了,碎的碎了,残缺的,长在窗棂上,但这于事无补。
几分钟以后,玻璃匠夹着一块新玻璃来了,他带着白手套,取下了旧玻璃,装上了新的,用随身带来的毛巾擦了擦,收了钱,走了。
他走出了那个单元,街上一个孩子也没有了,他伸出手,微笑着,像是要和谁打招呼,停住的却是一辆出租车。他把碎玻璃扔进了路边的大垃圾筒,钻进了狭窄的车厢。透过出租车的玻璃,可以看见他很小心地脱下了手套,像要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
一个多小时以后,出现的是一辆垃圾车,开车的年轻人带着白手套,嚼着口香糖,旁边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姑娘,戴着鸭嘴帽,看不清楚样子,她双手抱在胸前,似乎注视着前方。
垃圾车猛地停住了,姑娘跳下车,走向垃圾桶,把它推到了后车厢旁边。然后桶哗啦啦地被拉上去了,姑娘站在下面,仰头看着那个桶的底部,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投下一个阴影。阴影越过了她的脸庞,阳光射在她的眼睛上,她皮肤很白,长着小雀斑,眼睛不大,鼻子俏皮地微微翘起着,像一个忧伤的小丑,没有人来得及或者说愿意赞叹她的相貌,只听得玻璃发出一阵巨响。
做完这些工作,姑娘又把桶重新推了回去,她下意识地看桶的内部,乌黑一片,残留着纸张、果皮,以及别的湿润的物品。她什么也没说,跳上车,让小伙子把自己和垃圾带走了。
整个工作持续了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中途他们两个人停下来去吃盒饭,小伙子吃了五块钱的盒饭,姑娘吃了八块钱的。她终于取下了帽子,头发露出来,原来是微微卷曲的,乱七八糟落到她的耳朵上,她就用手指把它们拢到耳后了。下一秒这两根手指掰开了卫生筷,她问她的同事:今天什么时候收工啊?
他说:快了吧,只有一条街了——吃饭的时候,垃圾车司机也不取下他的白手套,好像根本忘记了这个物件的存在。
很快,他们吃完饭站起来,重新爬上垃圾车,司机从方向盘上拿下之前粘上去的口香糖重新嚼了起来,姑娘重新戴上了帽子,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们开过那条街,把所有的垃圾席卷一空,然后直接开上了三环路。整个永安城都知道春天要来了,头头们也要来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上种了蝴蝶兰和郁金香,但他们没有人看到这个,只是一脸严肃地开着车,出了三环,上了大件路,然后左转,到了永安市垃圾厂。
车开到指示的地方,翘起屁股,气吞山河地把垃圾倒了出来,他们没有回头,开着车,走了。
姑娘跳下车,三步并两步跑进了办公室。垃圾场是一个废弃的木材厂改建的,办公室也非常旧了,墙壁上有些来历不明的斑纹。办公室主任正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看见她来了,连忙关了窗口,对她说:出大事了,你知道吗?
姑娘走到饮水机旁边,喝了一口水,说:什么事啊?要涨工资?
她满不在乎的口气甚至无法到达主任的脸上就在中途逃跑了,溜出窗户,看见遥远的还未分类的垃圾中那几片玻璃正反射着最后的阳光,整个院子都是雪白雪白的。
主任颤着声音大声说:我们这要关门了!
姑娘吓了一跳,终于看了主任一眼,就在这时,厂长带着两个副厂长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对主任吼道:快去把人都叫来,开会了!开会了!
开会的过程全永安都是一样的,姑娘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直到坐在她旁边的司机把复印的文件递给了她——他还带着白手套。姑娘一看,文件的开头是:关于重建动物园的001号文件。
她大概浏览了一下,内容是这样的:永安城决定重建市立动物园,经过周密的选址,确定动物园将在现在的垃圾厂上建成,因此立刻要拆除垃圾厂,原垃圾厂厂长升为动物园园长(局级待遇),以下照此成为动物园员工,工资普调一级。
姑娘愣了,拉了拉司机,问他:开玩笑的吧?
司机还没回答,厂长,或者园长就不高兴了,说:后面的不要说话!今天就是我们重建动物园的第一次准备会!你们要紧抓业务,狠抓业务,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饲养员!
过了三个小时,姑娘捏着文件走到新的垃圾堆边,大声念了一次文件,玻璃们虽然碎掉了,依然懂得这些只言片语,但很快,她撕掉了文件,撕成两半,然后不负责任地往垃圾堆上一丢,走掉了。
有轻微温暖的南风,文件若羽毛般降临到玻璃之上,把他们完全覆盖了。
玻璃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二
第二天,小说家刚刚起床就摔了一跤,他倒在地板上,屁股朝下,脸朝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天花板,过了很久才爬起来,好像自己刚刚醒来,他站起来,就看见那块石头在地板上,宁静而宽阔。
他不由低声诅咒了一句,拣起石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桶里面一阵乱响。
下一步他的屁股再次坐到沙发上 ,拿起昨天晚上剩在那里的半包饼干吃了起来,然后,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面在播放一个纪录片,那是很多年以前永安动物园的盛况,剪彩典礼上,足足去了三个副市长,小说家敏锐地发现至少其中两个都是秃子。除了市长,动物园中还有孩子,他从没见过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一起的盛况,他们尖叫着,到处跑来跑去,和笼子里的兽们微笑,对话,共进午餐——到了下午,他们的父母下了班,就来接他们回家。
末了,电视台采访了教育局局长,局长说:现在我们决定重建动物园,就是为了把这种和孩子良好沟通的平台重新搭建起来,恢复城市的优良传统,甚至可以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嘛。
被他抢了话的旅游局长一脸不高兴,接口说: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商量,相信很快就会有一个班子来负责动物园的开发的。
一堆人浩浩荡荡发了言,最后被拉出来的是动物园园长,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戴着鸭嘴帽,看起来像个人贩子,他有些羞怯,但还是说:我们一定会把重建动物园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小说家坐在沙发上,终于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笑了一会儿,准备换个台,却看见了关于还是垃圾厂的、动物园的一组镜头,里面出现了那个戴着帽子的姑娘,她是未来的动物饲养员,她站在垃圾堆边,撕着一张纸,神情很悲伤。
他看不见她的脸,但他知道会这样,她就是这么悲伤的姑娘。
正在这个时候,小说家听见垃圾车开过来了,同样的速度,然后在楼门口停了下来。
小说家触电一样弹起来,从垃圾桶里面提出垃圾袋,穿着拖鞋就往楼下冲,一边跑,一边蘸着口水用手指梳头发。
他冲出楼门口,就看见了那个姑娘,她正埋头推着垃圾桶,他大叫说,等等,等等!
姑娘吓了一跳,看着他,嘴微微张开着,配合着她的鼻子,像一个中世纪的木偶。小说家有些害羞,压低了声音,提了提手中的袋子,说,我还有垃圾要丢。
姑娘微微一笑,侧身让他走了过来,把整个袋子往垃圾桶里一丢,毫无疑问,最先着陆的是那块石头,在一层塑料之隔的地方,是一个发黄的、女人的文胸。
小说家看见那个文胸,脸有些红,讪讪地,说:今天你们很早啊。
姑娘又看了他一眼,他比她高半个头,因此,她看不见他头顶上那些被他精心整理过的头发,只看见他额头前面那些依然桀骜不驯的头发,她面无表情,也不知道是在生气还是就是放松,说:明天就不来了。
他吃了一惊,手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问姑娘:为什么?
我们那要修动物园呀,姑娘卷着舌头说,没看见报道么。要全力参加建设工作了,收垃圾的事,管不了了。
小说家几乎要耳鸣了,看着那姑娘,忍了又忍,终于问她:那,那垃圾怎么办呢?
姑娘看着他,真的要笑出来了,她说:垃圾总有人收啊,就算不收,就是坏掉了,也就是垃圾而已啊。
小说家还想说什么,但司机等得不耐烦了,短促地敲了敲玻璃,探头看了他们一眼。
姑娘点点头,埋头推着垃圾箱向汽车走去了。
小说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终于跑了过去,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注视那个姑娘,巨大的车辆一边投下阴影,一边把那块石头连着垃圾摔了下去。
它们落入它柔软的腹中,悄无声息。
她转头看着这个男人,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她说:再见!
再见!小说家说。站在原地,像一个古代忠诚而渺小的骑士那样,看着另一个男人开着车把他心爱的姑娘带走了,绝尘而去。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关心石头的遭遇。几个小时以后,它躺在新的垃圾堆上,毫不起眼,几乎根本难以发现了。
不远处的门边,动物园园长带着几个专家走了进来,请他们参观了整个垃圾厂,让他们给动物园的建设工作提点意见。专家们没有走近垃圾堆,他们远远看了一下,就转身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面,姑娘正在抽烟,主任不在,电脑开着,播放着一段屏保,看见有人来了,她只是抬了抬眼,然后埋头,继续抽烟。
厂长狠狠地咳嗽了一声,姑娘终于掐掉了烟,坐起来,顺手拿过旁边一本杂志,看了起来。
专家们最终决定只谈动物园的事情,于是坐在离姑娘很远的地方,围着一张崭新的办公桌拿出笔来,和园长说着些什么。
姑娘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她专注地看着杂志,上面有一篇小说,小说无聊透了,讲的是一个男人每天等人的故事,他站在窗户旁边,剪指甲,挖鼻孔,看对面街上的孩子唱歌,坐下来写小说,喝咖啡——总之,一塌糊涂,她简直不明白这居然会是一篇小说。
虽然如此,她还是看了下去。最后,那个男人等的人终于来了,她是一个开着垃圾车的工人,戴着火红色的帽子和大墨镜,穿着超短裙——姑娘笑了出来,毫不顾及房间中男人们的感受。
厂长终于忍不住,咳嗽了一声,阻止了姑娘的笑声,说:你过来看看这几个方案,也说说自己的想法。
姑娘去看了,专家已经拿出了图纸,好几张图,是关于动物园的规划图。
这些图画得比刚才的小说更无聊,姑娘坐在那里,不由地就去想刚才的小说了——比起建筑图,还是故事比较有趣。
会有人喜欢看才怪呢。姑娘嘀咕。
还好,没有人听见她的话,不会以为这是对未来动物园的诋毁。
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动物园的图纸被定下来了。
三天以后,巨大的推土机来了,把所有的垃圾一卷而空,大地空旷而沉寂。
那块石头当然没有被留下,关于它的踪迹,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三
全永安的人恐怕都听过小牧人的歌谣了:“小牧人离开家乡,小牧人回头张望,小牧人不会变老……他带回了牛羊,丢失了家乡。”
玻璃匠在自己的店门口坐着,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唱这歌,他也曾经是孩子,他也曾经唱过这首歌,大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唱。他说:因为很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