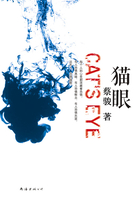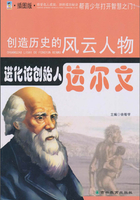天刚蒙蒙亮,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孙安路把妹妹安芯送上了裹着一身泥浆的长途汽车。班车车顶上驮着高高的一大堆行李,后面背着一个烧煤烧劈柴的锅炉。孙安芯扒着车窗探出头,眼睛红红的,说:哥,真想让你送到乐平县。你咋是这样一个人呢,经不住一句好话。孙安路默默地目送着班车驶出车站,从一段段泥泞驶向一截截坑洼。负重蠕行的班车要前往早在1936年就打算建设、其后却屡建屡停的宁赣铁路建设工地。
孙安路眼里也潮了。安芯说得对,自己的确耳根子软。这几天他向段里要了补休,一是秀的预产期到了,二来打算把安芯送到新线指挥部所在的乐平县。可是,长途车票刚买好,派班命令就来了。他去找张段长,说安芯心里有事呢,不盯着她全家都不安心。再说,秀该生了,前两回都碰上跑车他不能照顾,这回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光靠奶奶忙不过来。张段长显得很不自在,但态度却坚决,他说:这回临时派班,拉的是军列。谁跑,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孙安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俺不是党员。他的意思是说,这么重要的任务应该派在党、政治上靠得住的同志担当。张段长便笑:原来你心里有个结啊!想想,这回派你的班不就是对你的考验吗?孙安路说:我都烤成炭啦。张段长趁势又给他灌了许多好话。无非还是说他责任心强技术过硬线路情况熟悉而已。孙安路却是热血沸腾了。
不过,这回孙安路对张段长还揣着几分敬意。司炉陈连根如愿娶了梅香,正是张段长帮的忙。孙安路替司炉去找领导,张段长当即拍着胸脯打了保票,难得的豪爽。陈连根父母的工作好做,媳妇虽是二婚头,可她没生养,又招人喜欢,再说儿子早已迷上了她,陈家也就顺其自然了。难办的是聚族而居的港背村,全村男人都姓刘,都和梅香的前夫是亲戚,火车轧死他们亲戚那事虽已处理,他们却很不满意,开始是扛着锄头铁耙闹着要拿铁路的人抵命,后来又要赔偿,经过铁路上再三说服教育,他们懂得了过铁路要走道口,要一停二看三通过的道理,但他们却与铁路结仇了。很长一阵子,这些菜农在菜地里干着活,遇见从身边经过的火车,拾起土坷垃就掷。他们管铁路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铁皮俚。一旦逮住在藕田里钓鱼或在菜地里拾菜叶的铁皮俚,他们可凶啦,踩烂鱼篓菜篮不说,还常常拳脚相向。好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孩子,都叫他们吓得夜里做噩梦。张段长第一次去与铁路新村紧邻的港背村,还没找到梅香家就给轰出来了。第二次再去,他依然穿着带铜扣子的制服,却在胸前别了好些枚抗美援朝的纪念章,金光闪闪的两排,好像大英雄似的,全村的孩子冲向他,簇拥着他,唱着嘿啦啦啦嘿啦啦啦,把他领进了梅香家。只要能见着梅香的公公婆婆,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张段长是带了条件来的,可以把他家女儿招到行车公寓去当服务员。儿子死了,媳妇再嫁,梅香公婆原本无奈,见自家竟也能出个铁皮俚,自然喜出望外。
所以,热血沸腾的孙安路领了任务后,还对张段长说了一句话,他说:张叔,你去港背村那事干得漂亮,大家伙儿都夸你是孤胆英雄,盼着你常去港背,多给段里找几个丈母娘呢。
因为任务光荣,孙安路特意换了件白衬衣。秀叫起来:你就这一件白衬衣,家来就染黑啦!你不是还念着打扮得像个学生,找个上海的洋闺女吗?俺可不给你洗。
孙安路嘿嘿一笑,用手指蘸着口水,又搓出一个黑疙瘩蛋来。
军列是头天夜里抵达合欢的,停靠在525部队、也就是铁道兵材料场的专用线上。军列上拉的是卡车和炮。炮都用篷布遮盖着。还有几节闷罐子车厢,是兵车。合欢城是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美蒋侦察机经常光顾它的上空,有时它们会扔下一些传单糖果玩具什么的。奶奶就反复叮嘱孙子孙女,在车站、铁路边拣到糖果可不敢吃,那是老鼠药呢。范站长的老五范多多,为么长得猴似的,就是吃那些糖果吃坏啦。当然,驻扎在铁路沿线的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每有击落美蒋侦察机的消息,总能让合欢城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连着乐上好些天。
军列肯定是敌机侦察的重要目标。所以,军列常夜行昼伏。悄悄地去,正如悄悄地来。不过,神秘的军列始终与铁路非常友好,尽管站岗的战士一般不让人接近列车,可见了铁路制服却不管,哪怕是孩子。军列上的战士们整天坐在闷罐子里熬时间,只有吃饭撒尿才能下车,铁道边用帐篷布围起来的棚子,就是临时厕所。临傍晚,刚刚接班的孙安路路过这里掏出家伙时,遇见了放映员。他说:倒坝啦!你的尿脬够大的。你们部队没厕所啊,憋着尿送到这里来。干脆送到厦门前线去得了,直接炮轰金门不好吗?
放映员叫声大哥,便笑:你看这一地!我相信,全国人民一道撒尿,一定能把金门淹了。
你多久没家去啦。老太太天天念叨着。安芯的事知道吗?这会儿她该到站下车了。孙安路问。
放映员告诉他,这阵子自己正忙转业的事,单位已经定下来了,去的也是宁赣铁路工程指挥部。毫无疑问,他是冲着安芯去的。随着新线上马,他的爱情工程也该好好规划设计开筑路基了。
孙安路不无自豪地说:干铁路,你要学门技术,别再放电影了。电影里的火车都是假的,假的火车能解放台湾吗?能把部队送到前线去吗?当个装卸工巡道工也比放电影强一百倍。俺当年好歹也算知识分子,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才去学司机的。
放映员不敢苟同,说:每年二七,放二七风暴,那场面多感人呀。全城的人都跑到我们部队里来,把礼堂挤爆了,改在露天放。二月天夜里多冷呀,一个个冻得把鼻涕都甩到幕布上来了,看完一遍还不走,嚷着再来一遍。这就是电影的力量。
傻小子,咋不开窍呢。不想想当初安芯为么放着光荣军属不做,非找张卫国不可。想去吧。俺跑这趟军列哪。
放映员嘿嘿地递上了一张纸条,是安芯给他的,上面没几个字,只是告诉他自己调走了。安芯喊他于金水同志。于金水同志便用这张纸条证明,他的爱情工程就像铁路工程一样,是从两头铺轨,然后在中间合龙。孙安路照他脑壳给了一下,说:还是老太太的山东大葱管用!喂,你没事替俺回去看看,你嫂子生了没有。这趟车得十八点三十分发车。来得及就过来告俺一声。
于金水看了看手表,忙不迭地跑走了。
那张纸条让孙安路的心情好极了。他带着副司机何刚正和司炉陈连根上了机车,细心检查好机车,等着要道要信号时,孙安路告诉他们,秀今天下午住进医院了,没准夜里生产。老三要是在军列出江西之前出生,就叫孙鹰,进入福建境内呢,就叫孙厦。他俩都说孙师傅有学问,虽然孩子的名字都是地名,让他随便一拆,又文气又好听。
陈连根便向孙安路讨要红鸡蛋,孙安路从饭盒里掏出来两个山药蛋,鸽子蛋般大小。他说:俺预备着呢。不是俺小器哦,买不着呢,俺媳妇也吃不上。不过,俺相信她奶水旺,不用催奶,天天就是稀饭红薯糠菜团子,照样哗哗的。
陈连根便笑:我嫂子变成奶牛啦!要是梅香到时候奶水不够,我向嫂子借去。
何刚正说:你借你还啊。
陈连根不由得感叹:我这个老婆真是来之不易,是打败了美国佬的英雄顺手替我摘来的金达莱。
何刚正讥嘲道:什么金达莱!明明是港背蔬菜大队菜地里的南瓜花丝瓜花。孙师傅,张段长只得过一枚奖章吧,他竟敢拿纪念章糊弄老百姓。
孙安路却说:这事做得好。俺觉着,这比冒着轰炸扫射的危险驾车更了不起。为么呢?那是工作是任务,胆小,不去,行吗?上了车,敌机来了,丢了车逃命去,行吗?都不行。工作就是俺的命。可闯进港背村不容易啊,挨骂挨揍都是白搭的!为了这件事,俺得敬他三分。好,赶紧吃饭吧。
他们蹲在车轮边打开了各自的饭盒。孙安路边吃边说,这趟跑彰武千万不能麻痹,即使对线路上的情况心中有数,也要大睁双眼。鹰厦铁路经资溪穿越武夷山入闽境,地质构造系古华夏大陆的一部分,为太古代的花岗片麻岩,上层为石炭纪石英岩,板岩及三叠纪、侏罗纪沙岩及页岩。主要工程地质特征是岩层风化作用,尤以化学风化为剧,一般深达五至十五米,使岩层物理技术特征改变,稳定性大为降低。水文大部分埋藏较深,地面下四至十米,土壤中水与裂隙水分布极广。再加上沿线温暖湿润,雨量丰沛,它成为穿行在风雨中的钢铁大动脉,成为一条湿漉漉的路。特别是台风季节,线路经常因山体滑坡、路基塌方而中断行车,有时得抢修几天才能恢复运营。孙安路这个车班,就曾几次被阻隔在武夷山中。其中一次,是在深夜里,拐过长长的弯道,他突然发现前方道心滚落了一块巨石,赶紧撂闸,滚滚车轮在大山中发出尖利的悸叫,把绵绵群山都惊醒了,列车稳稳地停下来,火车头前面的排障器正好抵着那块巨石。孙安路惊出一身冷汗。事后,何刚正对司炉说,孙师傅不仅反应迅速,而且在紧急刹车时力量把握得恰到好处。否则,要么撞上巨石,要么车厢凭着惯性往前冲,整个列车拱起来,造成部分车厢脱轨。
司炉陈连根放下饭盒,便去泡了一大缸浓茶,递到孙安路手里,同时,还给他点了一支烟。一枝笔的。那一枝笔专门用来孝敬师傅了,所以总也抽不完。
天色暗了。孙安路看看挂表,三人同时确认信号、道岔正确,同声高声呼唤“确认”,紧接着,孙安路踩响了风笛。出库的火车头很快挂上了军列。攒足了劲憋足了气的火车头,好像迫不及待似的,烟囱里一阵黑烟滚滚,烟囱旁的气眼哧叹哧叹地喷着汽。从列车中部向两头走的列检员,一手握电筒,一手攥着尖嘴小头,一直弯着腰,不时钻到车厢底下敲一敲。来到火车头边,列检员便向列车尾部晃手电,夜色中,他们用手电的光柱,画出一个个明晃晃的圆。在列车尾部的守车边,呼应他们的,也是那样的圆。
随着一声长鸣,军列缓缓启动了。从材料厂的专用线出来,经过股道间散落着好些扳道房的西站,手执信号旗的扳道员,笔挺地站在道岔旁致意,目送着它离去。咣咣,咣咣,列车行进的速度渐渐加快,其节奏却是明快动人。
陈连根对何刚正说:看来,孙师傅家的老三该叫孙厦了。
何刚正大喝一声:你说什么?
火车头上,是钢铁的轰鸣,炉火的呼啸,疾风的嘶吼。可是,坐在驾驶座上了望前方的孙安路,却看清了那个名字,叫孙鹰。
那是奶奶站在铁路新村的道口旁呢。她身边还有就要转业的于金水。于金水冲着火车直招手,而小脚的奶奶,举着比小脚更长的手电筒一个劲地晃,晃出一个又一个圆。圆圆的肚皮,圆满的结果。就像列检员的信号。
秀果然又给孙家添了个小子。
奶奶告诉秀,跑车呢,可不敢让男人揣着心思上路。
秀对着怀里的老三说:鹰啊,等你翅膀硬了,怕也追不上你奶奶。你没看见她跑得多快,你天黑时落的地,她从医院直接跑到火车的头里去了。
奶奶则感叹道:有双大脚多好!别说三个孩子,你生上十个八个,俺都不让你累着。俺裹脚那会儿,好些个一般大的闺女都疼得不行,哪能不疼呀,用老长的裹脚布紧紧地缠着,就像包粽子,把脚指头都蜷过来了,光剩下大拇哥,一走路咯吱咯吱响,骨头断了似的。那些闺女哇哇哭,不乐意,遭罪呢。有些娘心疼闺女,就让放了脚。俺娘心狠,不让放,俺娘说大了你就懂了,那些放脚的蹄子保准嫁不出去。可赶上这年头,还是大脚好哇。
奶奶是四五岁时裹的脚,用了三年时间,初步长成这般模样。弓弯短小,脚底凹陷,脚跟臃肿,脚背隆起。奶奶烫脚的时候,大孙子庄儿常蹲在脚盆边,忍不住伸出一个小手指去摁摁,也不嫌水烫。有一天,奶奶干脆满足了庄儿的好奇心,把她的小脚伸给了他。庄儿握住小脚,拧着个脑袋看脚底。还有四个脚指头哪去了?那四个完全扭曲的脚趾藏在脚心里呢。奶奶的小脚就像一个三角形的肉疙瘩。庄儿便掰那些压在脚板下的脚趾。奶奶骂道:鳖羔子,俺可不做蹄子!
这会儿,奶奶羡慕大脚,为的是上山去挖野菜,或者像蝗虫一样在蔬菜大队的菜地里拾荒。黄菜叶子红薯根红薯藤和甘蓝包的根蔸,甚至肥田的红花草,都成了美味佳肴。正赶上自然灾害,每个月粮食定量减少了,幸亏家里有个火车司机,孙安路能吃上四十斤,奶奶和秀两个人加起来才四十来斤,三个孩子总共还不到四十斤。奶奶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揣着户口本、粮油供应证去给孩子加粮食,每长一岁能添两斤口粮呢,直到十四岁吃上二十几斤为止。凭着供应证去粮站买米,得排老长的队,排着排着就没米了。那点口粮中还要配售百分之十的糠,细糠掺些面还能对付,买来的若是粗糠,那就苦了嘴和腚,粗糠几乎就是稻谷的谷壳,咽不下去,拉不出来。那阵子,坐落在单身宿舍后面的公共厕所里尽是使劲的憋气和撕裂的叫唤,跟产科手术室似的。于是,铁路新村的家属都盯上了周围连片的人民公社菜地。可拣菜叶需要腿脚利索,就像游击队似的,菜农走了,赶快拣去,菜农来了,没命地奔逃。菜农对此恨之入骨,不让拣,逮住了就踩扁你的篮子,扒走你的衣服。正如铁路职工把他们拾煤渣的妻女撵得狼奔豸突一样,他们见了蹿入菜地的铁路家属注定要以牙还牙。
奶奶为脚感叹的时候,也就是拿定主意要出门的时候。秀说:别去拣了。先向范家借点米吧,等出了月子,俺去。
俺不好意思去范家啦。你说范站长心咋这么狠呢,俺说卖个老脸吧,去替他女婿求求情,别开除啦。可他没二话。俺这老脸不算么,可那是他女婿呀。没工作了,让他喝西北风去?闹得俺见了晶晶那闺女,怪不自在的。
奶奶嘀咕着,又往腿上套了一条单裤,还剪了几截麻绳揣在怀里。秀知道劝不住,便喊:庄儿,枣儿,把写字本收好,搀着奶奶一块去。两个孩子马上跑到奶奶跟前。
奶奶说:乖,该做么做么去。赶明儿上山剜野菜再带着你俩,山上有花,能看见火车打老远开过来,能看见你爸爸在火车头上鸣笛,庄啊枣啊,俺回来啦。今天俺去拣菜叶,菜地里有老虎,虎口拔牙呢,老虎的嘴巴这么大,吞个孩子跟嗑瓜子似的。
枣儿怕了。庄儿却拽着奶奶的衣襟不撒手。奶奶说,那就跟着吧,你放哨。看见扛锄头的,就叫奶奶,俺俩赶紧躲开。
奶奶领着孙庄往远处去。经过道口时,遇见正在那里歇脚的巡道工,他拦住奶奶寒暄了一会儿。巡道工说老家来信了,他媳妇在县城当老师教得可好啦,年年当先进,几个孩子也很有出息,最小的也参加工作了,老大就要出嫁,找的是部队上的政委。奶奶却笑:火车头是爹,车皮子是娘,娘不随爹爹闹心。你别是逗嘴玩吧?
巡道工说:你别不信,明儿俺把信带来,就怕你不识字。
奶奶却自豪了:俺有庄啊。俺家庄儿才上学,认的字就能装满一节六十吨的高边车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