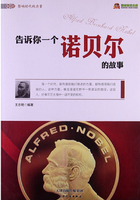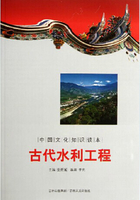章士钊所引布赖斯的“国宪者……所以构成一社会而宰制之统合之”的看法使***进一步确认了他以往关于一部“广被无偏”宪法对于保障国家“治平”、人民幸福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有容”与“有抗”的观念告诉他,宪法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做到“有容”,而其能否作到“有容”,又在于“宪法构成之质得其衡平与否”,即宪法的制定及其内容是否体现了各种对立意见或派别的平等参与和各方面的意见。这种“衡平”的获得则在于“有抗 ”,即首先应使不同的意见、派别形成对立。
他指出:一部好的宪法,应当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亦不许某一派势力或某一团体专断。宪法容量的增加有两种情况:一是随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需要增加内容。这时只要精通宪法的专家根据法理和社会需要提出修订意见就可以了。二是社会某种势力根据自己需要要求扩充宪法内容。这就不是几个学者可以解决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订宪法者分为两派。这两派要形成“并持对抗”之势,但同时又“各知尊奉政理,容纳涵蓄,不敢妄冀专断”。
如此说来,“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没有两对抗势力相抵以达于平衡,决不会产生宪法。那种由一家意见或一派势力产生的所谓“宪法”只不过是“一势力之宣言”,硬把它说成“宪法”罢了。这种由一种意见和一种势力产生的“宪法”是真正靠着“力”而产生的,“力存与存,力亡与亡”,无所谓遵守,更谈不上为国家维持治安、给人民带来幸福了。
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在宪法产生之前,应当先养成“对抗势力”,或者确切一点说,是先求国内各种势力之间达到一种对抗中的平衡。为此,他恳切地向袁世凯政府、进步党、国民党及所谓“社会各方人士”分别提出了劝说意见。
对于袁世凯一派“有力者”,***希望其“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不要摧残异派势力,以造成“政治新运,斩绝中途”。
他指出:宇宙之中任何一种“动力”,只要它发生了、存在着,无论用何种“权力策术”都不会让它消失,因此,智者总是对这种“动力”发生的原因“穷其究竟”,并在宇宙间给它以相当的位置,使其不致冲决泛滥,对于政治势力尤其是这样。
然而,这方面相反的教训太多了,以国内言,清政府排斥革命势力,结果被革命所推翻;革命者中激进分子不讲“有容”,结果导致国民党覆灭。现在政府又乘“凯旋之余威”,惟所欲为,倾注全力,以图彻底摧毁包括进步党在内的所有抵抗力。自以为这样能收长治久安之效,其实是厝火积薪,大乱不远。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以其并六国之威,不惜用销毁兵器的办法消灭“抵抗力”,结果秦至二世而亡。在俄国,沙皇有哥萨克铁骑镇压反抗,而无政府主义分子遍布全国。更有同中国情况相近的墨西哥,被排斥压制的势力屡起革命……
所有这些,“皆由于一势力崛兴,不容他势力平和活动之余地,终至溃决狂奔,演成怵目惊心之惨剧”,当政者难道不需要深思吗
***引述明代思想家李贽有关“君子之治”、“至人之治”之说写道:
昔李卓吾论政有曰:“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夫人之与己不相若也,有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而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
“君子之治”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善恶利害原则施政的一种政治,在这种政治下,统治者自己以为是善的、有利的,希望别人和他一样认为是善和利;统治者自己认为是恶的或有害的,希望别人也和他一样认为是恶和害。
这类统治者这样做未必不按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原则度己度人,但是一个人的思想终究不是天下所有人的思想,即使是良善的统治者,其个人的好恶也不能代表天下所有人的好恶。一定要以个人的好恶定之于法律,要大家来遵守,这是叫人很不能理解的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实行统一教育和刑法的工作,而人民中间的违法乱纪之事反而会增多。
所谓贤者智者认同统治者的道德和法律原则,而所谓的愚与不肖者则由于不能认同或不去认同而与统治者愈来愈疏远,加上统治者又有表彰惩罚善恶的政令,人民由此分为君子小人两类,这不更导致纷争吗
“至人之治”是一种“无为”政治。统治者并不以自己的好恶去统一天下人之心,而是沿用以往的政策法令,不改变人们的习俗,顺应人民的习性而不阻挡其能力的发挥,这样就会避免那种“有为”政治产生的弊害。
李贽这一明显是老子“无为”思想翻版的议论被***看作是前人批评好同恶异思想的绝好材料,也成为他后来提出“民彝”政治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和依据。
但是,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后来又同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并不愿意连道家的因循甚至倒退的历史观一起接受过来。
他在引述李贽的话时,已经觉察到其中因循思想成分,因此,在引到“顺其性不拂其能”一句时戛然而止,省去了下面的“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叫百姓听他们熟悉的东西,不想要百姓接触以往不知道的新东西,以免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产生波动)。尽管下面的“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絷而颠且仆也”(行事以安定为原则,不想给百姓定过多的制度、法律,以至束缚过重,怕他们因束缚过重而受不了)一句的内容对他的论证亦有很大帮助。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嫌疑,同时也为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指出李贽的议论说明“好同恶异”不可取及“开明专制”不可行之后,特别针对袁世凯政府以大量清末旧官僚充任政治会议和政事堂成员一事提出批评,指出袁世凯的这种行为“亦萌于好同恶异之念”,是不可取的。
他说:宇宙是进化的,“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
对于曾经依附袁世凯,以抵制革命势力的进步党,***希望其“以极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不要阻止正当异派势力的发生,进而应当振起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和暴乱之势力,舍迷途而趋正轨”。
他说,历史上朋党之祸,大抵由于所谓君子不能和衷共济、牺牲意气,因而门户横分、自相水火,又被小人中伤,而引起的。近如戊戌维新运动中温和、激进两派本同为救国,却“忘提携之谊,开冰炭之局”。其后,革命、立宪“党派分流”,所谋数年不成。而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又正是两派同心协力的结果。
他对历史的回顾,目的在告诫进步党人在考虑与国民党或其他日后将要产生的政党之间关系时,要汲取教训,“不可互相水火,与人以渔夫之利”。
他并不认为进步党曾引袁世凯之势对于民初一度“势焰熏天”的国民党加以限制一事为不正确,但认为他们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所矫之势已尽,不复为患,而所引之势,专恣自僭,亦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党应当反过来对于袁世凯政府“立于批评谏正之地位”,“力能矫则矫之,一如其初。力不能矫,则离以自树,待他势力崛起,相引而与此绝盛之势力抗,以遏抑其横暴”。
按照他在前边所说的一种力产生即不会被消灭的认识,他告诉进步党人在一种势力发生时,“当先察其动作,是否合于正轨,合则引为己友”,若是一时不能确定其是否合于正轨,“亦当勿阻其势力之进行”。即便是该势力的行为不合于正轨,而“仍狂奔于迷而不复之域”,那就更须“掬血诚披肝胆以相告诫”。这也就是说,再不能采取像对待国民党那样的过分态度了。
为解除进步党人在对袁世凯由以往支持转到对抗一方可能在道义上产生的顾虑,他指出:
盖政治之活动,殊无历史关系之足顾,更无恩怨之可言,或昔合而今离,或昨敌而今友,为引为抗,举不必有恋舍之顾虑、恩怨之痕蒂,丛杂于其间。政治界无上之大义,在权衡政治势力之轻重,畸于何方,然后以自挟之势力,称之剂之,以保厥衡平。苟能剂政力于平,则毅然以临于离合引抗之间……径本政理,以为向背,此政治家自觉之道义,所当共矢者也。
这似乎是说,政治党派的正义行为是在政治势力的对抗之中起一种平衡调节作用,当甲派势弱,便要支持甲方,以与乙派抗衡;当乙派势弱,又应支持乙方,以与甲派抗衡。其目的就是维持政治上向背两力的对抗均势,避免因一派势力过盛而导致专制局面。至于某一党派怎样在处理不停地变换“离合引抗”立场同坚持本党政见的关系,***在这里没有向深处探讨。
说到“今也国会灭,政党涣,自治解”,政治由一人专断,“环顾政局,更无毫末之力,足当遏制之任”的事实,他进一步敦促进步党人:想要保持政治平衡,只有遵循正轨“求抗”,不要因为“幻云逝水之微嫌……而重贻政治前途以无穷之累也”。
***没有因为袁世凯政府走向新的专制,而对反袁的国民党改变看法。他认为国民党以往“滥用其势力,致遭败覆”,现在仍想“以零碎之血,快意气报恩仇”,劝告他们“当以绝痛之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赶快将自己的势力纳入正轨,不要去摧残国命、躬蹈自杀之路。
他觉得国民党人首先应认识到“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的道理。为此,他不仅引述托尔斯泰“无抵抗主义”观念,要国民党人认识到“暴烈之革命既已过时……实际之自由,非能依巷战虐杀而获者,宁罢止服从一切人界之权威,始能获也”,而且对自己一年前就提到的用暴力对付暴力,结果将是“以暴易暴”的命题作了进一步论证。他写道:
盖政权之起伏于暴力间者,恒奔驰于极端之域。彼以力据,此以力攻,力之所冲,反动必起。两力消长之际,强者居胜,同时反动之力,应强者之量而郁酝于无形。及其发也,亦必预蓄有较强之力,方能摧折其所向。于是复反动力又应之以起,其强又愈于其初。如是展转,互应不已。反动之力,愈激愈强,其力既足倾其所恶,而能自行,又安所惮而不自任以恣。愈激愈强之反动,将终不能潜消,其结果则以暴易暴而已。
这里说的暴力,在***看来,与对抗力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
首先,对抗力是在宪法允许的政治争论范围内不同意见或不同势力的和平对抗,暴力是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或被压迫人们要用武力去夺取政权的一种行为表现。
其次,对抗力是两力相抗相抵以达于平衡,一方存在而另一方消失,对抗力便不复存在。暴力表现为一方以力据守(政权),另一方以力进攻(争夺政权),两力不是对抗相抵,而是冲突,结果强的一方获胜,弱的一方被摧垮以至于销声匿迹;然而失败者既受强者压迫,其反抗的力量又会在无形中酝酿,直到强过对方,而又起来压倒对方;而被压倒者复再酝酿其力……如此展转往复。
再次,对抗力是对抗双方在一“广被无偏”宪法范围内彼此容忍对方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暴力的发生则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有较强势力的,把持政权的一派不给另一派以政治上应有地位,甚至不容忍该派存在。二是施行暴力的派别不“自纳”于政治正轨,即不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用政治手段、争论方式与反对派对抗,而用非法手段,夺取政权,以至于将其反对者消灭。
***认为国民党的错误正在“滥用势力,自轶于政治竞争之正轨”。他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就是以此看法为据的。
他告诫国民党人,以暴力争夺政权的结果,将激起循环不已的暴力冲突,法国革命和葡萄牙革命的“杀人流血之惨”的历史殷鉴不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又将面临“危机存亡,千钧一发”的形势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问题。况且既然以暴力压服反对派,也必然要用夺取的政权压服不同意见者,其结果共和民主和人民的幸福都无实现之期。
他希望国民党人“自纳其力于正轨,静待机势”,也就是说让国民党放弃革命手段,等国中专制势力衰弱下来,再和民间逐渐增长起来的“正当之势力”携手形成针对现政府“横决之势力”的对抗力。
在***看来,袁世凯的暴政势力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民党的“滥用势力”,及其坚持革命的行为激发起来的。一旦国民党放弃革命,政府没有了革命势力的威胁,其专制倾向就会减弱,政治上便会渐有可以形成民主争论的气氛,政治对抗的形势就有形成之机。
***当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没有先前同盟会发动革命,就没有清王朝垮台;没有随后护国战争和各方势力武力反袁,就没有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走向专制除与国民党争势这个因素外,还有其他原因。同时,国民党也决不会因***这样的知识分子劝告就轻易放弃革命行动。
这样看起来,***的上述想法就未免太“冬烘先生”气了。
***的第四个呼吁对象是所谓“社会各方人士”。其中更多的也许是他一直抱有恶感的那些攀缘权贵、贪图利禄之士。他希望这些人认清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至为绝盛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从同”。
为“绝盛势力”所吸收,是指归附袁世凯政府;“盲心从同”是指不加任何考虑而附和当权者。***劝说这些人养成独立之人格,坚持独有的见解,特别是要他们认识到在当今时代,民众才是真正伟大的势力?他写道:
吾尝远纟番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
显而易见,***在几个月前写《风俗》时流露出的一旦民众风俗转而向善,便可制约“元恶大憝”的念头,在这里已明确成为民众思想决定人物、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乃至世间一切变化的认识。
***这一认识来自法国学者勒蓬和早已为他所熟悉的托尔斯泰启发。
从勒蓬那里,他得到“群众时代”的观念;从托尔斯泰那里,他得到历史事件由“势力”引发,“势力”是由一定人物代表的“群意志之累积”的观念。
他确认:随“世运之变”,帝王势力、宗教势力都已消逝而去,在其基础上兴起的“新势力”,即“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
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累积,而群众意志,一旦既让诸其人,其人复得以斯势力范制群众,群众不悟其人物之势力,即群众意志之累积,其人物遂得久假不归。群众苟自觉悟,则其势力顿倾……足见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