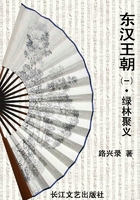在小小的病房里,我和西西过起了哲人的日子,简单而平静。生意不做了,书店也盘出去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像旷野中的两株野生植物,整日里晃晃荡荡。
这倒让我们俩有了举案齐眉的新鲜感,一起吃,一起睡,睡的时候也会暧昧一下什么的,可是每每要真枪真刀的干一仗的时候,西西总是找一个理由摆脱掉,我以一个男人的本能感觉得出,她心里有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一天,我想把一切都跟她坦白了,既驱除掉徘徊在她心里那个幽灵,也好争取个宽大处理,可是我刚开个头,西西就打断我,扭头去锅炉房打水去了,躲避我就仿佛躲避一头龇牙咧嘴的野兽似的,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想起我和洪荒、格林曾经在一起谈过:女人对男人来说究竟是什么?洪荒说,他的女人对他来说就是孩子的妈,她为他生孩子养孩子疼孩子,所以他就要养他的女人疼他的女人宠他的女人。格林说,他的女人是他的避风港,他远航回来,她会在港口等他,他疲累时可以偎依在她的怀里,她可以用柔情来温暖他。我却说,男和女就像拳击场上的对手,都想把对手打倒,打倒了还不算,还要数十下……记得,我的这番话当时还曾遭到过洪荒和格林的一阵嘲讽呢。
改变我对男女关系看法的是西西,是西西身上散发着的清新而富有朝气的气息,她是那种要爱就爱得死去活来,要恨也恨得咬牙切齿的女人,跟她在一起心里敞亮,我想我会跟她厮守一辈子,因为她就是天堂,可是几年下来,我和她之间竟也有了巨大的天然屏障,这个屏障就是背叛。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冷战下去吧?
依照惯例,人家是有困难找民警,我则是跟教授去请教,教授清脆的声音和达观的情绪总能给我以力量,不再沉重。这一次,他听了我的倾诉,教授默默不语,我只好又追问一句:我是不是要一五一十地跟她说清楚?
教授说:不,打死也不说。
万一要瞒不住呢?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
瞒不住也要瞒,一旦你承认背叛过,那么一条不祥的阴影就会跟着你们一生,永远也摆脱不掉,教授说。
想到那条阴影,我不禁感到迎面扑来一股只有坟墓里才有的寒意,是,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我故意铿锵有力地回答。
于是,在一个刻意挑选的日子里,我开始跟西西摊牌了,郑重地告诉她,虽然我在昏迷的时候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呓语,但那不是事实,也许只是一些潜意识里边的东西不小心的流露,我基本上算得上个良民,我可以用人格来做保。
我知道,我能否成功就取决于我的态度和语气了,态度要慷慨,语气要激昂。
西西一直没插嘴,像谛听一只鸟鸣啭一样。我不得不佩服我的狡辩水平,使她由冷淡渐渐变得开朗起来,两眼里也闪烁起兴奋的火花,我明白,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了。
最后她提出了若干的疑问,我都一一给了她满意的答复,之后,我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这时候我才感到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倦意袭来,我闭上眼,我困了。
谁说不信你了,是你自己多疑,西西满脸笑容地说,同时也用目光温柔地亲吻着我。
那天是五一劳动节,病人们都跑出去看焰火去了,只有我们俩躲在病房里拥抱、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