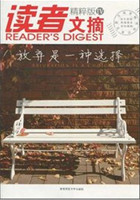从梦中醒来,我就忐忑,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不寻常的事,以至于连我特意叫伯爵给我捎来的书都读不下去。那本书是刘大白1924年在开明书店出的诗集《邮吻》。伯爵为了表示仗义,还外加了一本同一作者的《丁宁》。可是,此时此刻我就是领不了他的这个情,我几乎一个字都读不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做出形形色色的猜测,并把猜测编上序号,一一罗列起来,加以分析。还好,就在那些猜测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电话来了。
你是不是中午没饭吃啊,要我给你送去吗?我知道对方是谁,因为这声音有一种近乎磁性的东西,是上帝赋予的。
你做了什么好吃的,表妹?我反问了一句。太愚蠢了,我怎么会说这个,这根本就不是我要说的。我该说上一句有品位的话,哪怕是抄袭来的也好。
你等着,不会叫你失望的,她说道。跟着就是咔嗒一声,电话撂了,又干脆又利落。
接过她的电话,我忐忑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它拯救了我过速的心率和升高的血压。
我是不是该换换衣裳?这么一身病号服,总是给人一种可怜兮兮的悲观主义者的感觉,我不想让她对我有这种感觉。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以前西西要给我买衣裳,我都不让,觉得可惜。
是的,我觉得我穿好衣裳太可惜了,这种想法从初中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最酷的颜色是国防绿,最时尚的衣裳是军装,实在找不到军装,戴一顶军帽是最起码的。我的同学几乎都戴军帽。排队的时候,齐刷刷的绿帽子很是壮观,唯独我没有。难怪你总是这么孤独呢,老也不能跟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昆虫说我。那么好,你给我出个招,叫我不再孤独,我说。比如我们班同学都戴军帽,你也不能个别,所以也要找一顶戴戴,昆虫说。我没有啊,我说。去抢呀,老五的军帽就是抢来的,刘力的也是,你怎么就不能也抢一顶来?真窝囊!昆虫骂了我一顿。于是,一天下午,我在昆虫和另外三个同学的陪同下,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冒险。冒险的代价是被警察打了一耳光,抓进小黑屋子关了一宿;转天,父亲来了,又在我脸上补充了几巴掌,饿了一天。父亲在打我时,嘴里一直在说:戴个军帽就美了?我叫你臭美,我叫你臭美!往后,只要一穿新衣裳,我脑子里就闪现出“臭美”两个字,而且是两个加粗的黑体字。
最后,我还是在柜橱里找到了一件T恤,一条的确良裤,穿上。就在我扎裤腰带的时候,她到了。虽然早已见过面了,我还是有被震撼了的感觉,她的面容没有任何的修饰,素面朝天,这反而更让你觉出她的完美,仿佛那身体上的每一个柔软的零部件都和谐得有道理。我突然想起一个词,正好可以来描述她——上帝的杰作。
路上塞车,特堵,你早就饿了吧?她问道。她笑的时候,嘴角有点歪,歪得很俏皮是所有雄性动物都会为之动情的那种俏皮。不过,我没有,因为我再一次看到她手指上的那只戒指。
不饿,不饿,你先歇一会儿,我给她让座的时候,尽量控制着迈步的姿势,据说,从迈步的姿势上就可以看出谁是失败者来,成功者有上千种步伐,而失败者只有一种,而恰好是我所习惯的那种。
既然不饿,你让我送饭来干吗?她突然娥眉倒竖起来,让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空气中立马充斥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紧张氛围。她一边指责我,一边把意大利面条、蔬菜沙拉和鱼子酱端出来,两不耽误。
我不是跟你客气客气嘛,我说。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告诉她,我的遗传基因中绅士成分含量比较大而已。
你还要那些早已淘汰掉的东西干吗呀,什么客气呀,什么礼节呀,哼,老土,她说。
是,我承认我身上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说。
她绷着的脸突然松弛下来,扑哧一声,笑了,笑得一双黑玉似的大眼珠笼起了一层雾。
我说:你可千万别对我笑。
为什么?她问。长长的睫毛一忽闪一忽闪的,像抖擞着翅膀飞着的蝴蝶。
我说:因为,你的笑里面有毒药。
德行,她又笑了。
这顿饭,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截止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的名字——翩翩。一个跟天空跟白云跟小鸟和翱翔有关的名字。我所了解她的只有这么多,而我的所有档案秘密,她却都掌握了,包括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做爱以及第一次带女孩子去妇产科的全部细节。靠,昆虫真不够朋友,竟敢出卖我!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俩反倒默默无语了,就这么相互凝望着,凝望了很久很久,久得仿佛有一百年。不是不想说点什么,而是不知道说点什么,优柔的香气,在我的周围流淌着,很微妙,也很凌乱,我知道,那是她的味道。
我几次张张嘴,想问她个问题,却总是问不出口。翩翩的眼风似乎始终在我脸上徘徊,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她说。
我想否定,可是翩翩尖锐的目光一落在我的脸上,我就慌了。我估计我这人要是在白色恐怖时代被捕,严刑拷打都不怕,就怕美人计,来个窈窕淑女往我跟前一站,我就什么都招了。这不,翩翩尖锐的目光一落在我的脸上,我便坦白道:我一直想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
她愣了,愣了半天。我结婚,我结什么婚,我跟谁结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问这么没头没脑的问题?翩翩说。
那你手上戴着的这个……我指了指她戴着的订婚戒指。
哦,这个呀,她突然笑了起来,但又戛然而止,那笑犹如鱼儿在水中游过,没留下任何的痕迹。我结婚怎么了,难道你以为我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吗?她眉头紧皱地说。
我心里骤然刮起一阵寒风,落叶飘零。我竟失落得要命,仿佛我是个孤寂的夜行人似的,尽管我有堇子和西西。不过,我还是特虚伪地说:谁说你嫁不出去来着,像你这么妩媚,恐怕连上帝都想娶你。
不理你,我走了,她说走就走,走到门口,她回过身来,问了我一句:你真的没见过我吗,以前?
我摇了摇头,又想了一想,最后还是摇摇头。
我却见过你,你那时候好可怜啊,她说。
怎么可能,我为什么不记得?我问道。
她说:我还跟你说过话呢,你忘了,在从武汉飞达北京的航班上,我问过你——你是哪个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