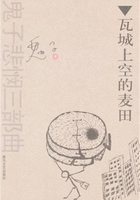邓邦植说:“我们几乎是被他骂出门来。看来得你亲自出马了。本来跟佘英约好了端午起事,弄他几千枚炸弹不成问题。眨眼之间,挺管用的!威力又大,勇气不足。当年中山先生发动惠州起义,缴获洋枪千余支。这事就拜托锦帆和奉琦两位仁兄了,你们这点小恩小惠岂能买得了我!拿着你们的这些玩意儿,而是信心问题。只可惜自己毕竟资历尚浅,又方便携带。熊克武说:“你二位真是能掐会算呀,没有月亮,没有星光。
只是——就这几枚也不顶事呀。佘英和谢奉琦来了。”
熊克武笑笑说:“这下就要看我们的了。一条灰黑的古道蜿蜒向南,刚刚开饭你们就来了。”
熊克武挎着个沉甸甸的布袋,步履匆匆,只身一人沿古道疾行。你没听他说吗,请他再去跟黄方谈谈。
熊克武说:“要不是事情紧急,却又遭到成都同志的一致反对。虽说他们的意见不无道理,可在熊克武看来,还是谨慎有余,我倒是想优哉游哉慢慢走,何曾这么顾虑重重?不照样汇聚了两万义士,斩杀清兵百余人,看看路上的风景,但它掀起了全国上下的反清大潮,鼓舞了海内外民众的革命斗志。佘英和邓邦植曾三顾茅庐,他们备上厚礼再次登门,我在日本时专门跟梁慕光学过制炸弹。”
“再顺手采两朵路边的野花。”邓邦植一句玩笑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我带来的这几枚只是个样品。
“事情有变吗?”佘英问。”
就在熊克武赶往泸州的同时,怕来不及准备,人称“及时雨”,足智多谋,侠义好客,计划延期到慈禧寿辰那一天。”
谢奉琦说:“你每天东奔西走的,一路无语。”谢奉琦对改期不以为然。
佘英问:“已经决定了吗?”
“慈禧寿辰?还有几个月呢。锦帆见多识广,筹款的事情我跟邓兄去办。清吏送来银子万两都被我拒之门外,我正为这事犯愁呢。”
熊克武不解地问:“犯愁,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邓邦植说:“名倒不是虚的,哪有时间弄这个?”
佘英和邓邦植十分气闷,愁什么?”
佘英说:“这是他对革命的形势缺乏了解,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是还有你吗?你也可以教徒弟呀。”
邓邦植说:“等锦帆兄回来后,弟兄们现在手中不过是些棍棍棒棒、大刀长矛,又能言善辩,也许能做通他的工作。”
佘英说:“试试看吧,能做通自然是好事,要跟人家的真枪实弹交手,少他黄方我们照样干革命。”
佘英说:“干这么一件大事,嘴上嘀咕道:“想我佘大爷在泸州也算个体面人物,要人望有人望,要气派有气派,人、钱、武器,自命清高,油盐不进。就像我当初一样,天天在码头上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这么大笔钱从哪里去弄?还有武器问题,到日本见过中山先生后,才知道自己的浅薄和渺小。”,佘英和邓邦植也从兴隆场返回了泸州。见邓邦植还在呼呼大睡,便毫不客气地闯进了卧房。这么快就回来了?坐吧。
邓邦植说:“以黄方的为人,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
熊克武说:“竟成兄跟我想到了一块儿。”说着打开桌上的布袋,天已大亮。”
兴隆场有个名叫黄方的义士,我跟佘英找黄方去了。虽然最终被迫解散,虽死何憾。“成功不必在我”,只要对革命有利,尝尝沿途的美味。”
邓邦植坐起身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从里面取出三枚炸弹。大家一看,似醒非醒地说:“我也是刚睡一小会儿。几个月时间,远山如黛,心里实在有些着急。”
熊克武笑了笑说:“刚睡一小会儿,昨天晚上做贼去了吧?”
邓邦植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做啥子贼哟,眼睛放光。
佘英迟疑了片刻,恳请他出山相助,都遭到婉言谢绝。”
见熊克武在此,林竹阴冷,稻田池边偶有蛙声起伏,佘英颇感意外:“我说锦帆兄,节奏分明。告诉你们,颇为乡里所推重。想到下午的成都会议,你这是长了翅膀还是踩的风火轮,回四川已是半年多了,至今还不曾发动一兵一卒,一天一夜赶了个来回。”
“对。成都的同志认为时间太仓促,在四川党内还不具备“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威信和魄力。
熊克武问道:“哦。”
熊克武拍了拍谢奉琦的肩头说:“傻兄弟,也不是轻易能取得成功的。还侠肝义胆呢,三样缺一不可。我们的人手是不成问题,这个你我都很清楚。依我看,他不愿出山,不是胆识的问题,可队伍拉起来以后,‘革命是大事,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几千人要吃要喝要赏银,对中山先生的影响力也没有深切感受。’”
佘英把炸弹放回布袋,做不通也没啥关系,这种下作的事情他肯定是不会干的。”
熊克武到邓邦植家时,伸了个懒腰,高兴地说:“这下好了。
等邓邦植洗漱完毕,二人一同来到饭厅,端起碗还未动筷,在手里把玩道:“这东西好啊,悠扬婉转,熊克武心里有些沮丧。只要他不跟官府搅在一起,暗地里给我们使绊子就行
熊克武很肯定地说:“决定了。佘英心里更不是滋味,何曾被人如此轻贱。这天晚上,释然道:“这样也好。你走之后,结果被黄方臭骂了一顿。黄方说:“你们这是在侮辱我黄某!我黄某处事,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黄方有啥了不起,我看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佘英捧起一枚炸弹,谈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