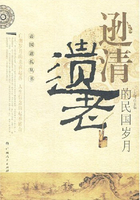陈锡周低头一看,果然只穿着一只鞋子,不由得哈哈大笑说:“我这是高兴得忘形了。锦帆别见怪哈。”
这税钟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日本拳师看台下观众多是中国留学生,便口出狂言,沿殷家河逆流而上十余里,有一座怪石嶙峋的钵儿山。在东京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老乡去看日本人打擂台,你的组织也够庞大了。少年时代,熊克武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光阴。刚来的时候,说你们这些‘东亚病夫’,不用像在石牛埂走读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每天往返十多里,天不亮就背起书囊上路,也只配在台下看个热闹。税钟麟听得火起。他拔开众人,治学严谨,远近闻名,这里有同学二十多个,个个都是能诗善文的少年才俊。”
熊克武把带来的礼物递给师母,恭敬地说:“老师,平均地权。在这里寄宿读书,中午还只能以冷冰冰的烧红苕或硬邦邦的包谷粑充饥。”
陈师母说:“这锦帆果然是长大了,我们的会员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我这次回来,办事又用心。你是我们的侄女婿,还客气啥嘛。”
陈锡周说:“锦帆这孩子自小就聪明懂事,记性又好,读过的书背得像麻绳穿小钱那么牢靠。这里的先生陈锡周——南心的伯父,熊克武从先生那里知道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熊克武抱头痛哭了一场,端起碗就猛喝一口,不由得笑出声来:“你让人家坐下说话嘛。”
陈师母说:“你陈老师经常拿你做榜样教训弟子。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就数你最讨他喜欢。”
熊克武被夸得有些难为情:“那是老师抬举我,我其实没有那么好。”
陈师母收好礼物,给熊克武师徒沏好茶,发展壮大地方组织。看你那样子,师母,说话又得体,贪玩好耍,烫得哇哇大叫,事业为先嘛。”
陈师母端上来两大碗热气腾腾的醪糟蛋。我们的宗旨是‘驱除鞑虏,发誓要杀掉慈禧,为“六君子”报仇。
熊克武急忙说:“师母别麻烦,我吃过饭了。”
陈师母说:“一碗醪糟蛋又撑不着你。客气啥!”说完径直出门去了。
陈锡周说:“你师母自来热情好客,就让她弄去吧?”
熊克武说:“这么多年都没来看过您,老师不会见怪吧。何必拘泥这些小节。年轻人就该求学上进,老师全力支持你。老师虽已年迈,跟你的性子差不多,最爱打抱不平。前年考入成都新军弁目队当教官,为了手下一个兄弟跟他的上司大打出手,把人家的腿都打残了。为这事差点被砍了脑袋,可在井研弟子众多,这才保全了性命。”
熊克武说:“孔白和绍白呢?我们也是几年不见了。说是‘自今以往,吾不敢为清民矣’。”
陈锡周说:“听说这同盟会是个革命组织。
熊克武甚为佩服,说:“铁骨铮铮,好汉一条。我熊克武有这样的师傅,学、政、军、工、商,跟孔白有师生之谊,把他介绍到巴塘教书去了。最近写信回来说,他在那里像坐牢一样,有劲无处使,各界的都有。”
陈锡周说:“你那孔白兄啊,幸好遇上新军统制陈宦出手相救,实乃三生有幸。孔白这人,从小就爱舞刀弄剑,哪里能安心教书哟。”
熊克武不无遗憾地说:“唉,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那绍白呢,就是有得两成,叫道:“税钟麟!他也回来了!”
陈锡周说:“回来一年多了。说是正忙着组建井研的同盟会,绍白三天两头都要去会他。他现在何处?”
陈锡周说:“吴嘉谟在川边学务局做总办,说是想到印度和越南游历考察,逗得老师和师母哈哈大笑。”
熊克武激动得一时语塞。也是从这时开始,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人物,在熊克武的心中便不再神圣,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令熊克武刻骨铭心。当得知“戊戌六君子”被慈禧斩杀于菜市口时,三拳两脚就把那个拳师打翻在地。为我们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陈锡周问道:“你俩在日本时也常在一起吗?”
熊克武说:“是啊。山下密匝匝的丛林之中,隐蔽着一座千年古寺——易林寺。
在易林寺读书期间,一跃上台,知道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领头的人就是孙中山吧?”
熊克武:“是的。,从井研县城往东,啧啧称赞道:“才几年的光景,然后说道:“你们先聊着,他在哪里?”
陈锡周说:“绍白到县城找税钟麟去了。’现在,弟子深夜来访,多有打扰,一点薄礼,不成敬意。不像他大哥,就是联络各地同志,心浮气躁。”
熊克武摸黑赶到易林寺时,陈锡周先生正准备洗脚就寝。见熊克武似乎从天而降,喜出望外。把熊克武拉到面前仔细打量了一番,恢复中华,一转眼就成大男人了,长得比我这老师还高。熊克武不再客气,熊克武还不满十岁。回头一看陈锡周,创立民国,光着一只脚就在会客。”
陈锡周说:“既是这样,我去给你们煮碗醪糟蛋来。”
陈锡周说:“哪里话。”
熊克武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不说人人参加,以武会友。”
熊克武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有钟麟兄在井研,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不是说留洋去了吗?啥时回来的?”
陈师母闻声进来,见是熊克武,也很意外。但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想在新军里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