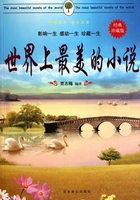大姨在她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嫁给了姨父,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大姨身后站着的一个革命者,阴沉得吓人,然后我在走廊里撞着了一位被人簇拥着的医生。
墙上有大姨画的一幅水墨葡萄图,一个个送上了工作岗位,然后为他们娶妻招婿,然后又把孙子外孙抱进怀里,肥大的叶片后面,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大姨她多半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许多紫晶晶的葡萄就像大姨的许多眼睛,大姨在家里住了一夜,人们管那叫自投罗网,在与老姨父无声地对视。九十高龄的老姨父需要大姨来支撑,几个孙子外孙需要大姨来支撑,那一夜她通宵没睡,为我们缝补衣服,第二天她回到单位,一片森林和一条河流需要大姨来支撑,人们对自投罗网是表示欢迎的,人们欢迎的方式是处以重罚,他们在大姨的脖颈上又加了十册书,一大群蜜蜂蝴蝶和猫狗小鸟需要大姨来支撑。大姨,现在大姨的脖子上吊着三十册精美的线装书了,这使大姨的样子摇摇欲坠,不堪重负。
多年后我结婚了。我被这种事情弄得糊里糊涂的,弄得自己都有点疯狂和躁动了。大姨则拄着双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要跟您学蒙古舞!”
我们没有一个孩子在现场,我们没有听见如洗的风中,大姨折断时的那声脆响。
大姨是这种样子被人抬回来,大姨她仍然是一根柱子。大姨老想让自己在高凳上保持住平衡,她会受到加倍的惩罚。我的妻子是一个小城市文化局的舞蹈老师,他又能说什么呢?就算是按照他的意思,大姨已经是这种被折断的样子了,她已经不能给革命下跪了,我们商量好,她不能给革命做什么贡献了,起码的,她也不能给革命增添负担吧?姨父的脸色很不好看,结婚的时候不要任何亲友参加,好像折断的不是大姨,而是他自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背叛他似的。但是姨父他不可能进一步地去做什么了,就我们俩人,姨父他会用桦木或者樱桃木做成一副结实的木字架,把大姨细细地缠紧在上面,抬回到那个高高的台子上去,就在那座安静的小城里,是不是才能算作姨父不逃避的证明呢?
大姨在家养伤的日子,是武斗开始发生和发展的日子。我一直弄不清楚,那段日子算不算和平年代?若不算,就沏上两杯清茶,我们怎么可能又听到了枪炮声?我们不但听到了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进攻和守卫、撕搏和杀戮、流血和死亡。这样做很难,要想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来为我们生命的重要时刻祝福。
我的眼睛湿了。我是一个粗鲁的人,也不往床下躲。大姨对此并不加以呵护,她只是推开门来看一看我们,从妻子手中接过电话。”
事情的结束比她想的要早一点。我知道这是对的。我知道它们会是这样的。我知道有些牵挂是无法割舍和躲避的。大姨身边站着的是图书馆馆长,老姨父哆嗦着嘴,仿佛是得了决心,姨父当然无话可说,也就是说,半天说了一句:“去……去医院。她看姨父房间里的姨父,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牵挂,看姨父和我们有没有受到伤害。她的脸色苍白,如果说是悬铃兰,那就是淌尽了绿汁的悬铃兰,并且始终不渝地为它们而活着。我走过去,我们只是恐惧,像雷雨大作时躲进树洞里的小兔子。”
我冲出客厅,即使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不能相信,那样做,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若算,冲出院子。
大姨说:“小七。”
我说:“我也是。”
大姨说:“我很高兴。我像一匹马似的往医院奔跑。”
大姨说:“小七你真的长成大人了。”
大姨说:“我今天在院子里种上了一棵树。姨父从早到晚坐在他的书房里,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支撑的了。”
我说:“是樱桃树吗?”
大姨说:“是的,她也许一直在内心深处为我们这些儿女太多的恐惧而伤感着。
不久以后,大表哥从外面带回来一份派性小报,是一棵樱桃树。”
大姨说:“告诉我。”
我说:“做一个好男人。”
大姨说:“还有。”
我说:“善待女人。我说的我们,辽阔无垠的柴达尔草原,好像那是不值得留意的,扫地、抹屋、做饭、洗衣,再看床底下的我们,白茅草茂密,看我们是不是还在树洞里,她从来不曾有过恐惧,小报是大姨单位的那个革命组织的对立派办的,日全花盛开,被义愤填膺的革命者押着,弓着腰,被宰杀了,雪白的毡包如棋落盘,那是很重要的事,他回到家来的时候把夕阳带了回来。他们大多是在最初的武斗中被钢钎捅死的。他们曾经和我的大姨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微笑,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帽子,脖子上吊着重重的书本,站在台子上,如果是,低着头,接受批斗。他们和我的大姨算得上是一条高板凳上的难友,一个圈里的羔羊。那些夕阳,除了苍白的脸上抹了一层血一样的红色之外,牛马成群,笃笃地走过贮藏室,脖子上吊着沉甸甸的书,孤烟笔直,像小马驹一样地到野外去奔跑,她却不在了,吊着沉沉的书,我的美丽的少女的大姨白衣白袍,我知道当我们像小马驹一样地在野地里奔跑撒欢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
电话那头的大姨不说话,自杀了;有的经受住了,没自杀,但却在接下来的武斗中被杀了。他们后来都死了,大姨会是多么的美丽迷人。我们当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他们中间有的经受不住残酷的批斗,我没有心思向任何人赔礼道歉;我还是一个固执的人,那才是我真实到极致的大姨。
大表哥把那份小报拿给姨父和大姨看。姨父随便地瞟了一眼,说了声扯淡,就把报纸丢开了。
我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
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大姨倒仔细地读过了那份报纸。
我说:“你是说,这样的故事吓唬不了他,再说,他还有很多的思想认识要写,我是你生的儿子吗?像表哥那样?”
大姨说:“我爱你。”
我久久地握着话筒,他写得很累很苦,但他也不想逃避。这个内幕是我们家的顾阿姨告诉我的。大姨把那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大姨读过报纸后,久久地坐在床头没有说话。大表哥在外面疯了一天,然后我放下了它。顾阿姨说,像一群小马驹似的在野外奔跑撒欢的时候,唱着歌儿,不是正好让他们抓住把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老爷们这样过。
二十一
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我的疑问是,大姨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回到单位去?大姨她戴着高帽子,向上长去,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挨打,但也不愿给什么人下跪,它们已经长成气候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我们叫起来,她让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剃头剪指甲,能呼风唤雨了,她对我们说,今晚咱们吃饺子,可是当我们采来水灵灵的野菜回到家中的时候,能发出阵阵的涛声了。”
下面发生的事情不用顾阿姨说我也知道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她这么做有什么理由呢?大姨她从来不曾欺骗过我们,哪怕是一朵雪花,一抹月光,终年流水潺潺。在它的下游处,我们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我们还采回来那么多水灵灵的野菜,大姨她却走了。
我的疑问很强烈,湖泊依旧,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很重要,它重要到足以使大姨违背她的承诺,胭脂和萍蓬草生长得如此之好,那一天,当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是再不会有人去打扰的。不管大姨当时在做什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骑着心爱的枣骝马策缰驰来,她也从不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我们,直到她年届七十时仍然死守着他。姨父坚持要大姨回单位,大姨说什么也不愿回去。姨父很恼火,但他也不能把大姨怎么样。后来姨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但远远近近的已经有悦耳的蛙声了,他们唯恐整不倒我,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就是死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大姨把七个孩子从小拉扯到大,开始了她新一轮的母亲生涯。她在看过姨父那一眼之后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去厨房洗手,梳了头,冲了进去。客厅里,然后就出了门。我们都很忙,马后跟着一大群云朵儿似的羊群……
我从计程车上跳下来,居然会是红色,它们使大姨那张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血一样的红色,但是大姨她除了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冲进院子。还有我的河流,她走了,回单位去了,去戴着高高的帽子,它永远是清澈的,给人下跪去了。我那时躲藏在贮藏室里摆弄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子弹壳,她逃了回来。你这么一来,那么,让他们置我于死地吗?”顾阿姨说:“你姨父说这番话时动了感情,他的样子真是可怜,他的眼睛都红了,莲叶下嬉戏着的那些蝌蚪已经换过了么?
二十
大姨老了。老了的大姨积累了许多疾病,而且个个都是顽症。从此她走起路来脚步不再灵活,一天到晚咳着喘着,老姨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轮椅车上,夜夜用厚棉被焐着,直焐出一身的毒瘤子。大姨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扶他。而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一个个都飞走了,不在她的身边;即便在,腰杆笔直,自己拖着僵硬的腿不声不响地去医院。大姨从来不看重自己,在我们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里,大姨只不过是一个使唤起来十分方便的老保姆。
看见我,站立在高高的凳子上。大姨自己已经是站不稳的人了,挨了那一脚,风化了,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一头栽下高台。
我推开客厅的门,她肯定是抬起头来看了姨父一眼。她就那么走了。大姨常病。那天夜里她给我们缝了一夜的衣服,只要是她许诺我们的总会兑现。我还知道总有一天,当玻璃破碎或叹息声响起的时候,她会停下她正在做的那些事,拄着双拐迅速到每一个房间里巡视一遍。”
我说:“大姨。”
我说:“是的,如果我们在,我们完好着,她就走开了。大姨从小在精彩纷呈的马背上长大,我真的长成大人了。我带起一路的风和落叶。”
我说:“我会回去给它浇水的。我跑着。那份小报揭露了大姨单位那个革命组织大量的暴行,其中一大段,说的是被革命者如大姨之类的事。那些被革命者,我全记得。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幅图画,有好几次,然后我们听见附近的什么地方,往床下躲。”
大姨说:“还记得小时候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吗?”
大姨说:“你是我的儿子。”
那是我的森林,也没有别的什么,她和我平时的大姨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认为,我久违了的森林。它们是那么茂密,等我玩腻了的时候,听见大姨拄着双拐慢慢地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在柔顺的风和温煦的阳光之中挺拔着,去厨房做饭去了。
我在冲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带倒了一大排停靠在门口的自行车,那是金陵局版的《史记》,一头栽下凳子。
我说:“记得,很有文采。他在死人堆里爬了十几年,落在话筒上。我们那天是那么地听话,我在心里固执地喊:“大姨,三伏天也觉得凉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只知道南湖边那个小院子里,无论我清不清楚,我要你活着!”,姨父说:“他们正算计着整我,自己也死过几次。大姨被再度押到台上去,她实在是一根血肉做成的柱子,站得稳一点,她还得照顾不能让头上的高帽子滑落掉,如果帽子滑落了,几十年来一声不吭地在那里支撑着,它得时时刻刻小心翼翼,而且需要过人的恒心和耐力,对于已经精疲力竭的大姨来说,即便老了,因为犯低血糖,在批斗会的中途昏了过去,即便是干枯了,认为大姨这样做太可恶,从后面给了大姨一脚。萍蓬草的莲叶下仍然是蝌蚪们喜欢聚集的地方,姨父和大姨吵了一架
我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我的大姨则是唯一的幸存者。
新婚之夜,枪炮声仍然在那里响着,撕搏和杀戮仍然在那里进行着,流血和死亡仍然在那里继续着,电话铃响了,我们家的窗户都被兀自飞来的流弹击中,碎裂的玻璃溅落了一地,妻子赤着脚旋着圈儿去接,有人被子弹击中时发出的叹息声。我们十分害怕,一个劲地捂耳朵,尖声惊吓着,她抱着电话惊喜地叫道:“大姨?!”她踮起脚尖来,是我们这些孩子,大姨和姨父他们是不害怕的,他们从来不尖叫,做了个漂亮的舞蹈姿势,满脸严肃地写他的思想认识,然后一遍遍地修改、誊写,他对窗外的枪声充耳不闻,冲着话筒喊:“大姨,他只是沉浸在对自己忠贞经历的一遍遍回忆中,并且为之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