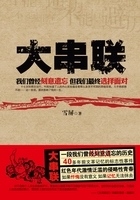这一晚躺在炕上,谢晚桃几乎整宿不曾合眼。沐房之中发生的那一幕,像鬼影一样在眼前不断地盘旋。
没有证据,她眼前似乎一片迷茫,当然只能猜测。但事实究竟是怎样,其实她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那场大病于她而言,完全是一场新生,而现在看来,显然重新活过来的人,不止她一个。
谢晚桃侧过头去看了一眼身畔的早桃,她阖眼安睡,呼吸沉静悠长。
嗬,如果她的猜测成真,老天爷给她安排的这一场重生,便更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意玩笑,而她念念不忘的姐妹情,现在看来,更是个愚蠢无比的笑话。而早桃呢?她心中到底怎么想,她又预备在这个玩笑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再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身边空空如也,冯氏、四郎和早桃都已经不见了,唯有谢老三还裹在被褥里,鼾声如雷。
以酒为生,有时候也真是一件爽心之事啊,至少,谢老三想喝就喝,想骂就骂,随性而至,肆意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不是也算是个性情中人?
谢晚桃知道她今天是起得迟了些,只怕那早点摊子已经收了。于是赶紧坐起身,冲着谢老三的背影习惯性地翻了个白眼,三两下穿好衣裳下了地。洗漱干净后走到前院儿,果然发现门外用来摆放包子稀粥的桌子已经撤了,甫一转过脸,恰巧看见早桃立在东墙根下,正朝自己这边望过来。
她手中捧着一簸箕晒干的枣子,看那模样,应是正在清理枣子上的浮尘。两姐妹各自站在原地,不说不动,只静静望着对方,目光在空气中碰撞,火光迸起,似乎发出“铛”地一声脆响。
少顷,谢晚桃率先收回了眼,不疾不徐走到早桃面前,弯起嘴角叫了声:“姐。”
早桃如释重负般立刻展颜一笑:“还以为你仍在生我的气……早起都没敢叫你。”
“姐,你也太小看我了!在你眼里,我就那么小肚鸡肠?”谢晚桃嘻嘻一笑,然后小心翼翼地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之前爷爷不是让爹跟着大伯二伯上山猎野物去吗?怎么他还在炕上躺着?爷爷就由着他这么懒下去,也不说管管?”
“嘘,小声一点。”早桃瞬时皱起了眉头,“爷爷那性子,你还不清楚吗?可巧这两日家里又有客,当着那涂老先生的面儿,他便更顾惜自己的脸皮,怎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教训爹?……你过来,让我瞧瞧你的脖子。”
她说着便将手中簸箕搁在倚墙而立的木架子上,伸手轻轻掀开谢晚桃的衣领,那一片白腻的肌肤上犹见五个指印,隐隐透着些青紫。
“还疼吗?”早桃的手轻柔地从指印上拂过,眉毛不自觉地揪到一处,“我心里内疚得紧,想着你昨夜肯定被我吓坏了,没睡好,早上也不好叫你起来支摊儿。我……我真是发了疯了,把你伤成这样,往后,你怕是再不敢跟我一起洗澡了。”
“哈,姐真是瞎操心。”谢晚桃不动声色地朝后退了一步,“你忘了陆沧说我什么来着?他说,我是这松花坳一霸,天下就没有我害怕担忧的事,这点小伤,又不疼又不痒的,算得了甚么?哎姐,你若实在心里过不去,要不,你也让我掐一下?”
“行啊!”早桃真个把脖子凑了上来,“你掐,掐了我心里好过些。”
“哎呀!”谢晚桃赶紧推她一把,“我跟你说笑,你怎么还当起真来?姐那是想事情失了神,自己在干什么恐怕都不知道,可这会子,我却是清醒得很,要真掐你一下,那我成什么人了?好了好了,姐,这就不算是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咱们俩从没打过架红过脸,为了这一点小事,还没完没了了?别老在这事儿上打转,行不?”
早桃垂首不语,过了片刻,无声地伸手过来,拉住了谢晚桃的手。
她垂着眼皮,谢晚桃无法看清她的眼神,被她攥着的手心里,冒出一层细细的汗。
半晌,她终于稍微用力,把手抽了回去,摸摸鼻子道:“姐,你这是忙活什么呢,要我帮忙不?”
“不用不用。”早桃也收回手,将那簸箕枣子复又端了起来,“娘让我四处掸掸灰,我见这枣子晒了好几天,落了不少尘土,就拾掇拾掇,说话这就弄完了,倒是……”
她顿了一顿,抿唇道:“倒是有件事,你可不可以帮我?”
“好哇!”谢晚桃一脸诚恳地点头,“咱们姐妹俩,还说什么帮不帮?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那我就先谢谢了。”早桃嫣然一笑,“是这么回事。早晨袁叔家的李婶子来找我,百般央我帮他们家袁奕做一双鞋垫。可是你知道,替二伯娘做的那件肚兜子我还没绣完呢,哪里忙得过来?你手脚快,要是闲着没事,就帮我把那鞋垫做出来好不好?李婶子赶着要呢。”
“行啊,那有什么问题?这会子我去找陆沧,等吃了午饭,姐你把尺寸给我,没两天我就能做好。”谢晚桃痛痛快快应承下来。
“啊,还有……”早桃想了想,又接着道,“最好别让家里人看见,我怕二伯娘又找茬。”
“知道。”谢晚桃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转身就朝大门外走去。直到估摸着早桃应是再瞧不见自己,才猛地停住脚,双眼瞬间如同冰窟。
鞋垫?哼,滑天下之大稽。
离开谢家,谢晚桃先去了一趟半山腰,在陆沧的小院儿门口敲了半天,不见他来开门,又踮起脚尖朝里面瞧了瞧,发现门窗都是紧紧闭着的,心下便有些纳罕。
陆沧平日里轻易不会去什么远地方,即便进山三五天,院门往往也大敞着。反正在这松花坳附近住的都是熟人,也不必担心会丢东西。
可今天,他不但锁了院门,就连晒在院子里的衣裳也都全收了回去——这家伙惯来不拘小节,有时候洗干净的衣裳在院子里晾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记得收,每每都是谢晚桃终于看不下去,才帮他收进屋里。今天这是怎么了,转了性子了?
谢晚桃来找陆沧,原本是想让他陪着去山谷中看看那群獐子。但既然这会子他不在,之前又曾千叮万嘱,谢晚桃便只能将这个念头暂且压下。这些日子,松花坳里的流言好不容易逐渐消停下来,虽说她心下一片坦然,但谣言这东西,永远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还是能避则避的好。
她立刻从半山腰上下来,径直回了家,帮着冯氏做家事。不一会儿早桃也回来了,将谢晚桃拉到僻静处,细细将鞋垫的尺寸说与她听,又给了她两块靛青的厚布。谢晚桃倒也不含糊,取了针线,自寻了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认认真真忙活起来。
临近午饭时,其中一只鞋垫已经做了大半,谢晚桃觉得有些累,便将东西仔细收好,慢慢悠悠晃出院子,打算松松筋骨,一抬眼,便见涂善达独自站在院子外。
这涂老先生来到月霞山不过两三天时间,谢晚桃的日子始终避免与他碰面,说白了,也就是不愿给他留下太多印象。所幸谢老爷子是个十分好客之人,每日价不是邀涂善达进山赏景,便是与他在上房中盘腿而坐,温酒叙旧。两人许久未见,好似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堆,因此,除了每天吃饭时,涂善达甚少出现在众人面前,那件事,也就自然再未提及——至少,谢晚桃不曾听见。
如今见涂老先生就一人站在门外,她自然不愿主动上前打招呼,忙缩了缩身子,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背后绕进院子里。
就在这个当口,早桃手里拿了一件薄衫,脚步轻快地从院子里跑出来,直奔到涂善达跟前。
“涂老先生。”她眉眼含笑,一脸乖巧地仰脸道,“您披上件衣裳吧,山里风大,您在这儿站着,弄不好便要着凉的。”
“好,好,谢谢你。”涂善达垂下眼,冲早桃点头笑了笑,“你是早桃吧?常听你爷爷说,他这八个孙子孙女中间,你是最听话懂事的一个,如今一见果然如此。小小年纪便能如此为人着想,不错,不错。”
早桃似乎有点害羞,微微低了头:“涂老先生不要夸我了,我也只不过是希望能帮着家里人分忧。您是爷爷的好朋友,又山长水远来探望他,谢家自然该将您照顾周到,我也不过是略尽些力罢了。”
“唔,你还有个双生的妹妹,对吗?”涂老先生没接她的茬,不经意转换了话题。
“是。”早桃点了点头,仿佛很苦恼地叨咕了一句,“成日价往外跑,除了玩,便再不会别的,这会子又不知溜去哪里了。”
“你们都是孩子,玩心大一点再正常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涂善达捋髯而笑,“倘你们有兴趣,待闲时,可让你们的爷爷带你们来京城转转。那地方到底繁华些,好玩儿好吃的东西不计其数,小姑娘小小子们最是喜欢。老闷在这山里,把人也要给憋坏了,四处走走,也好长些见识啊!”
“好!”早桃脸上露出两丝欣喜之色,使劲点了点头,继而又有些懊丧地摇了摇头,“还是算了,家里那么多事情,爷爷哪里走得开呢?”
早桃这姑娘向来温婉懂礼,若搁在平常,谢晚桃绝对不会对她的举动产生任何怀疑。然而,在经历了前一晚沐房中一事之后,再看到这一幕,她心中已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
早桃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那些缠绕于脑海中的记忆,光是回头想想已然足够令人心生惧意,难不成,她还想再来一次?为了那样一个男人,何必?
嗬,若真是如此又如何?或许你仍然憎恨我,但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与你同嫁。
谢晚桃笑了一笑,扭头便要走,恰在这时,万氏的声音从院子里传了出来。
“四丫,站在那儿做什么?你这孩子,最近这几日,又偷起懒来。快进来帮我煮两锅豆子。”她一边说,一边走了过来,拉住谢晚桃的手腕,同时,遥遥冲涂善达点了点头。
“哦。”谢晚桃应了一声,扭头看了早桃一眼,随着万氏走进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