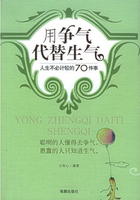罗老头知道她的脾气,只是低头沉默着剁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剔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净骨头,这也是不能随便浪费的,没事的时候,拿两根骨头炖萝卜白菜也是人人都爱的。
罗天都便暗地里嘀咕,姚氏说话也不嫌寒碜,明明那猪多半都是罗名都喂的,她可是天天看着罗名都吃了早饭就背着篓子出门打猪草,每两天就要烧一大锅猪食,只有分家的这几个月才是姚氏接的手。算起来这头猪杀了,她们家分十几斤肉真不算过分。
可是姚氏却不这样想。当初分家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分猪的事,既然没提,那就全是她的,她的东西怎么可能拿出来便宜罗白宿一家,她便站在门板前面,一双眼冷得像腊月的寒风似的直朝东屋瞪着。
要是东屋的那几个当真这么厚脸色敢出来拿肉,她就敢大过年的跟他们吵!
“大郎,还不来把肉拿过去趁早腌了?”院子里罗老头又在催了。
“唉,就来。”方氏应了一声,她不想和姚氏打交道,便让罗白宿拿出去买肉。
“上好的五花肉,肉铺里都卖一百多文一斤,家里如今没钱,要是卖了还能给白翰凑点明年赶考的路费。”姚氏挑起了眉,“哼”了一声道,“大郎,这一块可有十几斤,你是打算拿钱买啊还是拿粮食换啊?”
“闭嘴吧你!”罗老头闷了半天,终于也忍不住了,道,“都是一家人,杀了猪给大郎一家分点肉又怎么了?我给白秋砍肉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罗天都一听就知道坏了。罗老头一片好心,却成了惹怒姚氏的直接导火线。她现在可算摸清了姚氏的心理,姚氏心里头恨着她们一家,说到底还是因为罗老头,姚氏心里一直在跟着罗白宿的亲娘较着劲。罗老头如果对她们一家态度冷淡倒也罢了,若是像这样公然袒护她们,就算没事姚氏也会闹得天翻地覆。
“白秋是我生的,我养的孩子别说就是吃几块猪肉,就是要吃我身上的肉我也愿意给,别人家的,休想从我手里拿走一分一毫。”姚氏冷笑着道。
“你呀你!”罗老头指着她“你”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一句整的,最后才道,“你的心到底是咋长的?怎么到这个时候还说这种混话?大郎孝敬了你这么多年,你一句别人家的多伤孩子的心!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有儿有女,用不着别人来孝敬。”说起孩子,姚氏的声音也尖锐了起来。
她这辈子的怨都是从孩子这上头起的,就算她的心是豆腐做的,这么些年也足以被磨成块大青石了,又坚又硬。
得!又绕回去了!罗天都扯了扯罗白宿的袖子,悄声道:“爹,咱还是进屋吧。”
这肉就算拿回来了,吃着也憋气,还不如天天清水煮萝卜白菜来得舒坦。
方氏在屋子里听得明白,又看到罗天都和罗白宿都躲回了屋里。她想着姚氏说的那些话,虽然早已经听习惯了,可是每听一次,还是会觉得伤心难过。上辈人的恩怨,到了她们这里就成了解不开的死结,无论她和罗白宿如何做个勤快孝顺的儿子媳妇,到底还是输给了姚氏心里的怨恨。
她性子好强,看明白了这一点,便想争一口气,不理姚氏。可是一想到两个孩子一年到头都没吃上几口好吃的,这都要过年了,爷爷奶奶家杀猪,她们都尝不到一口,这心呀就像腌在缸底的陈年酸菜,酸得不着边了。
“要不,咱们拿钱少称点?”方氏便跟罗白宿打商量。
罗白宿是个疼孩子的,点了点头,道:“多少称几斤吧。”
头前买地的时候,去了十两银子,后来买种子打农具买年货,零零碎碎又花了两吊多钱,方氏便将剩下的五两银子兑了二两,换成铜钱锁在箱子里。这会儿她便开了箱子数了又数,方才数了五百文钱,拿在手里摸了半天,到底又再多拿了一百文,
方氏这回也没再让罗白宿去,自己拿件旧衣服将钱包了,去了院子里。
罗老头早将那块肉用稻草穿了,搁在一旁,看见方氏出来,便拎了起来给方氏。
不想姚氏却跳了起来,将那块肉一把夺了过去,对着方氏恶狠狠地道:“一百文一斤,想吃就拿钱来,没钱就回去吃萝卜白菜!”
“你闹够没有?都快过年了,你就不能消停点?”罗老头忍无可忍,冲着姚氏吼了一嗓子。
“罗全,你个糊涂蛋,你把人当儿子,也不看看人家有没有拿你当老子。白翰要说亲,家里没钱下不了聘,老大一家手里攒了十几吊钱,也没说拿出来给白翰娶媳妇!就这样只认钱不认人的东西,你还一心一意偏护着,你才瞎了狗眼!”
罗天都见两人越吵越不堪,颇有些同情方氏,也不知道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嫁进了这么户人家,糟心透了。
方氏都想抱着钱回屋,不买肉了。她有些后悔,怎么上回去镇上的时候没想着称几斤回来的,横竖都是要出钱的,她上哪买不是买?在家里还要受这种窝囊气。
方氏将旧衣服摊开放在桌上,露出一大包铜钱,姚氏看到钱,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上了嘴。她就算看罗白宿再不顺眼,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倒是罗老头顿时涨红了脸,瞪了罗白宿一眼,道:“这是干什么?眼瞅着快过年了,你这是故意让我心里不舒坦么?”说完把衣服照旧包好,递给罗白宿。
和姚氏不同,罗老头向来极少喝斥身为儿媳妇的方氏,就是方氏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当,那也是骂自家儿子,给媳妇留两分脸面。就像这回,罗白翰巴巴地带了个颖儿回家,他实在看不惯,也只找自家儿子出气,很少去寻颖儿的麻烦。
罗白宿却不肯接,按着罗老头的手,道:“爹,你就收下吧,也让咱家过上一个安稳的新年。”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罗老头就是有再多的话也全都咽了回去。他扫了一眼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姚氏,重重地“唉”了一声,也不知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方氏只拿了六百文钱,也不肯多要,罗老头有心帮衬他们一家,特意挑的最肥的那块,砍了六斤,又将厨房里已经凝成块的猪血,捡了一盆让方氏端了回去。
下午的时候,罗白秋和罗白翰一起进的门,同来的还有几个和罗白翰相熟的书生,都是听说罗家杀了年猪,跟着过来混一顿吃的。
罗老头因为颖儿的事,这些天对着罗白翰都没有好脸色,这会儿看到罗白翰的同窗,到底是外人,要给罗白翰留几分脸面,便没有再骂他,极为客气地打了招呼。只是那几个同来的书生,虽然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过,却开口闭口地“子曰”圣贤书,罗老头种了一辈子的庄稼,连大字都不认得几个,听着他们说话,觉得酸溜溜的,一句也听不懂,便只略坐了一会,就叫罗白宿出来陪客,自己去屋里歇着。
罗白宿自打太爷过世就没有进过学堂,闲时就是自己读书连文章都很少写,跟罗白翰的这几个同窗实在不熟,委实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陪衬一般坐在边上,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吹捧,牙都要酸倒了。
反倒是姚氏,听到那些酸书生奉承着罗白翰,心里十分得意,真恨不得日子“倏”地一下子就过去,好让罗白翰去参加秋闱,考个举人回来光耀门楣。又兼罗白秋回家,她自是要拉着罗白秋好生说几回话,便摆起了老太太的谱,不肯亲自下厨房,只指使着颖儿去厨下做饭。
东屋这边,方氏老早就把饭烧熟了,煮了一锅酸菜猪血汤,又炒了两个菜,打发罗天都去喊罗白宿过来吃饭。
罗天都跑到正屋,姚氏和罗白秋罗白宁窝在房里说悄悄话,厨房里只有颖儿一个人在忙活。堂屋里烧了一根老树桩,罗白翰带着几个同窗坐在堂屋烤火,她冷眼瞧过去,发现都是罗白翰平日走得近的几个书生,那个韩子承赫然也在,大冬天的也不嫌冷,还穿着件青衫,外面连件袄子都没有。奇怪的是看罗白翰和他熟稔的样子,似乎关系还很亲密。
她不由纳闷了。上次在“聚福楼”吃了酒,没钱会钞,那几个书生十分没义气地溜了独留下罗白翰一个人,分明就是拿罗白翰当成冤大头了,如果是常人,只怕早就翻脸不再往来了,怎么罗白翰照样跟他们谈天说地,那交情丝毫也没受影响。
她只在边上站了一小会,就听到那几个书生变着法子来夸罗白翰,一个夸他是少年英才,他日必然高中,一个赞他才高八斗,来年一定金榜题名。几人你唤我一声世兄,我回你一句贤弟,相互吹捧,那神态语气活似明年秋闱中举十拿九稳。她老爹罗白宿坐在角落里,像根木头似的一边烤火一边打呵欠。
罗天都翻了个白眼,冲着罗白宿喊了一声:“爹,娘叫你过去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