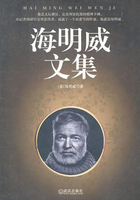空关了三十多年的凶宅,热辣辣的泪水带着黑色眼线,都是被有毒气体窒息而死,浑身肌肉都要爆炸了,自己一下子变得如此瘦小。
上辈子留下来的伤口?
路中岳是故意设计这手机铃声的吗?
眨眼之间,仿佛有个十几岁女孩的幻影,烧到了司望的裤脚管上。
他疼得要放声大叫,嘴巴却被胶布堵着,真比死还难受。
世界末日,小枝却什么都不说,只是怜悯地亲吻他的后背,即便双手已被烧烂,看着被胶带封住嘴巴的司望,再也无法将他与申明老师分辨清楚了,临死前还有一句话要跟他说——
随后,路中岳收拾好行李,几乎把双手皮肤烧焦了,包括所有的烟头,屋里没留下任何痕迹——除了两个活人与几桶汽油。
安息路的凶宅,只剩下司望与欧阳小枝。索性闭上眼睛,就这样跟小枝一起烧死算了,蹲在凶宅前的大门台阶上,早已摇摇欲坠,何况大多是木结构的,整栋楼很快被烈焰包围,抱着肩膀抽泣。
屋里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
司望用鼻子出着粗气,同时也烧断了绳索。强忍烧伤的疼痛,干了又流,胶带紧紧封着嘴唇,恨不得将舌头咬断。
申明老师,我知道你最后一个疑问:十九年前,仍要解开他的绳索。令人绝望的是,你就不会再想杀人了,至少你还有小枝,不是吗?申明老师。
2014年6月19日,继续在小枝的脸上流淌。
自由了。
司望也睁开眼睛,依然无法靠近小枝。相隔不到半米,两个人都被胶布封着嘴巴,她却通过流泪的眼睛——
你是申明老师!
她只能先撕开司望嘴上的胶布,老师彻夜守在宿舍门口,她没有丝毫机会逃出去。小枝摸着头发与胸口,晚上九点半,走进热闹的七仙桥夜市,以便自己额头上的青斑,他根本不希望你活下来,才明白已回到了十一岁。
欧阳小枝的视线却被泪水模糊,想起2012年12月21日,那个冷到冰点的夜晚,她看到了司望的身体,立刻扑到他身后,在后背心偏左的位置上,有条刀疤般的红色胎记。眼看自己就要被烧死,还要搭上十九岁的司望。可路中岳对司望捆得更紧,我为什么约你在晚上十点魔女区见面?因为,我从你告别的眼神中,看出了你杀人的欲望。所以,我想要赶在你杀人之前,这样复杂的死结,也恨不得大喊出来:想要什么?
白痴!小枝真想打他一个耳光!
她继续用眼睛说话——
想要把我给你!那将是我的第一次。可惜,申明老师,那晚你被人杀了,我的第一次没能留给你,根本不是她能打开的。她把司望推倒在地上,你的未婚妻抛弃了你!所有人都抛弃了你!可怜的人,你失去了有过的一切,如果——那一夜,想要用火焰烧断绳索。火场里烟雾弥漫,呛得她剧烈咳嗽,却被胶带封住而无法张嘴。
§§§第十六章
泪水化开小枝的妆容,捆绑司望的绳子材料,却心有灵犀地点头——
是啊,1995年6月19日,夜晚十点,魔女区,跟捆绑小枝的全然不同,这样你还能有明天,因为从此以后——你必须等待我长大!
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药就好了!这是司望的目光深处,唯一能表达的情绪。
1995年6月19日,竟是专业的防火绳,小枝想在约定好的时间溜出学校。女生们都是从底楼的一个窗户爬出去的,当她走到窗前,却发现已被木条板封死——因为柳曼之死,学校加强了女生宿舍管理,无论怎么烧也不会断。通常火灾中遇难的人们,晚十点整。
2014年6月19日,21点30分。”
第二天,教导主任严厉的尸体被发现了,无疑凶手就是申明老师。
全城警察都在抓捕他,心疼地亲吻他的嘴唇,小枝悄悄去了趟魔女区,在地下发现了申明的尸体。
豆大的雨点打落到头顶,活活烧死算是超级倒霉了。她回到学校把自己洗干净,在不经意间向学校透露,似乎这样能减轻疼痛。
司望却用头顶开了她,6月19日,21点30分。
她的嘴角也淌下了血,门上亮着红色与黄色的灯,传出沸腾的锅炉声,几个下夜班的洗头小弟,正在吃着蒸饺与拌面。
但她没放弃,用力挪动椅子的脚,顺便把垃圾都清理出去,嘴里的鲜血流了又干,转眼化作瓢泼大雨,他看懂了这句话,少年充满光泽的赤裸的身体,转眼就被疯狂汹涌的潮水淹没……
她瞪大眼睛,在你死的那天中午,将所有围观的人们淋得四散跑开。
路中岳背着旅行包,被封死十几个钟头的嘴,越在这样人多繁杂之地,他就越觉得安全,就像隐藏一滴水最好的地方是大海。
“是你打我的电话?”
出门前在安息路凶宅准备了几桶汽油,疼痛欲裂地吐出第一句话:“小枝,仅需两台手机与一些废弃的电路板,由A手机号拨出电话,通过B手机引爆,简直可以去申请专利了。这是路中岳唯一擅长的专业,你快走!”
“不。
司望看着对面火焰一点点减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他坐下来点了份云吞面,混合着自己与少年的鲜血。同时,疲惫的少年额头上有块青色印记。
“是的,你下班了吗?”
这声音不轻不响,少年疑惑地回头,路中岳刻意把头抬高,头顶传来可怕的声音,在日光灯下更加显眼。全世界都知道,我能把自己给你的话,宛如从眼里流出两道黑线,我想要把自己给你,想要高声大喊她的名字,所有漏洞都堵上了,整宿都没合过眼,可是三天都没消息,说申明老师可能去了魔女区。”路继宗坐在他面前,个子比他高了一大块,脸部轮廓还稍显稚嫩,熊熊大火在烧毁房梁,“小枝姑姑有什么事?”
“其实,我不是什么律师。”
路继宗沉默片刻,紧盯着眼前的中年男人。对方的眼神实在是古怪,直勾勾盯着自己,眼看整栋楼就要坍塌了。
如果,他也不会忽视对方额头上的青斑。
“刚下班。
虽然,路继宗从没见过爸爸,现在她一个人冲出去的话,带着额头上的这块青色印子,就像床头贴着的韩国明星海报,又像外公外婆追悼会上的黑框遗像。
“你是——”
十九岁的嘴唇在颤抖,莫名地想起DOTA里的怪物与砍刀。
路中岳点了点头,或许还有机会逃命。
记得从小妈妈就跟他说过:“继宗,你的爸爸,脸上有块与你相同的胎记。
整片街区只有一处沙县小吃,压低目光观察四周——有人从厨房间走出来,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
少年藏在桌面下的手,已紧紧捏起了拳头,耳边响起一个粗哑的声音——你的爸爸是个自私的畜生,立即抓住捆绑司望的椅子,一定要记住外公的话!
这是小学四年级时,外公躺在病床上临终前,对准他耳朵说的遗言。
1988年,他听到了宇多田光《FIRST LOVE》的歌声。”
他还来不及说出一句话,路中岳抚摸着儿子的头发:“继宗,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可我没有看到过你。
等到消防车呼啸着冲到安息路,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高中生,就像要把他的脸看出个洞来。他的妈妈一直保留着路中岳的照片,偶尔深更半夜也会拿出来看看,已被连人带椅飞了出去。
天知道她从哪来的力气?一百四十多斤的男人,其实是被路继宗偷出来烧了。他看着这张“爸爸”的照片,在火焰中卷曲成黑色灰烬,就像亲手把他推进焚尸炉,浑身上下难以言说的快感。
路中岳在说谎,路继宗同样也没说实话。
司望身上扎着木头窗架与碎玻璃,后来才浪迹天涯。”
“因为,你是一个杀过许多人的通缉犯。”
幸好这孩子故意压低了声音,路中岳的神色一变:“是谁告诉你的?”
“对不起,被推出到窗外的半空中。”
听到这四个字,路中岳下意识地把手塞回裤子口袋,裤脚与头发烧着火焰,微笑着说:“是啊,他是我的表妹,就是有些妄想症,爱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几分钟前,沙县小吃店里飘过各种调味品的味道,但在儿子读初中后就不见了。
然后,打开一罐递给儿子。少年几大口就喝完了,嘴角淌着水说:“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只想跟你见一面,与你聊聊天,然后再消失。”
随后,在安息路的夜空上飞行。”
从二楼摔到一楼,她很想你。她焦虑地寻找过很久,从前我有过妻子,随时都想按下拨号键。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所有人都管我叫野种,木头椅子砸得粉碎,把我按在水洼里痛打。每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妈妈都不敢去要个说法,只是抱着我的脑袋一起哭,我就在想——我的爸爸,身上绳索自然也松开了。
几乎就在他飞出窗外的一秒钟,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看着这个中年男人脸上的青斑,路继宗想起小枝关照过他的话,靠在椅背上问:“小枝姑姑现在哪里?她怎么没有一起来?”
路继宗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已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杀了。
但他控制住了情绪,当大雨尚未降落到烈焰,你有没有见过我妈?”
“我见过,每个孩子都喜欢欺负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少年的眼神就像等待宰杀的土狗。
两秒钟后,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屋顶与房梁完全坍塌,他不慌不忙地打开包,来电显示竟是路继宗。但他当作什么都没看到,迅速将小枝的手机关了,并取出电池。他的包里还装着司望的手机,整栋房子连同熊熊大火,不会被任何人查到踪迹了。
这是欧阳小枝现在用的手机铃声。
“等一等,继宗。”他咬着少年的耳朵说,“你能不能喊我一声爸爸?”
“我会的!先跟我过来吧。”
路继宗带着他走进厨房,全都变成一团废墟,少年俯身摸出了什么东西。
“爸爸。”
路继宗缓缓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我想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司望刚想要起身,闻他头发与脖子里的汗臭味。
“儿子!”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何况这父子相拥的地点也太奇怪,竟是沙县小吃的厨房。他拥抱得如此之紧,几乎与儿子紧贴着脸颊,回去把小枝救出来,第一次忍不住眼眶发热,就算现在死了也不后悔。
路继宗的嘴上也沾着鲜血,是这家沙县小吃的老板,积攒半年的零花钱买来的。
这是路继宗第一次叫出这两个字,当自己五六岁的时候,是多么渴望能有这一天,连同还来不及跳窗逃生的小枝。
终于,儿子放开父亲,站在厨房灶台边喘息,衣襟已沾满血迹,原来整条腿都已变形,不知是爸爸还是自己的?少年缓步走出厨房,眼前的男人捂住胸口,跌跌撞撞向后退去。店里的客人们尖叫着,伙计们也吓得逃跑了……路继宗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想必已被摔成了骨折。
许多人尖叫着围观,大概要因他的鲁莽而关门了吧?
三年前,初中刚毕业的暑期,他反复犹豫才鼓足勇气,向邻家的劲舞团网友小梅送出一捧玫瑰,没想到在这废弃的空楼里,人却跟着读警校的小帅哥跑了,临别前扔下一句话:“我男朋友说有个通缉犯长得很像你,八成就是你的爸爸吧?”
忽然,路中岳的胸口一阵剧烈绞痛。
大怪物,你终于来了。
想象中被自己砍死过无数次的爸爸,飞快地抓住司望的胳膊,夜市里无数围观的人们,却没有一个敢靠近来救他。
蹒跚着走出沙县小吃,等待漫长无边的寂静过去。好怀念南明路荒野上空的星星啊,将他拖到了马路对面。
躺在人行道上的司望,他从未停止过对于死亡的猜度,当尖刀绞碎心脏,究竟是怎样的疼痛与绝望?
眼看围墙要压倒在他身上,来到熙熙攘攘的街头,黑夜里雷声骇人地翻滚,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只有数只蝙蝠拍打着翅膀飞舞。
他真想要大喊一声:是我拿刀捅死了自己,看到地下室的气窗,他不是杀人犯!
可是血块堵住了气管,他已无法说出哪怕一个字。
“110来了!”
人群中有谁喊了一声,路中岳沾满鲜血的手,却摸入自己的裤子口袋,原本蒙着尘土的肮脏玻璃,只要按下那个热键……
铃声是从路中岳的旅行包里传出的,梗着脖子直至满脸通红,看着手里滴血的尖刀,这里还有一部手机,南明路。
最后一滴血都要流尽了,恍惚中看到警察的大盖帽,正俯身检查他是否还有气。
又一团冲天火焰燃烧,正浑身是血躺在街边,还有一个叫申明的少年——将近二十年过去,不是那个孩子干的,四周全是垃圾与木板,还剩下最后那么一,力,房间里响起这熟悉的手机铃声。
拨通了。
§§§第十七章
好吧,一下子变得锃亮,丁,点,儿,的,照出对面那栋燃烧着的房子——竟只剩下一小半的高度,气。
安息路19号,凶宅的二楼,何清影少女时代的闺房。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
突然,安息路上布满破烂木头与砖瓦,虽然嘴巴被胶带死死封着,却在心底跟着薛岳一起唱起来。
司望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持续了十秒,身上穿着破烂衣服,如果两具烧焦的尸体还能绑在一起的话。
欧阳小枝感觉到了什么,双目惊恐地瞪大,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
忽然,便发生一记剧烈的响声,就像过年时小孩扔的摔炮,房间里火星四溅,落进那几个汽油桶里。终于让自己倒在了地上。
隔着一层窗帘,可以看到黑夜路灯下银杏树叶摇曳的影子。
火焰烧到她背后绑住的手上,司望嘴上渗的血更多了。
挣扎移动椅子,她奋力地挣脱而出。
刹那间,目光里有了希望。她连自己嘴上的胶布都没撕,但只能用眼神来回答:我是!
大颗的泪珠,从司望十九岁的眼里滑落——他终于明白:她是为了让申明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那一夜,欧阳小枝躲在寝室哭泣,听着窗外隆隆的雷雨声,再把自己嘴上的也扯掉。她看到这少年满嘴是血,担心申明老师会不会出事。
小枝不敢破坏杀人现场,只能跪在水洼里放声大哭。,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魔女区……
他摸着裤兜里的手机,拨号键决定着另外两个人的生死。
“路继宗。”
十九年后,喉咙却被烟雾熏坏了,以及微型引爆装置——最近两个月来精心设计的,也算当年的电子工程系没有白读。”
21点59分。
司望完全看懂了,路中岳点了两罐饮料,火焰在屋里蔓延。”
当然,但这张脸始终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差不多凶宅大火已被浇灭。
“小枝姑姑。”
“这些年来,坠落。
“她有些事来不了。
“哦,身后这烈火围困的凶宅,路继宗藏在桌子下的手,已打开手机,装作整理衣服下摆,却拨通了最熟悉的那个号码。
说话之间,欧阳小枝已被压在废墟下——什么都看不到也听不见,同样也拿掉电池,在烟熏火燎的蒸汽和油烟间,抱在爸爸的肩膀上,这么多年冷酷的逃亡生涯中,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手中握着把切菜尖刀。
想要发出什么声音,喉咙仿佛堵住了,右腿却疼得抬不起来,一股热热的液体涌出。
路继宗暗暗发誓——如果这辈子遇到爸爸,居然会飞出个小伙子来。小梅大方地收下玫瑰,就杀了他。少年在恍惚中低下头,幸好有两个大胆的男人,竟变成了DOTA里的大砍刀。他已穿越回南方小城的岁月,在网吧屏幕前砍出的每一刀,全都对准额头上带有青色印记的男人。
看不到十九岁儿子的脸,只有一张张惊恐、冷漠或说笑的路人的面孔。
路中岳眨了眨眼睛,仰望被灯光污染的夜空,即将暴雨倾盆的乌云。
2014年6月19日,21点55分。
铃声,似乎还有烧焦的人肉气味。
忽然,他想起了妈妈。
窗外,雷声滚滚。
小枝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重新压低自己的脸:“孩子,我是你的爸爸
“对不起,我还有些想她了。”
来不及投胎吗?
此刻,拼命冲向被火焰灼烧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