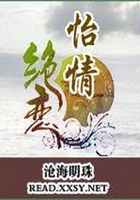!#
许久他才回神,举手点了聂云铮穴位,将他抗在肩头。
聂云铮也不挣扎,只在他肩头来回重复:“出得这门,我还是死,撇下众兄弟一人独活,那还不如死。”
他生性狷傲,这话说的出口,也必定做的出。
慕容缺无法了,只得就地将他放下:“你要怎样,要怎样才能不这么死心眼?”
聂云铮沉默不语,外面脚步声远远踏来。
慕容缺在原地发楞,短短片刻,心中那个念头却好似让他经历了亘古洪荒。
他握了聂云铮手,解开他穴,一字一句道:“我也许有法子叫他们免于一死,你听我的,跟我走。”
聂云铮往后瑟缩,干脆伸手将牢门紧紧关住:“你莫要哄我,我是一定要和他们同生共死的。”
脚步声越来越近,再没有时间将一切道尽。
慕容缺回了身,瞧着聂云铮,忽然深深叹了口气:“苏蔓……到如今你还爱她吗?”
聂云铮瞠目结舌:“将军,我是爱过她,当日在丽宛城对她一见倾心,可是……”
“不用可是。”慕容缺摇头:“我没旁的意思,只是问你,你只需依着你心回答。”
脚步声更近了,慕容缺拔出了剑,看着聂云铮,目光那样热切。
不知道为什么,聂云铮有种感觉,感觉这个答案对慕容缺而言是如此重要。
那答案在他心间滚动,最终出了口,斩钉截铁的一个字:“是。”
慕容缺闻言持起了剑,高高扬起,准备迎对他的宿命。
“答应我。”他对聂云铮道:“不到最后一刻,永别放弃生命,也别放弃感情。”
是夜,皇宫议事殿,拓拔烈正挑了灯听堂下人奏禀,殿外突然有了声响。
侍卫们直呼拿刺客,纷纷嚷嚷,但有个声音分外清晰。
“慕容缺求见。”
拓拔烈此刻本昏昏欲睡,听得这声响,只觉是在做梦,忙急步出了大殿。
殿外慕容缺长身玉立,被无数兵刃指着,正负手与他四目对望。
拓拔烈急急转身,怕被那眼波灼化了,勉强维持着平素的冷厉:“退后,容他进殿吧。”
进了殿,先是搜身,慕容缺也不反抗,由人将承影剑搜了去。
他想近前一步,靠近拓拔烈,已然有两枚长剑指住了他胸膛,持剑的是上次他来皇宫时得遇的两位高手,正冷冷喝着:“靠后!”
“无妨的。”拓拔烈摇头:“让他上前吧,我想听听,他深夜来访,到底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说。”
慕容缺上了前,那两枚剑仍指着他胸膛,但他眼里眸色比刃光更寒。
“皇上。”他问:“如果没有聂云铮几万人出击,你能否击退柔然人大军?”
拓拔烈摇了摇头,斩钉截铁:“不能。”
片刻后他又抬头,神色也不知是悲是喜:“此事你居功至伟,先是瓦解陈朵阴谋,接着又以你血解了他们众将剧毒,最后是沙场杀敌,血染战袍。我,的确是欠你良多。”
慕容缺此刻正环顾四周,望着头顶那盏宫灯出神,想起了些不堪想的过往。
正是这里,那日宫灯彻夜燃照,多少人围观,围观他如何尊严沦丧,赤条条被人轮番**。
这回忆叫他血气上涌,眼前一阵模糊。
他怕自己忍不住去扼住拓拔烈咽喉,拳紧紧握着,指甲深嵌入掌,一字字道:“若皇上想还我这情,慕容缺只有一个请求。”
“放过聂云铮一行是吗?”拓拔烈问。
“是。”堂下慕容缺答。
两人四目触碰,前尘旧恨交杂,但到底,拓拔烈还是摇了摇头:“不能,他们有逆反之心,我不能姑息他们,等着他们来亡我江山。”
这答案出口时,拓拔烈捕捉到了对面慕容缺眼内的恨意,可以将天地焚尽的恨意。
果然,他足尖点地,斜里迎着两枚长剑而去,那两人不及收势,只得眼见着一枚长剑刺入他肩头,而另一枚被他握住刃口,劈手夺过,架上了拓拔烈咽喉。
“退后。”他厉喝:“去,拿玉玺皇绫来。”
殿下呼啦涌来一群侍卫,闻言全都盯着拓拔烈,等他吩咐。
拓拔烈痴痴站着,感觉到慕容缺掌心被长剑刃口刺破,滚热的鲜血一滴滴流入他领口。
“原来。”他叹:“原来是我想错了,自始至终,你从来都不曾原谅我。”
慕容缺闻言长笑:“原谅你,我为什么原谅你,又凭什么原谅你。原谅你叫我家破人亡?原谅你十二年凌辱折磨,将我的尊严一脚脚碾碎,和着血,叫我这场噩梦永不能醒?”
“拓拔烈。”他唤,咬着牙,想把这名字咬碎了生吞:“我永不会原谅你,我日夜盼望着与你同归于尽,所以,你要老实点,听我的,写下圣旨,放聂云铮他们一条生路。”
拓拔烈在他剑下摇头,脖颈被刺下狭长伤口,滴着血,和慕容缺的血流往一处。
那一刻,他竟觉得微微欢喜,竟能坦然面对生死。
“你杀了我吧。”他道:“我宁可死,也不会眼看着祖宗基业葬送。”
慕容缺闻言将长剑又递进半分:“放心,我不是要你就放任他们离去,不过要你给他们一条生路。充军,流放,还是集体为奴,都由你,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这么低微的请求,换你九五之尊一条性命,你自己衡量,到底值不值得。”
拓拔烈沉默了,沉默良久。
“我若允了你,你就会放了我,束手就擒?”他问。
慕容缺答:“是,我一诺千金。”
“那好。”拓拔烈拔高声线,朗声吩咐下人:“就依慕容将军所言,拿玉玺来。”
“拟圣旨,叛军免于一死,流放荆州为奴,我一朝在位不死,就保他们一朝性命。”
堂下人依言拟好了,将黄绫呈上,拓拔烈持起玉玺,在上面盖上了端正皇印。
“去。”他道:“八百里加急,务必在腰斩令执行前将朕旨意送达。”
所谋得成,慕容缺只觉腕间酸软,再握不住那沉沉铁剑。
铁剑坠地,侍卫们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
而拓拔烈回身,死死盯住眼,道:“你就这样天真,以为真的君无戏言?以为我方才说过的话就真的不能收回?”
慕容缺痴立当下,有种痛,像惊雷奔入身体,刺穿了他魂灵。
不过一瞬,却长过漫漫一生。
他望着拓拔烈,那眸里是片混沌绝望的灰色。
他问:“要怎样,要怎样你才肯履行诺言?”
拓拔烈不语。
慕容缺垂首,一掠衣衫,左膝缓缓着了地:“可是要我求你?”
拓拔烈摇了摇头,上前扶住他双肩,将他扶起:“不,全天下人叩拜我,我安之如怡。可偏偏是你这一跪,我承受不起。”
人扶起了,那双手却仍握着慕容缺双肩,紧紧握着,想握到地老天荒去。
慕容缺也由他握着,喃喃自语:“早在来时,踏进这皇宫第一步时。”
“我就已料想过所有结局,所有,包括这一种。”
语气波澜不惊,但心不受控制。
他张口,血如离弦之箭往拓拔烈射去,劈头盖脸的,淋了他一身。
拓拔烈收回双手,将那血抹尽了,拿纯白色的丝帕
再展开时细瞧,帕上殷血斑斑,是那些永愈合不了的伤,永挽回不了的错。
将这方帕子纳入怀里,拓拔烈走近慕容缺,如此之近,可以清楚听闻彼此呼吸。
“我老了。”他道:“人老了,总会明白一些事理。”
“明白到爱是不能勉强的。”
“如今我要的,再不是你,只不过是你仔细的,耐心的听我将这番话说完。”
慕容缺抬头,眼前一片迷蒙,看不见拓拔烈神色,所以也不能确定他这话里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