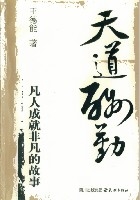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
当身旁最后一名士卒倒下,十数把寒气森森的兵刃指向他胸膛时,慕容缺并没有觉得害怕。
帝都君王下旨,要削除他慕容家一切藩位,赴京侯旨时,他就知道,这一世荣华与性命,都去到了尽头。
起兵抗旨,只不过是心有不甘后徒劳的挣扎。
半生戎马,叱咤风云,他性子刚烈的父亲本无异心,但也不会就这般伏低了身子屈辱着死去。
沙场上拚尽最后一兵一卒,战袍上血迹层染,仰天长啸着赴往不归路,才是唯一衬得上他慕容家世的死法。
“来吧。”沙场上慕容缺再无余力持起长剑,对那三月前就已注定了的命运抱起了一个笑,三个月心力交瘁的苦苦挣扎,尘埃落定后一切释然的轻松,谁说不是呢。
“父王,柳云,淳儿。”他回了头,身后是如血一般的落阳,此番兵败,阖家怕只能在碧落黄泉相见了吧。
“圣上有令,留慕容缺活口。”一骑轻骑踏沙而来,马上人朗声发话,这样决定了他生死。
“慕容缺。”待得他被反缚了双手,马上人近得前来,是一张清秀的男子脸颊,用一派冷冽眼光扫过他全身后,幽幽的叹了口气。
“持剑纵横沙场,却生得这样英挺俊朗。”
“难怪。”他沉吟着,像是有些心伤。
“他肯出倾城之力,来换你臣服。”
“走吧。”将披风裹紧,他重新上了马,却又故意拉紧缰绳,放缓步调,跟随在大队人马之后。
“慕容缺。”见人马中囚犯不肯屈从,他又缓缓沉吟着这个名字。
“你的地狱之门打开了。”
身后斜阳没入了天的尽头,最后一丝光亮隐去,黑暗开始弥漫。
夜来了。
“慕容缺。”诺大的宫坻里,烛火通明,只有一张座椅例外,掩在黑暗里,散发着任是什么也不能照透的阴郁之气。
“我等了你这么久。”座上人披着一件重裘,身子隐没其间,只露了一双苍白得几近透明的手:“等得心都凉了呢。”
见阶下之囚不肯言语,他又凌空比了一个手势,淡淡一挥,却饱含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朕喜欢讲话时对着面前人双眼。”
立刻有人将阶下慕容缺发顶提起,对着阶前高座。
一缕鬓发垂到了眼角,月光适时透过窗格映入,他眼波流转处,隐隐透出了银色光华,平静清澈,照得月华也黯然失色。
“听说你象你母亲。”座上人缓步下了高阶,用力捏住他下颚,目光却坠入了他双目星光,无法自拔。
“难怪。”许久许久,才有一声叹息荡漾:“慕容云天盖世英雄,断弦后却无意再续。”
“这样的美色,该是人间有的吗?”
慕容缺不语,目中也是一片沉寂,没有欢喜哀愁。
“哟。”颚下冰凉的手突然抽离,他脸颊重重触到青石地面,背脊却一阵锐痛,那手又抚上他后肩伤口,在血泊中游走:“你受伤了。”
“圣上。”反剪着双手的人终于开了口,却没有痛楚,只有淡淡不甘:“先帝开朝创业,慕容家居功至伟,边陲异族入侵,慕容家世代镇守。”
“世代忠良,却换来这般下场,圣上不怕天下人寒心吗?”
“忠良?”披着重裘的君王轻轻笑着,声音也是如人一般的尖削单薄:“我连下十道圣旨,宣你进京,你却执意不从。”
“这等忤逆,也配称忠良吗?”
一语击中要害,慕容缺将头别过,心中那点已接近麻木的钝痛又袭上身来。扼住了他咽喉。
三年前随父进京面圣,是一切苦难的开始。
迈进这深宫禁院前,他是长身玉立,傲骨铮铮,久经沙场历练的世袭藩王之子。
作别这无涯红墙时,他的心连带自尊,都被捻成了齑粉,四处飘零。
无法言说的苦痛啊,在他心滋长成了一颗毒瘤,日日吞噬着天地的每一寸光明。
承袭了母亲容颜,却也遗留了父亲筋骨。
这样的苦痛,叫这样的他于谁人诉说。
告诉他人在这红墙金瓦之内,三千粉黛无颜色,君王只爱后庭花?
告诉他人这样血染长袍,也从不蹙眉的自己,骄傲就这样被撕裂,鲜血淋漓?
不能说,沉默的钝痛,在他心一下下敲打,血涌上了心尖,却又只能暗自吞下。
时日久了,父亲也似有所顿悟。君王下旨邀他赴京时,父亲从他决绝目光中读懂了那抹痛色,再没有追问,平生第一次违抗了圣旨。
不是不愿意为家人付出,只是那样的屈辱,冰不能形容其寒,火不能比拟其烈,重得远超出了他心弦能够承载的极限。
“结束了。”往事飘落,慕容缺眉心终于舒展,目中荡起了讥诮:“我来这里,只为告诉你。”
“天下之大,不是你所要的,都能如愿。”
“拓拔烈。”
被人直呼名号,殿下君王却并不气恼,只将一方绢帕塞入了对方口中。
“咬舌自尽。”他摇着头,将长裘风帽摘下,露出一张清秀却透着妖异的脸。
“这样老套的法子,也能谋得一死吗?”
“朵儿。”他唤着,立刻有身形闪近,步伐轻飘,不带一点声响。
正是那日沙场上授意他免他不死的清瘦男子,生得一双丹凤眼,眉青目黛,两颊泛着一点病态的嫣红。
“将慕容公子武功废了,省得他持武自傲。”
“是。”那端人应着,波澜不惊的语气,仿佛他心是深湖,风吹不皱,雨淋不乱。
那苍白无力的手指按上慕容缺后背,却汹涌出一股无尽力量,在慕容缺四肢游走,最后破穴而出,连带激起一阵血雾。
二十余年辛苦修炼,沙场对敌,才换得的这一身武艺,顷刻间化为乌有。慕容缺却似觉得并不可惜,目光仍是一片空明,定定望着前方,仿佛那口中罗帕上沾的,不是他的血,那随掌力散去的,不是他的武功。
绝地求生难,慷慨赴死易。
一个决意求死的人,还有什么值得记挂惋惜。
“慕容淳。”着重裘的人又返身坐上高座,用绢帕反复擦拭着双手,目中光华闪烁,阴晴不定:“年方六岁,虽不及其父俊朗,倒也生得端正,骨骼奇清。”
“这个人若被带入宫中,自小做了檀奴,慕容公子,你看,会不会有前途啊?”
提及爱子,堂下本了无生趣的人突然昂起了头,目中陡然燃起了杀机,渐渐渗出血色。
“十八岁得子,宠爱有加,慕容缺,你父岁战死沙场,但你娇妻爱儿还在。”
“你那懵懂不知世事的娇儿,正等着你来拯救他的命运。”
“一日你死了,来这宫中接替你位子,便是你膝下娇儿。”
“慕容公子。”高座下的人俯下身来,唇边漾起一抹邪恶的笑:“薄唇最是无情,你唇生得这样薄,是你先无情,我才无义。”
床围外轻纱摇摆,拓拔烈将一个葡萄纳入口中,单薄的双肩微微颤抖,似是余波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