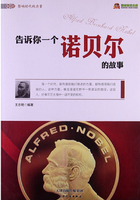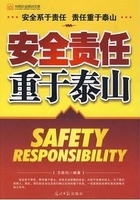摆在明代史研究者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尤其通过现代性的合法逻辑,我们必然要与传统政治的视野分离,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之后,兴起了两个主要的研究趋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经济社会进步论证,为史学研究寻求新的视野;抑或从现代政治的视角,通过与传统政治割裂,从而找到另一条史学写作的合法途径。当这两种现代性的观念成为了史学工作者的潜意识的时候,他们会自觉将自己的视线调整与此两种观念同步,以期史学研究能够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
处身现代史学中的明史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无论是民国时期老一辈的明史研究者,还是21世纪涌现出的新一代明史青年学者,也都依从现代史学的步伐,将现代性的视野融入到明史研究之中。前者如从日本政法大学归来的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虽形式还是传统的,但治史的视野却是现代的,通过对于明代皇权政治的批评,孟先生为之后的明代政治史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即通过现代政治的视野对明代政治进行研究。而后者如胡吉勋博士对“大礼议”的研究,通过对时局人事变动的探讨,认为明世宗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所施展的一系列举措,加深了帝制时期皇权不可挑战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在朝廷中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孟森先生对明代政治史的评价基本一致,也证明在政治史研究中,通过现代政治视野对明代政治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了不言自明的传统。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辩后,对于中国历史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就逐渐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而作为晚期封建社会的明代,其的重点还不仅仅限于对封建社会经济的研究,而且在资本主义萌芽、日本前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对商品经济社会的研究也不断成为明代史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背景下,将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衡量明代社会的标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通过这一标准,田澍先生将“大礼议”中张璁、桂萼等人判定为社会革新力量,通过这一角度对“大礼议”进行讨论。
这两种正统的现代性历史观,对明代史学研究而言几乎是交叉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于明代政治史研究一般会采取现代政治的角度,而对社会史则会采取经济发展的视野。因为现代研究的专门化,这两种导致不同结论的做法也不会产生实际上的冲突。然而,分科并不意味着明代史学研究的这两种视野不会产生碰撞。在“大礼议”这一问题上,它们便产生了具体的碰撞。政治史研究者往往认为杨廷和为首的朝臣,通过“大礼议”事件,限制了皇权专制的蔓延,从而表现出现代政治的品质。而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则认为张璁、桂萼等人,通过“大礼议”事件,打击了封建保守的政治势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中的进步势力。现代性的研究视野在“大礼议”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对立,在这种研究思路对立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们。
现代性史学所拥有的这两种视野,都来源于现代的启蒙哲学运动。这场现代性的反叛运动,最终导致了现代视野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恰恰是我们对传统社会心存疑虑的重要原因。因而反思现代史学研究的视野,必须从反思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这一概念源自于柏拉图的《王制》第七卷的洞喻,启蒙哲人借用了这一形象,从而开启了现代性社会这一巨大图景。
在柏拉图的洞穴中,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远远燃烧着一个火堆。在火堆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
此时,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从洞穴中走出来,因为日光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蹦,以至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只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他的视力就可以恢复,首先大概看阴影最容易,其次是看人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是看事物本身,在夜间观察天象,之后就可以在白天看太阳本身了。此时他便明白:“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的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于是他回想当初穴居的情形,就会庆幸自己在认识上的变化而对同伴表示遗憾。他既已见到了事物之本身,便宁愿忍受任何痛苦也不愿意再过囚徒生活。然而,当他复回洞中,那些同伴不仅不信其言,还会觉得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对“影像”竟不能如从前那样辨别。他的同伴们不仅不想出去,甚至想把那位带他出洞的人逮住杀掉。
在这则寓言中,柏拉图试图通过形象的比喻将传统社会比作“洞穴”,而洞底的囚徒则象征着被欲望所束缚的大众,而在矮墙后生活的则是能够给大众带来影像(响)的君子,走出洞穴接受阳光启蒙的则是哲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生活: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正好与柏拉图洞穴中区分一致,也就是说囚徒习于享乐的生活,士人则习于政治生活,而走出洞穴的哲人则习惯于沉思的生活。通过这样的区分,奠定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也就是古典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人类心性的等差,因此洞穴成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典政治的形象表征。
而走出洞穴的哲人,如果成功地将洞底的囚徒带出地面,让他们享受到阳光的启蒙,人人皆获得理性的智慧——这恰恰就是启蒙哲学家一直坚持不懈做出的努力。为了达成这样的理想,启蒙哲人设计了两套方案来彻底颠覆洞穴的政治伦理。其一,启蒙哲人认为囚徒因为经济问题,所以无法享受哲人沉思型的生活。故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人们可以获得沉思的闲暇,就一定能够享受到哲人沉思性的生活。第二,启蒙哲人又假定当人人皆获得理性后,就能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不必再接受君子们的指导。既然走出洞穴之后,自由民主是好的,那么生活在洞穴之中,接受洞穴中阶级政治的统治就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套方案,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现代性史学研究两大视野的来源。通过现代政治与经济的角度,重新反思洞穴中的传统政治。当我们先天接受启蒙哲学家的方案,才能判定通过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一定能够获得走出洞穴的机会,或者只有打破洞穴的阶级统治才能获得走出洞穴的机会。
上述两条现代性的方案成为了现代史学研究的两条重要道路,一旦接受了启蒙哲学家的方案,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回归洞穴政治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反思的是,明代历史是否依旧属于古典政治传统,当我们采取了现代性研究路径时,是否已经遗忘了他仍然还在洞穴之中的可能性。对于历史所采取的现代性研究路径,是否会因此将破坏传统政治当成历史的合法性,而将回归古典政治传统、维护洞穴政治的稳定视为历史的反动?
当我们认识不清楚这一点时,就会将错误的判断带入到历史研究之中,正如将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带入到明代史研究之中。当我们假定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能够推导出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晚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激增,也同样产生了要求打破传统政治伦理的启蒙思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动摇了传统政治的基础,而启蒙思潮的传播也大大削弱了王朝正统的儒家伦理,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国家行政能力的萎缩,对内对外维持政治稳定能力的下降,以至于对内无法对抗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对外无法抵抗来自东北的女真族的崛起。
在现代启蒙的两大方案在明王朝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启蒙思潮对于传统政治伦理的批判,造成了古典政治哲学基础的人伦观与华夷观的崩溃,使得李自成能够将明王朝推翻,更造成了无法抵御外族的入侵。这样的教训已经非常的沉痛,但却一直缺乏对于历史教训的反思。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依然在启蒙哲学的指导下,延续着现代政治与社会经济研究的思路,努力将古典政治诠释为现代社会。
当认识到了现代性史学无法对传统政治社会进行合理的研究时,我们必须提出研究传统政治社会的思路与方法。对此,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回到洞穴之中,通过古典政治伦理的视野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在“大礼议”这一问题上,笔者发现了现代性史学的冲突,因此对现代性史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如果要超越现代性的视野,就必须超越“大礼议”双方的政治立场,在这时笔者发现了顾鼎臣。作为三朝老臣,却能摆脱当时党争的纠纷,并且有着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此,笔者非常的好奇,希望能够通过对顾鼎臣的研究,超越现代性史学研究的视野,返回古典政治研究中来。
要回到古典政治传统,我们必须知道古典政治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就是传统政治的大事!祭祀包括祭天与祭祖,这两者都是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无论祭天还是祭祖,都要通过君主展现出人伦秩序,从而体现出政治的合法性。在《尚书?洪范》中,当尧舜禹等圣王在能够稳定自然秩序和人伦秩序之后,上天才降下大法,来帮助圣王进行统治。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君主通过祭祀礼仪,彰显出其统治人伦秩序的稳固,从而祈求获得上天的认可,获得天道的合法性。而战争则是用来维护政治秩序的手段,能够维持人伦秩序和天道纲纪方为华夏之邦,反之则为夷狄之国,不与华夏同。而当华夏内部出现秩序紊乱的时候,王者必须通过战争手段来重新恢复政治秩序。而当外部有夷狄侵犯的时候,也需要王者通过武力进行驱逐。因而,古典政治虽然看起来是分为内外两部分,但究其实质仍然只是一条,即维护稳定的人伦秩序。
那人伦秩序究竟有哪些呢?通过孔子的论述,我们知道其将人伦秩序分为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总结出孝、悌、忠、信等基本的人伦道德基础。又经过儒家的深入总结,将其发展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通过古典政治的熏陶,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到儒家学术与古典政治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对于古典传统政治进行研究,就必须遵循儒家所设定的人伦秩序观念。
在顾鼎臣这样的个案研究,也可以通过古典政治的视野进行重新的反思,就会发现顾鼎臣完全符合古典君子士大夫的美德,无论是在家族中所体现出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抑或是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出的为政以德、忠于职守,甚至通过在对嘉靖帝的经筵中,劝说其致天下太平。恰恰正是由于顾鼎臣所表现出的卓越的美德,故嘉靖帝在南巡时,才将京师交给顾鼎臣进行管理。而顾鼎臣正是因为在尽职尽责对京城的管理中,身染重病,死于任上。
这样一位身俱古典士大夫美德的明代重臣,却因为不符合现代性史学的两条研究标准,被广大的明代研究者所忽略。因为忽略了古典政治传统的视野,也放弃了实践古典政治伦理的士大夫群体,这是一项多么大的损失。
从古典政治传统的视野来看王朝的政治兴衰演变,我们甚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恰是由于顾鼎臣类的士大夫群体在晚明社会的衰败,才导致了明代晚期政治伦理不断被破坏,并最终造成了明王朝灭亡的教训。也许这个说法过于专断和狂妄,但笔者相信,随着此视野的展开,将会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古典政治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属于封建残余或迂腐文化,其重要作用或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