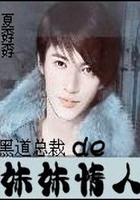[15号哨位]
躺在黑暗的地底下,让虫子一点点地龁你的皮肉和骨头,想想看,那滋味怎么样?
听连长说22号哨位弄到了一颗人头,米开广心里紧张了半天。他倒不是真想拖一具敌军的尸体--那样说无非是让连长高兴。他不会为了抢敌军的尸体而让某个战友去丧命,也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敌军的尸体。想当英雄也不能这么当。让他紧张的是,他们的山洞和敌军的山洞相通,那次夜战前在下面埋设雷障以后再没有下去过。要是敌军悄悄排除了雷障,再偷偷地摸上来,那就危险了。米开广的想法和有些兵不同。他不怕死,但他也不想轻易送命。
下午四点多钟,米开广决定下去看一看,叫顾家荣和蓝文定配合他,任宠留在洞口值岗、做饭。他们找绳子的时候,任宠把煤油炉子端到洞口--他们都这么干,这样烟子散出去比较快。
“别让我们再吃小便了。”蓝文定说。
任宠的嘴角往下耷拉。米开广眄视着蓝文定。“闭上你的臭嘴。”
“开个玩笑嘛。”蓝文定说,“你不会当真的,是吧,任小弟?”
“去去!”任宠说,“让老鼠更狠地咬你一口才好。”任宠朝蓝文定望来时也望到了米开广,这时他的嘴角动了动,似笑非笑的,好像铁皮上生出来的一层锈。
米开广没忘掉那天他用枪口对准人家的额头。他一辈子忘不掉。
这两天任宠表现不错,主动要给他们做饭。米开广深信,任宠在家里从来不做饭。昨天任宠把小便当酱油要怪米开广,是他把装了小便的罐头盒放在炉子边。虽说他们都把小便盒放在那里,但米开广忘了倒掉。近来他小便红赤,看着真的像酱油,上面又起了一层醭。吃好饭以后,说起今天的菜有股什么味,好像老鼠尿似的,才发现他们一起分吃了米开广的小便。
蓝文定一黄昏都在吐唾沫,想呕吐又吐不出来。
“不要吐了。”顾家荣挖苦道,“你不是最喜欢吃粪便吗?”
“你才是狗。”蓝文定说。
米开广到任宠身边,对他仔细说明,多少米用多少水,顾老兵切好的土豆丝和大葱怎么炒,再开一个午餐肉罐头。任宠一味点头,也不看米开广。由于不见阳光,任宠那张脸白净得有点苍灰,这时泛着忽浓忽淡的红晕。离开任宠,米开广又转身望一眼。任宠把炒菜用的压缩饼干箱搁在点燃的煤油炉子上,举起清油瓶,指甲掐在油瓶上,估量该倒多少油。也许应该叫顾老兵做饭。可是,到那个洞底通道去,凭着手电筒或蜡烛作业,那是很危险的。不管任宠对米开广的安排怎么想,首先考虑任宠的安全,这是米开广这个哨长和老兵的责任。
今生今世,米开广想,但愿我再也不会拿枪对着战友额头,格老子。
只要人没死,这个后悔没个了结。
爬上石坎,底下是一道十多米深的陡坡,望下去黑黢黢的不见底。腰里拴绳子,摸索着下去,米开广有降到地狱去的感觉。
敌军真的来过,他们把米开广设置的雷障都破坏了,这让他大吃一惊。要不是鬼使神差地让他突然想到了,今天晚上就可能遭偷袭。洞底里有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湿气流,既有从敌方那边流过来的,也有从我方这边流过去的,它对流着,分不清强弱。可能敌军经常到这里来偷听他们说话,只是他们不知道。
米开广打着手电筒,小心地往前摸。洞突然变小了。这里好像是敌我分界的一个小关卡。米开广又吃了一惊,一根细铜丝绊线碰到他的光脚背。仔细瞧,他上次朝向敌军设置的两个定向雷转过来朝着我方了。米开广把手电筒倚在石头上,使光朝上照,摘下定向雷,又转向敌方。
正琢磨着用什么方法使敌军无法排除,就听到轰的一声响。最初一刹那,米开广以为自己弄响了地雷,紧接着听到蓝文定的叫声:“不好了,哨长,快上来!”听到蓝文定和顾家荣一先一后跳下石坎的足音,他朝他们的洞口跑去。
这个洞底,简直是暗道机关,哪一块石头下都可能埋有地雷或手榴弹,石壁上也不能随便乱摸。在那正对我方的岩壁上,浅红的火光时明时暗地闪烁。那里怪石峥嵘,红光明亮时,突出的石尖石棱就像暗室里闪光的刀面,凹陷的部分更为阴黑。猜不出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敌军不可能在天黑之前发动愚蠢的袭扰。要是任宠引燃了煤油,不会有这么响的爆炸声;要是弄爆了一枚手榴弹而使煤油燃烧,也不可能有这么红亮的光折射到这个洞底的岩壁上,虽会引起洞里那些弹药的连续爆炸,但记得任宠是把煤油炉端到洞外了的……这时米开广嗅到了一股特异的气味。
在米开广摸着绳子爬上石坎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洞里已灌满了有着那怪异气味的烟和火。焱花已经在弹药箱上跳跃。洞里的温度升高了,阵阵熜气夹着烟味向他扑来,一下子催出他的一股泪水。蓝文定弯着腰,火光把他的裸臀映得很亮,手里拿着一只看上去好像魔方似的饼干箱,舀了一箱(也可能是小半箱)潴留在洞里的积水,如同跳舞一般把水往弹药箱上泼,而这只是使火焰腾地向洞顶一跳。顾家荣在外面一点,抡着一件沉甸甸的看来打湿了的军衣,拍打着弹药箱上的火焰。那衣服扫过去,似乎把火头扫灭了,但衣服刚刚离开,那木板上又跳出火花。这两个笨蛋!米开广心里想骂。
“棉被!棉被!”米开广叫着跳下石坎,向那边跑去。没有看到任宠。浓烟隔断了他的视线。洞口那儿熛焰卷动。在紧贴洞顶的上部,才能见到小片烟雾中扁扁的空隙。
米开广抓住蓝文定的胳膊。蓝文定猛力挣扎,朝米开广投来惶遽、紧张、恼怒的一瞪。“任宠呢?”米开广问,“任宠呢?”蓝文定挣脱米开广的抓握,又去舀地下的积水。米开广在眼睛的余光里瞥见,那只木箱子的一角焌穿了,露出绿油油的六〇炮炮弹的弹身。一霎间他想到这些炮弹里都装好了药包,只差没有上引信。这箱炮弹爆炸,那就会引发连锁爆炸,能把这个山洞炸塌,把他们全埋在底下。米开广抢过去,抱住箱子,正要转身时,被蓝文定没头没脑地泼了一身脏水。“别泼了!拿棉被!”米开广闭着眼睛叫唤,凭着走过无数遍的印象,抱着箱子往洞底跑。凉水有股极其难闻的气味,恶浊,腐臭,还腻人。抱在怀中的炮弹箱发热。还没完全爬上石坎,他就把炮弹箱掷了出去,立即趴倒,往石坎下面滚,与此同时,听到炮弹箱落在洞底破裂的然音响。会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他在下意识里张大嘴巴,捂住耳朵。可是没有爆炸声。他跪着,朝那里望望,惊愕莫名。真要感谢敌军,是他们破坏了雷障。也顾不上多想,爬起来就往浓烟中钻。
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没有尽头的斜坡上滑行,蓝文定还拿着那只饼干箱在积水里舀,饼干箱刨着石头的声音非常刺耳。不过他这会儿泼出去的水有点作用了,水泼在正往弹药箱上覆盖的棉被上。他的动作过于猛烈,紧张,迅速,仿佛豁出命来,用的力气太大,但泼出去的水很少,动作又滑稽又可笑。焰燏在减弱,浓烟中多了一丝棉花烧焦的气味,噎得人嗓子奇痒。这时顾家荣在一大团浓烟中咳嗽,一只手拦在眼前,另一只在扯棉被角。那棉被按下去,弹药箱上一朵活泼地跳跃着的火花须臾消失,而在他的头上,忽然升起了一小团像刚杀死的鸡血那么鲜艳的火朵。“头上!”米开广喊,“你头上!”他的头发着火了,他愣在那里,好像浓烟憋得他一口气没能喘过来。他的两手捂住嘴,伛偻着腰背,在一只垫脚的弹药箱上转圈子。一时找不到帮他扑灭头上火焰的东西,又见蓝文定的饼干箱刚好舀起一些水来,米开广夺下那箱子,对准顾家荣的头,劈头盖脸地朝顾家荣泼去。顾家荣“啊”了一声,好像溺水人被推出水面时的那一声叫。他头发上的火焰消失了。
“任宠呢?”米开广大声问,“任宠在哪里?”
“弹、弹药,”顾家荣说,“要炸了!”他指着弹药箱。箱子上浓烟弥漫,但火焰已经熸灭,不会再引起爆炸。一缕不知在脏水中泡了多久的小布条粘在他额上,像一枚抓钉或一只壁虎。
“在那儿。”蓝文定说。
一个着火的赤膊的上身从浓烟中冒出来,手上举着两枚手榴弹,手榴弹上也在着火。是他,任宠。“任宠!”米开广喊。任宠弯下身去,又在浓烟中消失。米开广记起他俩的坑铺头上放着五枚拧开铁盖的手榴弹,还有重机枪,他的冲锋枪,都在那里。米开广冲过去。地上滚动着火焰,有半尺来高,好像茅草地上的野火。石头很烫。他的赤足踏在上面,好像踏在弹簧上似的,一下子往后弹了回来。米开广的心要往前冲,可他的脚把他往后拖。米开广抬起脚,摸了摸脚底。这时候听到洞口外响起两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洞口的火焰忽地一暗,接着又红了,照出两只乱动的脚。“任宠!”米开广大叫。任宠从浓烟中冒出来,抱着那挺重机枪,枪身上和他身上都在着火,火光映亮他的脸。他低着头,似乎在找脚前的路。他的身体周围浓烟滚滚。石洞的洞顶、洞壁一时之间都隐在浓烟后面。
“任宠!”米开广连声大叫。
“哨长。”任宠说,那声音哭哀哀的。从这声音里,米开广就明白了,这场火灾不是他造成的。任宠向米开广寻望,仰起那张稚气的脸,脸前火光跳跃。他的肩上、头上、脖颈上、手上,都跳动着一朵朵一撮撮的火花,从上到下都是火,成了一个火人。那条燃烧的短裤正在破碎掉落。但他的手仍然抱着那挺重机枪。不知是看不清地面还是脚不能走了,他停在那里蹿动。那枪身一定被烧烫了,那会灼伤人的肌肉。
“把枪掷掉!”米开广说,浓烟呛得他嗓子奇痒。
“把枪掷掉!”顾家荣叫。
“快掷掉!”蓝文定叫。
“我不!”任宠说,那样子想往这边扑来。突然他跌倒了,带着机枪向后仰去,传来身体着地和枪件碰触石头的声音。
“这笨蛋。”米开广心酸,气愤,去拽那帱覆在弹药箱上的湿棉被。一只弹药箱被他带动,摇摇欲坠。顾家荣伸手把它推住。这是一晃眼中看到的。他拖着棉被,往任宠那儿跑。脚板还踩在那些烧热的石块上,可再也没感觉到灼烫。他感到蓝文定跟在他后面。浓烟底下,火光中,任宠正在爬起来,那挺重机枪压着他的双腿。米开广右手抓枪,烫得他缩回手,第二次才把枪抓住,掀到一边。在任宠刚屈起双脚准备站起来而人还在晃动的时候,米开广用棉被裹住他的身体,抱着他就往洞后面跑。洞外是不能出去的。米开广瞥见,洞外地上,火焰烧得还很旺。一枚燃烧弹极为准确地落到了他们的山洞口,米开广刹时明白。冲出洞外的火区,只会让对方的狙击步枪补一弹。既然他们的山洞和敌军的山洞相通,就不必担心洞内因缺少空气而窒息。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一瞬间完成了。任宠头上的火焰也被米开广在慌乱中用湿棉被的一角拍灭了。米开广不顾一切地抱着任宠往洞的深处跑。经过顾家荣面前,他向米开广伸出双手。“去帮蓝文定!”米开广说,同时撞着他,撞得他倒退几步靠在弹药箱上。
石坎边有一片烟雾稀淡的地方。米开广把任宠放下去时,自己也跪下了,石头尖硌得他“呵”了一声。这里是一个斜面。使他感到庆幸的是恰巧把任宠的头放在高的一边。如果要抱着任宠再转一个身,既没有转身的空间,也抱不住了。他为自己的力气感到吃惊。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这么大的劲,用湿棉被裹着一个人,还能跑得这么快。
火,一会儿后都扑灭了,只洞口外还有火焰在炀炀地燃烧。那就让它烧吧。顾家荣摸到了米开广刚才掷掉的手电筒。“蜡烛都化掉了。”他说。
“电筒还能用,很好了。”米开广说。
电筒光照到任宠脸上,他闭了闭眼睛。他的左脸颊起了一些水泡,两道眉毛只剩下一点点。鼻子成了黑的。一颗门牙碰断,嘴唇也有点碰破,血从他嘴里流出来。没有烧伤的地方都是泥灰。他昂头,想坐起来,眉心紧皱,嘴咧开。“别起来。”米开广说。任宠的头又掉下去。
蓝文定从石坎高处往里挤。“当心点。”米开广说。
“怎么样啊,小老弟?”蓝文定说,气喘吁吁的。
任宠想说什么,嘴一张,流出一大股鲜血,牙齿都是红的。没有东西给他擦嘴,他们的手都很脏。“是颗燃烧弹,滚到了洞口。”任宠说。
“我们都知道了。”蓝文定说。
“把煤油炉炸着了。呵,哨长。我把煤油桶掷到了洞外。我怕它爆炸。”
“好。做得好。”米开广说。
“看看身上。”蓝文定说。
米开广小心地展开湿棉被。胸脯上起了一片一片的血泡,两肩的血泡很多很密。一道焦煳的烂肉从左胸下肋斜到右腹下,渗着血液。这好像是因为触到了烧烫的枪身。两只手放在身边,两手掌上都是血泡,小腹部伤得很厉害,不堪入目。脚底上的硬肉几乎撕光了。不过大面积深度烧伤的,好像很少或者没有。还好还好。米开广喘了几口粗气。
“你刚才差点把我捂死了。”任宠脸上起了一点微笑,“棉被包住了我的头。”
“你不该那样抱着机枪。”米开广望向顾家荣,“电话还能打吗?你去看看。”
“电话机是好的,放在顾家荣的铺角上。”任宠说,“可我把电话线扯断了。”
“线都烧烂了,肯定的。”蓝文定说。
米开广在想怎么向连首长报告。在采取正式行动之前,他摸到自己脚底几个烫伤的泡,在右脚。他心头隐隐兜起一丝说不出来的烦恼、悔恨和懊丧,然而又觉得用不着他来烦恼、悔恨、懊丧,总之感到不舒服又没有办法发泄。枪是战士的生命。爱枪是战士的天性。把任宠换成米开广自己,他也会那么做。然而,很可能,他还没有任宠这新兵娃儿那么细心,发现木柄已在燃烧的手榴弹,把它们掷出洞去……
电筒光的圆圈边,米开广能看到任宠眼里的泪花。“哨长,能把我送到医院去吗?我疼……”
“一定把你送下去,一定。就今天晚上!”米开广说,“我会想办法尽快报告连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