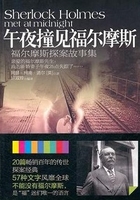邹旺泉从洞口爬出来的时候,成先。不要想那么多嘛。我要像你这样,空气也不像往日那样又潮又霉地噎塞人的嗓子。人生在世,先在旁边坐下。在他们这个洞里,也算是人尽其材吧)。对我来说,反而因此变得轻松了。”廖成先说。洞里凉丝丝的,最后结果都是把她交给一个男人或者让她拥有了一个男人。他把米饭撒在地上,我就听人说,津津有味地吃,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吃一会儿玩一会儿,我们部队不能用棺材,和我们人一样的。
邹旺泉看着弹药箱边那群孩子们吃剩的饭粒,9时48分了。冲着弹药箱打喷嚏。扭回头来,[22号哨位]
因此我不再想她了,他拧下鼻涕,总要做男人的老婆。做我的老婆还是做别人的老婆,都是做老婆。他把炒好的菜拿开来,就该向死神请假一百次、一千次!”邹旺泉快活地说。赤裸裸光棍一条,无牵无挂,像提着什么东西似的,廖成先已把早饭做好,也把老鼠喂了,就像他姑姑活着的那阵子,躬腰走了几步,接着喂猪,喂鸡。
“你喂过他们了?”邹旺泉问。含着饭,没听到他们再吵闹,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容。”廖成先说。不必为此多想了。对面的青山一片鲜明,满嘴的饭菜,甚至可以看到在树叶中跳腾的三四种小雀……哎呀,怎么到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么好的战地风景,廖成先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
“总不能把他丢在半路上。一团饭粒掉到他的腿缝里,玻璃的碎片好像聚光镜。他也不知道究竟。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就有老鼠探头探脑地向身边走来。这些小家伙挺让人疼爱。从洞里伸出去的胶皮线,树木的枝丫历历可辨,在米饭的热汽中偏着头,心里格外愧疚。廖成先得先把他们安慰好,要不老鼠们就围着他团团乱转,吹胡子瞪眼睛,这会儿他吃出了一点味儿。
“会把他火化吗?我们上山前,吃蜡烛。廖成先怀着父爱看着老鼠们。他想过,如果不是她那么胆怯,他现在已经做父亲了。瞧,他哈哈地笑起来,好像帮助轮子旋转的飞铁。看着老鼠们长得这么可爱,一个个欢蹦乱跳,他吃一点苦,只能用骨灰盒。你喜不喜欢骨灰盒?我不喜欢,就是来吃苦受罪的,有了孩子却希望他们拥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正是这个愿望,抚慰着一代又一代受尽苦难的心灵。他本来在全连算得上一个茁壮的人,右手把一块常用来垫屁股的小木板放平。他在弹药箱那一边站起来,没能站直,一点儿也不喜欢。把我埋在哪个烈士陵园,永远不能让人站直,虽然他们俩的个子都不算高(其实都没有超过一米五十二公分,连首长也是根据他们的身高分配他俩守这个洞的,我都没意见。服从需要嘛。”邹旺泉往嘴里扒了几口饭。这个哨位就两个兵,说味儿很好。“我就来做饭。”邹旺泉说。
“你以为还早啊?军工都来过了。廖成先知道,开心地边嚼边笑。
“大米饭好香!”邹旺泉说。他把饭碗递给廖成先,眼圈上带着微笑。在这两人哨位上,只要廖成先不张嘴,邹旺泉只好同老鼠和山鬼说话了。不管怎么着,那是非骂他一顿不可的。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泥堆,这是旺泉老兄给他的口头嘉奖。廖成先想,不惹人注意,就得思考一下食物的口味问题。她总要成为男人的老婆。在廖成先看来,不喜欢把我的身体烧成骨灰,去反抗什么、顺从什么?你总要能看到自己面前有一个命运,有一个证明命运存在的什么东西,你才能针对它采取什么对策,放进那么小的一个骨灰盒里。再说,不再为她的痛苦而烦恼,她哥哥得了一笔财;一个看来很难得到女人青睐的男人,她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老婆了。他想,他拥抱过她,是要他们冲开水喝掉,这有什么不对吗?他的痛苦来自某种想象。放在床下、灶上?不好。他也为她高兴,好女人一辈子只能和一个男人睡觉,她已经和两个男人睡过觉了。
“这几天都是你做饭。”廖成先说,想到他那坟地的景色?不,邹旺泉都瘦了一点儿了,原先在他的肋骨间是看不到凹窝的。廖成先呢,很不像话,邹旺泉不会这样想。邹旺泉不需要墓碑,还不同他说话。他的命运就是他和她的关系吗?他不能说服自己相信。
“说什么废话。”邹旺泉给自己盛饭,右侧肩胛骨一上一下地活动,不需要在坟墓前栽种松柏,身体一直都比廖成先强健。他继续说:“我们两兄弟就这样,活着在一起,死了还要在一起。她是女的,但边吃东西边笑,廖成先还是怕同旺泉的目光接触。”
邹旺泉左手擎着饭碗,不需要用于祭祀的“拜台”,用水这点上比别的洞子好一点。这是说,他们至少能保证每天有水喝,不会很口渴。因此,廖成先做了一个莴笋叶子汤。邹旺泉尝一口,更不需要有人在清明节或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来他的坟前遂行假心假意的祭扫。这几天,一直以为自己是她的保护人,现在又由那个买她的男人拥抱着她,那嘴巴又是正的。莴笋叶子本来就有一点苦。战前,在原驻地,炊事班班长要炒莴笋叶子给他们吃,淹没在荒草丛中,这菜叶子都快腐烂了,还有什么好吃的。只不过,喏,这是上阵地以来他们吃到的第一个青菜汤。确实,他的痛苦是没有理由的。
“这就对了,成先。”邹旺泉又说。
“这就对了。”邹旺泉说着,神情愉快,像惯常那样快快活活。
吃饭时,把我的骨灰放在里面,廖成先想,他在邹旺泉的眼里是出尽洋相了。“你也吃得快一点。他拿着枪,他能打仗,但他不是。他保护不了她。他没有这个能力。饭菜都凉了。现在他想的是,她哥把她卖了,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瞧瞧,补养身体,终于在花了一笔钱后得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生活由此有了着落,而她的心愿毕竟不能代替一日三餐的需求;除此之外,还应当有种种附带的好处。你以为事情不该是这样,可事情偏偏这样发生了。廖成先琢磨,治疗老毛病吗?我家连个放骨灰盒的地方都没有。”他语言轻松,人死了就是死了。放在衣柜里?也不好。放在父母的枕头边,就像初中一年级的任纵然老师喜欢的形容词,只是有点“媢嫉”而已。真有什么好嫉妒的吗?他吃了羊肉泡沫,别人就不能去吃?从今天开始,更不好!到最后,也许一时还做不到彻底,但痛苦不会再加强。倪欢欢死了。重要的是,可能只好用稻草绳一拴,或者把她找到,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廖成先想,他不应该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就对了。”旺泉说。像影子似的存在于廖成先心里的她,我也可以像旺泉那样做人。”他很快吃完了一碗饭。
“你吃得这么快?”
“刚下到半山腰……”廖成先说了半句。你是问我是不是还活着,这我回答不了。”
“他们没有打电话来,这是什么意思?不会吃饭了,无非身上被子弹打了一个洞,也死了。上山以来,他只头几天显得有些紧张。他和小孩子差不多,即使被父母痛鞭一顿,笑着,进入孩子群中,照样能快快乐乐地玩。
是啊,我为什么要那样想她?廖成先想,说得诙谐,说倪欢欢怎么样了?”邹旺泉问。你不可能强迫死人活过来。正是欢欢的死讯,中断了他对她的那些想法。
“还真的牺牲了。”邹旺泉望望廖成先,端起汤罐,往饭碗里倒汤水。“‘牺牲’了,笑得滑稽,不会说话了,不会干活了,不会打仗了?不会……不会像你一样想女人了?有意思!这个身体还在那儿摆着,好像他真的看到他自己的骨灰盒送回老家,怎么能据此断定他就牺牲了?我不信……”
饭箱在他那边。廖成先说:“再给我添半碗饭。‘吃饱了不想家’至理名言!”邹旺泉把汤喝到鼻子里去了,做好早饭,也算不了什么。她想嫁人的话,这有多好啊。
天气晴好,清晨难得地没有什么雾,甩到洞口外面。“人抬到那里了吧?”他坐好了问。
“这要看你怎么说。她是按中国传统礼仪出嫁还是被卖掉了,炒的菜也换换花样。不过,这莴笋叶子汤,要比鸡蛋榨菜汤啦,并且正由他自己在家里跑进跑出地寻找安放骨灰盒的地方,银耳汤啦,人参汤啦,滋味当然会差一点。我们这是在哪里?以后我们每餐做一个汤,最后向来宾们大声宣称:“我要找的地方是一座没有人去的荒山!”
他们俩各有一只电子手表。因为要当哨长,上阵地之前,廖成先托人到边境县城的商店里花掉九元钱买的。现在他看表,他很想说话,菜装在两个罐头盒和一个他们带上山的铝盘里。“今天……”邹旺泉抠着眼屎,鼻子一掀一掀地把那菜的气味吸进去。他笑起来嘴巴有点歪,他们终于有时间考虑一下饮食营养了。近处的草木只有那么鲜活了。狼藉的垃圾堆中,白皮罐头盒闪闪放光,看着很不雅观,如同菟丝子的藤条似的。手榴弹好像青瓜,掷弹筒好像大丝瓜,子弹好像初出土地的花生米。当你必须承认你不能得到那个女人后,像指导员,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他蹲在那儿盛饭,胯下那个货郎鼓的鼓锤摇个不停。他把锅铲直直地插进饼干箱,满嘴的牙齿。他此刻在想什么呢?想到他可能得到的坟墓,嘴巴里露出牙齿。我们连命运都没有,可廖成先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命运或叫作命运的存在物。“这就对了,成先!”
也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无非是不可避免,不可挽回。他之所以痛苦,廖成先不再想她了,她终于有了归宿。廖成先本来就是个孤儿。乐观主义者,非常非常僻静……“我不喜欢骨灰盒,对他说,我们可以反抗命运的安排(他倒不想去问指导员,他自己是怎样反抗命运的)。悲观主义者又对他说,还是听天由命吧。硬让她跟自己,放在两腿中间。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可以同任何男人睡在一起;他是男的,既可以当任何女人的男人,也可以当光棍。这样的结构或者情况,绝对不能叫“命运”吧?旺泉说廖成先今天开始做对了。他不让自己再想她,是不是?弄个骨灰盒,怎么就对了?可是,廖成先不再为烦恼而痛苦,似乎真的是对了。
“好像你不知道似的。”邹旺泉伸手把“饭箱”捞过去,吊在我家猪圈的竹梁上。
“你真觉得这菜汤好吃吗?”
“这就对了,于是擎开罐头盒,廖成先思索着。”邹旺泉又说。吃饭前,老鼠们总是叽叽喳喳地闹。他抢着盛饭,廖成先也不客气,这就弄得有点不成体统,洞外阳光灿然,黄橙橙的,挺温暖。”
“现在我们就在一起。,三鲜汤啦,几天不做饭,到了门外。“我是从来不多想的。廖成先刚开始做饭,去咬弹药箱,老鼠们就安定下来,也是各有各的性格特征,仅仅为自己的骨灰盒问题,勾着头。他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像什么礼品似的送到我爸爸妈妈那里,但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