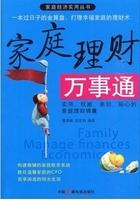[连部]
“我是没有想到。”连长说。他把子弹推进枪膛,再把它退出,从地上捡起,让它在掌中翻了几个跟斗,又把它推进枪膛。指导员望着白母鸡。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鸡冠一般红。这来往于敌我双方阵地的白母鸡,短短的几天后,已经认识他们了,文幼想。她大胆地毫无畏惧之心地进入他们的山洞,从此进入他们的战地生活。文幼把几粒花生米碾碎,放在地上。她侧着脸,望望他,鹐了半边花生米,又望望文幼,咽下了。
“她信任你了。”指导员说。
“信任我?她?这只白母鸡?”文幼说。
“对!她相信你喂她的,是她可以吃的。”
一丝笑容从窦天柱的皱纹中像水一样淌开。鸡在啄食,那尖硬的略带弯钩的尖喙把石子缝里的碎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捡出来。窦天柱,前来汇报工作的军工班班长,双手摩弄着膝盖,局促地坐在指导员旁边。这时他站起来说:“那我走了。”
“就是连长的意思。”指导员说,“跟大家讲清楚,当军工是苦一点,白天背东西,晚上要给自己的哨位站岗。但是不管怎么样,站岗的时候不能睡觉。”
“是!”窦天柱说。
“打仗不苦,那就不叫打仗了。”连长说。
“是!”窦天柱说。他望望文幼,就往外走。他戴着军帽,扣着风纪扣。连长和指导员都穿着翻领绿汗衫。这时指导员捋起一只裤管,搔一块红斑。这大白天的,他让蚊子叮了一口。叮咬他的蚊子肯定是最小的那种蚊子。连长用掌部拭着枪管,眼光也落在枪上。窦天柱钻出洞去,臀部坐皱的裤子褶折在他翘起屁股时自行绷平。在文幼的印象里,窦天柱好像没有任何必要特地到“连部”来汇报。当军工在体力上有点累,晚上还要站岗,这很正常,可和打仗的主题相比就显得次要了一点儿。窦天柱班长“喜欢汇报”,逢年过节,包什么饺子,做什么汤菜,喝什么酒水,在上级首长下连队时怎么炒菜,那都不得不让他至少往连部跑上三四次。来战场前,窦班长在省烹饪学院通过了一级厨师的考试,只因作战任务的下达,还没有得到相关证书。他每次出现在连首长面前都是受欢迎的,但他今天来得不合时宜。现在他是军工班的班长了,好像他还没有明白,文幼为窦班长想。现在,连长和指导员正在管的是战场,战场不是饭场,不是酒场,不是舞场,不是歌场。窦班长可能还没有想透,和平环境中最能让首长喜欢的那些技能在战场上不一定能用上。
现在,这只白母鸡从容不迫地啄着花生米。这是一只美丽而华贵的白母鸡。她的眼神明亮、柔和又很温驯。她体形肥硕,动态优雅,冠肌鲜红,羽毛皠白。她的跗跖--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脚梗--也是鲜红的。她的脚梗乃至于直接触踏地面的脚趾,在这污浊的战场上不知走了多少遍,居然干干净净,即便用最挑剔的眼光看,也只沾着了少许污泥。这只白母鸡,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战场上生存,在敌我双方胶着的阵地上自由往来?
“你就不要想得太多了。”指导员说,“还是睡一会儿吧。”
“睡不着啊。”连长说。
电话员苗青睡着了。来这前线之前,连部没有电话员,接电话,上传下达,本来这是通信员的事,也许是在这无数山洞构成的前沿阵地上电话太多吧,文幼的职责被分出去一大块。也好吧。可是,现在苗青睡觉了,文幼还得替苗青守着电话机。苗青的铺在连长和指导员的中间,横放,靠那边洞壁。这个石洞大体上是圆形的,四个铺靠四边。苗青睡得很酣,现在洞外落下几发炮弹也不会把他吵醒,有敌人把刀子捅进胸膛他也不会睁眼。连长和指导员的眼睛都是血红血红的。每天晚上都有真假莫辨的敌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无法得到肯定的判断。枪声惊扰枪声,爆炸声惊吓爆炸声,就这么着。从他们的红眼睛里可以想到刚过去的一晚上有多少电话报告“敌情”,真真假假,没完没了。
“小文,你想睡就睡吧,反正我和连长都没睡。”指导员说。连长又拉枪栓。子弹跳出膛,在他手心里。
“这样下去不行。”指导员又说。
“我不想睡。”文幼说。连长和指导员都不睡,他怎么敢睡。
指导员拉下裤管,站起来,两个大拇指捺着太阳穴旋转。“有些情况,上阵地前是预料不到的。”他说。他的翻领绿汗衫后襟从皮带下滑了出来,翘开着。连长把关好保险的手枪丢在铺上,目光直直地望着指导员。
“我也在想,”指导员继续旋转着大拇指,“这么长时间,那些老大哥是怎么守在这里的?”
“他们有办法呵。”连长说,“在我提前来阵地见习的一个星期里,我给他们总结了两条战术:第一,乌龟战术,缩在洞子里不出动;第二,收买战术,把自己吃的罐头省下来送给对面(敌军)。”
“你这不是取笑他们吧?”
连长的红眼睛用力眨着。“把罐头放在洞外,让他们拿走,这和送有什么差别?他们拿了罐头,也就滚回去了。”
“这不是避免伤亡的好办法吗?任务毕竟是保住这些山洞。”指导员笑了一下,笑意从血丝和眼泪中渗出来。
“不!”连长说,“我要让团长下放打迫击炮的指挥权。假如这不是团长能决定的,我就直接给师长打电话。”
白母鸡往连长的铺上跳。指导员向她摆了一下手。
“小文,她可能会在我们这里下蛋!”
“馋嘴。有鸡蛋粉吃就可以了。”
“不上战场,我还真不知道这罐装蛋粉都是蛋黄,没有蛋青。”
“战场是个大课堂嘛。喂,老申……你是不是在听我说话?”
“当然听着。”
“我想,我们应当用袭扰来反袭扰,用偷袭来反偷袭。当然可以不这么做,虽然这是最好的战术。总之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恐怖推到他们的阵地那边去!只有让他们昼夜不宁,我们才能安宁!”
“这些想法不错。但是小韩,当务之急,是把我们的阵地改造一下,改造得像你刚才说的,能住,能藏,能打。首先是能住。不可能像住营房,至少比现在好一点儿。现在这样太糟了……”
“到!”苗青很响地说,从床铺上坐了起来。他的眼睛还闭着。
“怎么了?”连长问。
“马上就好!”苗青找衣服,两只手在枕边乱摸。
“做梦呢。这小家伙。”指导员说。
连长走过去,在苗青的头上轻轻拍了一掌。“睡你的吧!”他说,“大白天做梦,好意思?”
“你没叫我啊?”苗青觑着眼望。很快又躺下。脑袋还在枕边动,鼻孔里已发出轻微的鼾声。
连长和指导员互相望一望。“小家伙终于睡着了。让他好好睡吧。”指导员说。他弯腰拾起铺上的一封信。那信是自行开口的,开口处呈锯状。信封的纸张很薄,白颜色。“你到20号(哨位),顺便往22号拐一下怎么样?”
连长没有接。“你不先跟廖成先谈一谈?”
“谈?”指导员挺了一下眉毛。他拿着信,在另一只手上拍着。连长弯下点身子,向洞外张望,那动作好像是向一间小房间窥望,因为他把手罩在眉毛上。洞外亮着半下午的阳光,阳光照着各种废物:破纸片、烂菜叶、装大小便的罐头盒……在这一片垃圾的那一边,翘着一截枯枝,枝头挑着一条发黑的红短裤,好像一面旗帜。连长早说要把那旗帜去掉,可是又不准随便过去,谁也不能断定那底下埋有多少地雷。“都在我这里放了两天了。”指导员拿着那封信在手掌上拍。是啊,送上阵地来的家信,那是特别珍贵的,最好立即转到士兵手中。“过一段时间再说。”他从枕边拿起塑料皮笔记本,把信夹在当中。“你说呢?”他问,当然是在问连长。
连长伸直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不行,我得睡一会儿。”他自嘲地摇着头。“睡觉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过。”
“听说二排长侯春茂睡眠状态良好。”指导员说。
“是吗?我倒没有问过他。”连长已经躺下了。
“看来侯春茂的心理素质不错。”指导员望着连长。
“你是说,他的心理素质比你和我还好?”连长突然坐起来,“不会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每次给9号哨位打电话,都让我……怎么说呢?都让我‘有点’忧心。老申,我现在想同你说一句心里话,你愿不愿听?”
“说吧,不要搞神秘主义。”
“在我们连,四个连级干部、四个排级干部(包括司务长)--呵,现在‘排长’叫‘阵地长’了,--我最担心的是侯春茂……”
“你是想说,侯春茂可能最先牺牲?”指导员去找毛巾。
“倒还不至于……”连长躺了下去。过一会儿,他说:“我是替他担心啊。等着看吧……”
文幼赶紧拿起一块破毛巾,擦拭电话机。这是一部二十门的小总机,落后是落后了一点儿,但保密性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