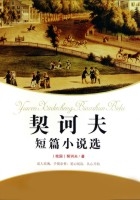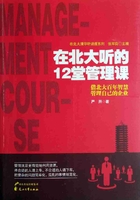我闭上眼睛。关鸿坐起来,窸窸窣窣脱了,很快滑进我的怀里。我的手便抚在她光滑细腻的身上了。关鸿两只胳膊用力箍紧自己,拼力抵抗着,急切地说:“不能的,不能的,以后招工过不了体检关……”
我那时只想要占有她,哪里还顾得上她以后的体检。我把她按在了身下。关鸿很快不抵抗了,只把牙关咬得很响。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温存,就像一个手艺生疏的庖丁。关鸿自始至终忍着,没有叫出声来。
然后她把背对着我,一个人小声哭到天亮。
以后的十几天,关鸿一直回避着我,不和我说话,甚至不看我一眼。她的眼睛是红的,脸色苍白无血,嘴唇干燥,头发从额上坠下来,绷得很紧,那样子就像一只陷入了绝境的小动物。她每天仍去出工,荷了锄头,匆匆地出门,匆匆地进门,烧火做饭,把饭盛到桌上,端着碗,让自己对着墙壁,连桌子都不挨一下,一句话都不说。
第二天晚上,她没有到我的小矮屋里来,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来。吃过晚饭后,她很快把自己反闩在自己屋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我推她的门,求她允许我进去。我说你开门。我说我不要,我们好好坐着,摆龙门阵。她不答应,也不开门,像死了似的。我自知无望,知道没有什么能说服她,但没有她我再不愿独自回到我的矮屋里去。
那是秋天里发生的事。生产队里收山坡上种的红苕,按人头,每天都有几十百把斤新出土的红苕要分。清早上山,挖完一片山的红苕,天就黑了,再一家一户一秤一秤分完,天就更黑了,黑得不像样子。男女老少打着枯葵秸缠成的火把,背着红苕下山,火把连绵不断,一气衔出十几里,红苕的清香味也一气衔出十几里。狗们娃儿们惊咋咋地欢吼着,像过节。阿格龙不吼,严肃认真地在我前面带路,有时路边窜出一只草兔或乌蛇,它也不屑一顾,任它们来去,决不捕杀,只是在很难走的沟沟坎坎处,它先站下来,歪了头看我,示意那里有障碍,等我吃力地通过了,再走。
五斤红苕抵一斤谷,每天晚上我都去帮关鸿背回分给我们的那一份口粮,我们要靠那些红苕活到来年开春。关鸿把自己关进她屋里时,我就执拗地坐在堂屋里择新分的红苕,把被锄伤过的、冒了浆的、瘦小死色的挑出来,尽快吃掉,其余的下窖过冬。新出土的红苕味道很好闻,有一种新鲜泥土不安分的腥甜气息。山风不老实,从门缝外往屋里挤,灶膛里的草木灰下,时而哔剥着跳出几颗火星,灯焰摇曳如舞,再加上那种新鲜泥土不安分的腥甜气息,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老山安静下来后的神秘。我就那么手脚不住地择红苕。择不择红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那么坐着,坐在堂屋里。还有阿格龙。
等到第十五天的时候,关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关鸿单薄无力地倚在门柱上,低着头,像一片纸剪成的人儿。倚了一会儿,她离了门柱,走出来,没看我,也没同我说话,径直进了我的矮屋。
六
秋天过去后,阿格龙和米娜都长成大狗了。
米娜越发出落得美丽,毛皮比最洁白的羊羔还要白,一对多情的眼睛汪着潮润,盼顾有韵。关鸿教会它不少杂耍,比如起立、卧倒、作揖、摇头晃脑,甚至还教会了它数数。关鸿伸出两个指头,它就叫两声,伸出三个指头,它就叫三声。最有意思的节目是咬尾巴。关鸿说:“米娜咬尾巴。”米娜就转过头来努力去咬自己的尾巴,越向前够越够不着,陀螺般急速旋转成一团白云,逗得我和关鸿捧腹大笑。
阿格龙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教米娜的那些游戏,我们逗米娜的时候,阿格龙总是站在一旁,目光冷漠地看着我们。节目一停下来,阿格龙就走过去,伸出舌头舔米娜,为娇喘吁吁的米娜舔顺弄乱的毛,然后再带米娜去池塘里喝水。它从来不在游戏结束之后走到关鸿面前去。它知道,关鸿丢出的加了糖精的玉米甜粑粑,是绝对没有它的份的,那是犒赏殷勤懂事的米娜的。
阿格龙已经长成了一条雄壮深沉的大狗。它不再那么顽皮得四处撒野,也不再去山上追逐土拨鼠和山蛙一类的野物吃,它开始显示出成熟的淡泊,对越来越多的事物表示出冷漠的神色和态度。儿时的那些游戏,仿佛再也引不起它的兴趣。
阿格龙常常独自伫立在高坡上面,把它巨大的头颅歪向有缺陷的那一边,凝视远方,屏息不动,任山风吹抚它一身漆黑油亮的毛发。偶尔会有一只长尾山鸡从草丛中惊鸣飞起,它也不去追逐,只是在喉间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下腹轻微颤抖着,压抑着焦灼和激动,让人隐隐觉出在它身上潜藏着的杀戮之意。
阿格龙真正显示出它的天才,充分表现它无可抵挡的搏击能力,是在一场纯属偶然的遭遇战中。那场战斗,使阿格龙成为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狗。
那一年初秋,生产队派了十几名壮劳力到万县挑运冬洋芋种,我是其中一个。我决定带上阿格龙。
我带阿格龙去万县挑洋芋种的决定遭到了关鸿的反对。关鸿说,四百多公里的路,大多是崎岖的山路,每人得挑百十斤的担子,自己照顾自己已经是很难的事了,哪里还有精力照管一条狗。再说,狗的职责--假如狗有职责的话--应该是看门,能在家门口耍耍威风已经算得上一条好狗了,带它跑那么远的路,跑丢了还算万幸,若捅出什么娄子可就麻烦了。
我知道关鸿那点儿小心眼。临行前,关鸿把我们小春吃剩的所有麦面都烙成了野葱饼,让我带着上路。与其说她是担心阿格龙在外面给我添麻烦,还不如说怕阿格龙和我共同分享了那些美食--而那以后,我和阿格龙正是这么做的。
我很固执。我相信阿格龙不是那种一离开家门就傻了眼的蠢货。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阿格龙和我在一起,我甚至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此行非得带上阿格龙不可。
阿格龙看着关鸿给我烙野葱饼,收拾东西,知道此行是一次远征,显示出兴奋的样子。在关鸿给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它与米娜做过许多次亲昵而又壮烈的告别。在性格温顺的米娜眼里,体格魁梧的阿格龙显然是一条英雄汉子,所以那两天,米娜对阿格龙极尽妩媚之能事,整天缠着阿格龙撒娇,弄得阿格龙魂不附体。
四百多公里路,我们二十多条壮汉子,只用了六天多就赶到了万县。除了磨穿两双新草鞋外,精神和体力都保持得很好。到先前联系好的白马公社看过洋芋种,人家很支持,称洋芋种的时候,秤杆翘得旺旺的,称完了还饶上二十斤,说是耗头。晚上我们队长吴卿有弄了一点儿米去,求人家借个火煮顿干饭,吃过第二天好有力气赶路。对方的队长很慷慨,看也不看就把米袋子丢了回来,大声武气吩咐下面的人煮一大锅洋芋米饭,下饭的是一大碗辣酱,撑得我们没有一个肚子不痛。黑儿吃完又偷偷捏了两个饭坨藏起,说要带到路上吃。问那个给我们煮饭的大娘,才知道白马公社是万县学大寨的典型,一个工分日值七角几分钱,听得大家瞠目结舌,顿时有来到天堂之感,羡慕得不得了。
当日在谷场上睡了一晚,次日天不亮就起程。除了我之外,二十多个人,每人一百二一挑。队长吴卿有说我伤刚好,创口挣不得,我那一挑只装了七八十斤。众人挑担起程,以后晓行夜宿,每日赶路。远行无轻担,我那副挑子虽说最轻,却日日时时都在长斤两,时间长了,肩头磨破了,露出了嫩肉,担子一上肩,火烧火燎地疼。
八天以后,我们进入灵通公社的山界,离我们队里,也就隔着一座七子梁山了。一嗅到山风里那熟悉的水土味,疲倦的汉子们一个个都活泛了,又说又笑,满嘴冒腥气:
“日他妈,这一走上十天,我堂客怕早把活儿忘得一干二净,今天回屋,头一桩事就是帮我堂客铲青苔。”
“王黑儿,你娃儿小心点,莫把你堂客打穿啰。”
“担冤枉心思,你只把你堂客招呼好就行了。”
“嘿嘿……”
听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闹着,我也十分愉快地想着关鸿,想她总是惊魂未定的杏眼,想她黑色瀑布似一泻而下的长发,想她颈下那片蜂蜜般橙黄的肌肤,想得身上一阵阵发躁。出来这些日子,关鸿从来不在我的梦里,倒是离家近了,就开始想她。都说古时的征人就这样,人在外,只想月亮,不想家中的女人,否则牵挂太多,是回不来的。我想我更多的是把关鸿当做一个年龄比我大的女人来眷恋,而不是爱人。
我们就这样嘴里疯癫心里抽搐着走进一座村子。那个村子隐藏在深山里,山路傍村而过,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村头玩耍,其中有一个剃月牙头的小男孩,赤着腚,一条脏兮兮的花狗跟在他后面,不住地伸出粉红的长舌去舔小男孩的屁股,看模样那小男孩刚屙完屎。小男孩站在村道旁,斜着眼睛看我们一个个挑着担子走过,突然伸手从走在最后的黑儿挑子里抓了一个大洋芋,撒腿就跑。
黑儿放下担子就追,一边骂:“踢死你个砍脑壳的小泼皮!”
小男孩跑出一段,看看不如黑儿腿长,远远把洋芋丢过来,一边喊:“大龙,怂!大龙,怂!”
跟在小男孩身后的那条花狗听到命令,箭一般从斜刺里冲出来,冲着黑儿狂吠。黑儿站下,拾起一节树蔸扔去。花狗敏捷地跳开,爪子刮起一片干尘,转了一个圈,又扑过来。黑儿吓得连忙撒腿往回跑。小男孩就咧开嘴嘿嘿地笑,很得意。
我们都放下担子在那里看,看见黑儿的狼狈相,也都笑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好玩。我们赶了半天的路,累了,需要调节调节。我在担子上坐下,撩起衣襟揩了揩汗,伸手拍了拍身边阿格龙的颈子,说:“阿格龙。”
阿格龙一阵风似的刮出去,横在黑儿腿跟后面。撵上来的花狗毫不提防,撞在阿格龙身上,被撞出几尺远,在地上滚了一圈,愣了愣,爬起来,嗓眼里尖锐地拉着鸣,斜过身子,围着阿格龙转了两个半圈,泼剌一跳,冲着阿格龙的上颈就下口。阿格龙自小就玩皮实了,对这些虚张声势的扑剪腾挪不感兴趣,一甩屁股,往旁边让了一下,躲开了。花狗没有扑中目标,有些恼,复过身子,又是一个大跳,这回用心恶了,白晃晃两排犬牙露出来,连珐琅器的碰磕声都充耳可闻。阿格龙仍是往旁边一让,躲开,不过气色已经较先前不同,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坐在那里悠闲自得地扇着衣襟,知道阿格龙火山般的斗性已在极薄的地壳下涌动,地裂之处,一股股炙红的岩浆正在往下坍塌,识趣的最好远远走开。
活该花狗倒霉,偏偏不识趣,它见两扑虽没扑上,对方躲开了,却没有反击,以为自己有咬金之猛,对方无罗成之勇,气粗了,回过身子又是第三跳。
谁也没看清阿格龙是怎么迎上去的,反正这一回阿格龙没有再躲开,四足收束,也跳了起来,两只狗在半空中撞到一起,落下地时一声惨叫。再等两只狗爬起来时,那花的一个已经瘸了一条腿,缩着脖子,夹着尾巴,哀号着一溜烟逃开,连头也没敢回一下。
大家都笑,说阿格龙是假装憨子,不怀好心,不是好人。吴卿有收拾挑子,招呼大家说:“天色不早了,走哇。”
大家纷纷整理自己的挑子,正欲起肩,却发现有些不对劲儿。
在远处花狗不住气的哀叫声里,村子里四处都传来狗子的噪吠声。叫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近,差不多是一眨眼的时间,从土墙后、树丛间、坡坎上,一下子涌出了二十多条狗,冲将过来,远远近近挡住了我们,把我们围住,凶神恶煞地朝我们狂吠。这回是那些在村头玩耍的娃儿们笑了--我们被二十多条狗包围在圈子中间,进退不得。
黑儿一弓身,挑担在肩,吆喝了一声,打头朝狗们冲过去,想冲出包围圈。几头凶猛的狗立刻封锁了路口,一起扑过来,差点儿没把黑儿扑倒。黑儿只好退回圈子中间。我们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放下挑子,把扁担取下来握在手中,提防袭击。
阿格龙先是感到困惑,在二十几条狗子一起出现在村口的时候,它瞪大了那双没有白仁的眼睛,仿佛想要弄清楚它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在那里乱叫个什么。然后它也开始兴奋地叫起来,阿格龙的叫声和那些狗子的叫声不一样。那些狗子叫得很响亮,中气十足,有一种受到侵扰和侮辱的强烈愤怒,以及同仇敌忾报仇雪恨的英武之气。阿格龙的声音不然,有些喑哑,缺少悦耳的喉音,丝毫不设防,与其说是唱和,不如说是一下子看见那么多红的白的花的杂的同类而感到刺激和高兴。
二十几条狗铁桶一般围成一个圈子,并不进攻,大声地朝我们吠吼着,阻止我们逃离,同时不住地往后面张望,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一声穿透的、滚雷般的狗叫声从村子里传来,围着我们的那些狗们立刻竖起尾旗,叫声也变了,换成急促而兴奋的那一种。那些在村口玩耍的娃儿们转过头去,高兴地朝身后看。一阵沉重的黄尘高高扬起,出现在村子口,龙卷风似的朝我们滚过来。我们脚下的地皮在颤抖。我看见一段土墙的残垣摇晃着,刷刷落下一层沙土来。所有的狗突然一下严肃地闭住了嘴,不再吼叫。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威风凛凛的黄色的大狗,它的身子足有小牛犊那么大,硕大无朋的躯体令人心惊胆战。它有一双比狼眼还亮的眼睛--别忘了我是见过狼的--和两排巨大的粗糙的钢牙。它风一般卷到我们面前,离着十几步,站下了,高高的尘土没有停下,卷了过来,遮掩住我们,半天没有落尽。
我说那条黄色的大狗有小牛犊那么大,我的说法是绝对靠得住的,事情过去十几年了,我不止一次回忆过这一幕往事,那条黄狗威风凛凛硕大无朋的身躯一直令我心惊胆战。事后我问过吴卿有他们,他们都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狗,它那两排钢牙完全可以当一把上好的泥耙子使唤了,当然不能用它去吹谷子,它要去吹谷子谷子里会满是沙石。我敢保证,那条黄色大狗出现的时候,有人当时就把尿漏在裤裆里了。
只剩下阿格龙独自在那里愉快地吼叫着,那条巨大的黄狗出现的时候,它叫得更愉快,好像那个巨大的家伙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似的。很快,阿格龙就发现自己多情了。黄色的大狗站下后,阿格龙向着黄狗走出两步,嗅嗅地面,仰头叫了一声,大概是礼节性的招呼。可黄狗没有理它,只是冷冷地看着它。阿格龙似乎感到有些不解,有些错愕。它委屈但却又警觉地摇了摇耷拉下来的大耳朵,也站下了。
黄色的大狗后腿一弯,坐了下去,一动不动,神情沉重而阴郁。不知是它的暗示还是别的什么,一只狗率先冲出阵营,旋风般朝阿格龙扑来,紧接着,七八只狗一拥而上,扑向阿格龙。
这简直是一场不公正的厮杀!差不多有十只红了眼的狗把阿格龙团团围在中间,共同对付势单力薄的阿格龙。公平地说,那些狗,它们全都是勇敢无畏的,这从它们冒着青烟的牙齿和奓立如针的颈毛上可以看出来。但它们不是同一只完整的狗厮杀,它们各自对付着阿格龙的某一部分,严格地说,它们不过是面对着一条狗腿、一只狗眼或狗肋狗颈。
我大叫一声,挺着扁担冲了过去。斜刺里冲出几只狗,跳起来,将爪子扫向我的脸,阻止我接近阿格龙。我的衣服被一只狗撕开了,肚子也被一条狗狠狠地撞了一下。黑儿赶紧上来把我拖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