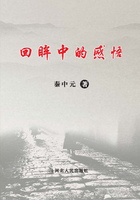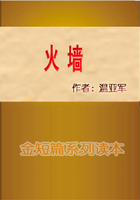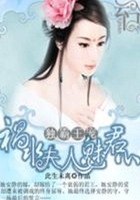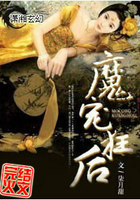如果你的生活还算宽裕,那么,每年计划一笔开支,带着孩子去旅行。
端端长大了,知道一个人跑出去玩了,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计划我们一家人一年中的一次或者两次外出。
我们距离最近的旅行是去端端的姑姑家。姑姑家在营城,邻铁道不远有一座独门独院,房子右侧还有一片大大的园子。姑姑家养鸡、养鸭,偶尔的一年还养猪,那里对于在都市生活的端端来讲,简直就是一个“自然博物馆”。
姑姑家的二表哥可以当端端的自然老师。
营城是一个小镇,曾经盛产大块煤,后来矿藏开掘尽了,一度繁华的街市渐渐冷清下来。
这里虽遭现代文明的侵扰,但有些地方自然风光保留得还算比较完整。至少,像端端这样的孩子,完全可以全身心地和他们梦想中的自然亲切地握手。
在姑姑家,端端接受了许多常识性教育。
他再也不认为西红柿是结在树上的,土豆是挂满枝头的。姑姑家的园子可谓“百草园”,那里边种有:白菜、香菜、茄子、西红柿、黄瓜、生菜、韭菜、豆角、辣椒、萝卜等十几种蔬菜,我和端端常一起蹲在那里,研究这些蔬菜的形状和特点。
端端在镇外的一条小河的回水湾处摸鱼。
还和他二表哥一起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山里采蘑菇。
记得一次雨后,我们骑上自行车,一同去土门岭的山里采蘑菇,雨后的空气十分新鲜。
小河横流,草色青碧,阳光在山林里被树木的叶子分隔得七零八落,鸟儿的啼唱显得那么婉转悠扬。
端端问:“表哥,蘑菇在什么地方?”
表哥说:“草地上、树根下都有,蘑菇喜欢成片儿地长,如果你采到一个蘑菇,没准儿就可以采到一筐蘑菇呢。”
端端信心百倍。此刻,他的内心全被这大自然的风景给迷住了!
让孩子在自然中学会感受。
1996年的秋天,我有机会去吉林市的松花湖看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我坚持要带端端同行。1996年,端端已经读书了,外出旅行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特意选择了一个大礼拜去赴约。
周五的晚上,我们乘晚班车赶到吉林,然后再搭乘朋友等候在那里的车前往松花湖宿营。秋夜凉,秋虫唧唧,湖风掠过堤岸,在空气中“飞短流长”。湖边渔灯点点,夜钓的人满怀执着和信心。
我们夜宿在远离大坝数十里的一处湖湾。
那里零星住着两三户人家。
几里外还有一位从南方一路追赶花期的养蜂人。
朋友们在张罗夜宴,我和端端坐在湖边感受湖风的沁凉,面对着黝黝的湖山进行着简单的对话。
我问端端:“你听见鱼儿在唱歌吗?”
端端说:“没有。”
我启发他:“仔细听。”
四周显得格外静。
好长好长时间,端端突然拉紧我的手说:“爸爸,我听见了。”
端端告诉我,他听见一条大鱼在给一条小鱼唱歌,唱的是《摇篮曲》,他说:“大鱼的声音像妈妈一样。”
我深受感动。
其实,孩子与自然之间是最通灵的啊,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堵塞了这条通道。
1998年夏天,我在北京驻寨的工作任务暂告结束,北归之前,端端和妈妈去北京看我,我们很珍视这次机会。除了带端端在北京参观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我们还特意安排出时间,去南京、苏州、镇江和扬州走了一圈。这几座城市的美丽自不必说了,单是它们的风物传说、历史遗迹,每一处都可以做一部断代史来阅读和评说。
这一程,我们走得很慢,在每一个地方都小住两日。我不期望端端一次就可以完全领略这些人间风景的全部含义,但我相信,这每一次切近的接触都会对他产生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一次,再一次,传统的频频不绝于耳的呼声,文化的灿烂,历史的无奈与悲凉都会激励和鼓舞孩子一生为他的目标去奋斗!
至少现在端端见到同伴再不会露怯。
他会说:“我去过营城。”
说:“我去过松花湖。”
说:“我去过北京。”
说:“我去过苏州。”
说:“……”
这绝对是一种成人无法体会的自豪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