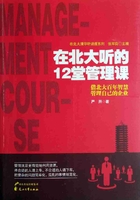与死亡有关的故事,现在才慢慢腾腾地开始。这些故事如同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一样,一点都不重要,但它们却确实存在着。有时我们还不无矫情地说,它们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一说法既虚假又真实。但无须深究,许多东西经不起哪怕一秒钟地揣摩,除非它们发生在我们生活之外。无任何刻薄与诋毁之意地说,一旦存在关系,即使关系并不密切——哪怕是牵强的感同身受,或者附庸风雅的虚伪理解,即使关系诞生并瞬间消灭在时间长河里,无丝毫痕迹从不曾向我们提醒它曾经存在过,即使它芜杂得像秋天的墙头草,我们也无法否认,它,像一根针一样微不足道地插进我们的血液里,并留下面目可憎的锈迹。
如同一个黑色的夹包,它曾经带着你的手纸和烟盒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见证了一次暂时有一些可能的意义的饭局上的邂逅,这对它亲眼目睹每时每刻与你擦肩而过的行人一样,于它将不产生任何影响,是否因此而带来厄运或内心虚构的良好愿望只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某一天,我们可以把时间假定为四年之后,你重新从满是灰尘的柜子顶端因为子虚乌有的契机把它翻弄下来,并从中发现了和马义那一刻面对的同样的东西,也许往事会像排山倒海一样汹涌而来,如果你的心还拥有所谓的并不可靠的宁静,和唐雨死亡后的马义一样,你可能也会在枯燥的生活中有了一丝难能可贵的触动或留恋,而且,片刻过后,你可能还会有一丝好奇,如同第三天黄昏深坐在秋天寂寥又令人躁动不安的灰暗天色里的黑色夹包面前的马义一样。
摆在马义脚下的黑色夹包以一种慵懒而不甘心的姿势,坦露无遗地显示着它的失宠,并以猝不及防的报复来弥补失去多年的原本就是毫无理由剥夺的穿越各种餐馆、街道、澡堂、会议且总是被搁置在最显眼角落的优越和快感。此刻,它裂开嘴,以冰冷而生锈的嘴唇嘲弄地看着马义,它里面除掉无孔不入的灰尘和一个硬得像冰块的口香糖外,只有一张匆匆撕下的长方形纸条。马义拿出来,里面记着四年前已经不复记忆的某一天,也许是他和唐雨初次见面的某个无聊的饭局上——当然生活只能虚构才能赋予不堪一击的美丽——唐雨以应付的手法给他写下的邮箱地址。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装相信,冥冥中确实存在天意,在四年之前,某个也可能是黯淡的令人生厌的即将对一切失望的秋天黄昏,唐雨应付陌生人马义而匆匆撕下的纸条,在四年之后物是人非的小楼里,将再次把马义带进一种全新的生活之中。它本身的意义仅止于此,至于它开启了什么既不决定于它,同样不决定于马义。
马义坐在电脑前,用唐雨的生日加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日期为密码打开了邮箱。电脑荧光屏在昏暗的室内泛出狰狞的白光,穿透不了黑夜,却与室外残留的无谓坚守的光线争执不下,彼此倾轧。机器内部以欢呼的战胜者般的腔调啃噬着灰尘,像是午夜某个房间内传出的梦幻似的惊呼。
唐雨的邮箱里邮件从三年之前就未曾读过。马义心头突然蒙上一层感动,唐雨当年给他的竟是私人邮箱,或许他该再仔细回忆一下具体情景,但马义最终拒绝自己这么做,没有必要兀自加上一些煽情的色彩和情愫,对一个已经走入另一个世界的女人,这样做更显得可笑。新邮件很少,除去马义这几年来给她写的几封道歉信(这也未曾读过)、广告,几乎没有什么人与她用这个邮箱联系。但在最上方,三天之前,也就是唐雨的最决绝的方式宣布与这个世界断绝一切关系的当天,比那个时辰早上一个小时左右,来了一封新邮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雨老婆,你好!
最近生活可好,想来以你的个性一定不至于太坏。当年我们就普遍认为温柔娴雅这个词是专门为你创造的。我很想念当初的日子,很想念你!
昨天,得知丁莹的噩耗,她死于车祸。一个想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方式,但是又那么容易让人接受,就像身边的某个人早上还微笑着和你打招呼出去,晚上却因为同样原因永远不能再回来一样。我很伤心,相信你听到后会是同样感受,记得当年有个周末的晚上,丁莹还整整写了两张纸的计划,说她能活到七十五岁,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要去大草原,然后死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起点上。
人生总是这么无情,让人稍一细想就觉得索然无味。请原谅,丁莹的死使我坚定了一个想法,但仍然拿不定最后主意,所以想请你参考下。
办公室里一个男同事,他妻子出国半年多了,简短说吧,和我发生了关系。你听来肯定会笑话我,但事实就是这样,除去许多感动和绚丽多彩的过程,无论其真假与否,有多少发乎我们内心?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就是这么简单而无趣,而且为了不影响你客观的判断,我也愿意刻意如此。
近来,他告诉我,出国在外的妻子要跟他离婚——瞧,多么俗套但又每天确实发生的故事吧,而他这个坏蛋,居然把责任、压力甚至道义和舆论的谴责全部推给了我,他居然厚着脸皮跟我说,如果我愿意跟他结婚,他就愿意和那女人离婚。你知道,以我当年那样而现在仍然令人遗憾的火爆个性,会毫不犹豫地来回抽他几十个耳光。
当然,你也可能会这样问,为什么要抽他耳光呢?有个男人爱你多好?我能理解,他或许是怕我拒绝才找出这种可笑而庸俗的理由的,他试图在我面前把自己变得强硬,但我能看出来,他很是惴惴不安。我不得不同样厚着脸皮说,你真是说道我心坎上了,你一定还是以前的你,单凭这点我就可以十二万分确信。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所以我没有抽他。
值得爱的男人太少了,而在此范围内,自己可以去爱的更少之又少。我们可能爱了一个男人一辈子,临死却发现他是个多么自私冷漠的家伙。你大可笑我幼稚,无论怎样,我愿意坚持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始终想以这种未婚女人的眼光去遴选男人,即使是远离真相,甚至与之相悖。
不必再多言。虽然你一直没有回过我邮件,算来我们已经五年来未曾联系,自从毕业你送我上火车之后。但我还是想发出这么一封信,我给自己,也给你——如果你没有收到,就算是给老天三天时间,三天后,我就要自作主张了,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
你亲爱的朱老公。
马义想都没想,仿佛自己就是唐雨,回过去三个字:甩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