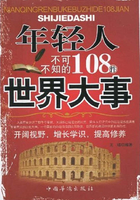直到第四天晚上,马义拉下书店的卷闸门准备回黑屋子时,才猛然明白自己的失策之处。无论他想见见“朱老公”的初衷是什么——他自己并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或者是拒绝多想。是想与这个相伴唐雨四年的伪老公深聊一下当年唐雨的生活和性格,抒发一下彼此的感伤之情?如果并没有啜泣到相对无言,也许还可以借机探讨一下唐雨的死亡动因——因为一个人的死亡其实从多年以前就有征兆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义是把自己排除在唐雨死亡的深层次原因之外的。因为没有一个犯错者愿意把自己的错误作为别人的批评对象。或者——直接说吧,马义如婚后的众多男人(配偶健在和已经死去)一样,企盼能够被动地发生些什么。
这种想法平日里不甚明晰,但正因此无处不在。即使某一个目标并没有切合他们意愿,也完全不足以让他们忧伤或焦虑,因为符合他们其实并不太渴望有下一步动作的纯粹想法的女人有无数个,她们遍布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站在你的对面等绿灯,与你擦肩而过,在某个服务机构穿着制服站起来对你说一声程式化的问候,骑着电动车从你身边一晃而过,风衣甩开得像一束洁白或火红的狗尾巴草,留给你一个婀娜的背影,或者端着盆子扭动着臃肿或苗条的腰身穿梭在某日你正好就餐的席间。或者她就在你长时间驻足凝望的橱窗内与你四目相对,并对你投以无法会意但显带诱惑的眼光。她们都是。无疑,朱老公符合这种想象,她不折不扣地是这群让人多情的女人中的一个,至少她与办公室男同事发生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天来,马义在书店里格外注目了各种各样的女人,从青春的十二三岁少女到七八十岁枯朽的老太婆。她们有些神采飞扬,有些面无表情。有些只是把书店当作临时避风的场所,焦灼或惴惴不安地望着马路上的行人或对面的某一家店门,等待或者似乎等待某个会也许不会出现的男人,有些只是一头扎进书堆里,躲在某个马义无法监视的角落里放肆而响亮地翻着书页。有些女人没完没了地与马义搭讪,天南海北地乱聊,仿佛在她们的心目中,书店的主人理应把普天下的书都看过了,却不知正因“卖席者睡炕,卖菜者只喝茶梗一样”,书店商人基本上是不看书的。也有些女人始终对马义的闲聊懒于应付,或者干脆装着没听到。几次下来,马义有些明白自己的意图,不容否认,他其实很想简便直接无后顾之忧地发生些什么。有那么几次,他其实也在一些休闲会所门前踯躅了几秒钟。我们无须苛责,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而女人唐雨死去已经有几个月了,或许还可以追溯到更长远的时间。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中间的某一天,他看到一个女人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去和她说些什么。这个女人年纪与唐雨相仿,甚至还戴着一条蓝色的丝巾,在脖子上环绕一圈在胸前打了一个优雅而蓬松的结。这种蓝丝巾马义恍惚记忆唐雨也有一只,但只配戴过几次就压在了箱底,表面的理由是唐雨扬言要和大学里的一切不成熟隔绝。马义之所以还有印象,是因为第二个冬天,那个老女人像驱赶不走的幽灵一样进驻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冬天,她就把家里翻了个朝天,并在某一天早上,她的脖子上就系上了蓝丝巾,像一截内部早已枯朽的老树桩在一夜之间竟发出了新芽,让人无法接受,甚至有些不寒而栗。
光临马义书店的这个年轻女人,坐立不安的模样使其看上去像一只折断翅膀的蝴蝶被狂风戏谑地卷动着,以极快的速度游走在书架之间。在她呆在书店的短暂时间里,几乎没有停息。偶尔有几次,她仿佛为了平息内心的焦虑而停下步子,站在马义的侧面,使得马义得以较为准确地观察她——不必隐瞒,不长的书店经营已经养成了马义坐在角落里观察女人的习惯,纵然以前在他课堂有那么青春妖娆,单纯到一个电话或一块巧克力就可以进行一次约会的女人,他却不曾留意。我们必须得承认,人的心理跟处境有关,而且还可以刻薄一点说,闲暇产生了欲念。
在马义的眼里,这个女人脖子上的蓝丝巾与上身紫色毛衣衬托出的玲珑胸部极不协调,并且由于她后面重叠两层的暗红色卷发的缘故,使她看上去就像脖子上前后挂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重物,而这些重物是从她的身体里侵袭出来的。和高档的肉色保暖丝袜以及尖而高跟的皮靴带来的具有侵略性能让男人不由自主从心中萌发出邪念的诱惑相比,她的面部表情却透露了她内心的枯寂。她也是一个自相矛盾体,和很多女人一样。她总是以蹙起的眉头、紧闭的嘴唇和时刻都紧紧收缩的鼻翼,伴随着从眯缝起的眼睛里射出的光,以一种怨愤的神色扫视着一切,书、马义、马路、行人和高楼。然而,这种怨愤又是无力的,它不仅慵懒,而且气若游丝,像一只飞蛾翅膀扇起的风掠过书页和马义的脸庞。没有重量,也形不成持久影响。
或许正因为如此,几分钟后,当这个女人冲向冬天泛白而冰冷的马路,并很快在前方街角向西拐而从马义视线里消失时,她也很快就从马义的想象中和心里消失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几次。每次他都可以从一些女人身上找到她们与唐雨的共同点,或者因为她们而刻意唤起对早已沉睡的年岁里某些可能不复记忆而自己却念念不忘甚至视若珍宝的细节的共同回忆。显然,她们不可能知道,她们期望热情拥抱的对象已长眠于城市西南角的公墓里,正与众多陌生的枯骨为伍。而马义拉下卷闸门的瞬间,他的另一个感觉也清晰无比,这四天里,“朱老公”并没有出现在书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