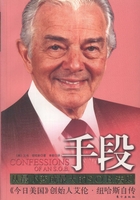梅蓝真的当着我的面拒绝过李玟一次。李玟未经通知地突然来访,梅蓝把她拒之门外,并且说,她正在和我吵架,为了乙肝携带者的事情。尴尬的是我,因为李玟在生活中早已经受打击,她不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抹平突然袭来的蔑视和攻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一生都用一种乙肝携带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及和这个世界有关的虚无缥缈的爱情和毫无保障的友谊。
苏秦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工作又丢了。想跟我见个面,喝喝酒聊聊天。我当着梅蓝的面说,我最近没空,梅蓝回来了。苏秦在电话那头由衷地高兴,他说,回来了好,那我过来吧,我也想见见梅蓝。我说,梅蓝现在不想见任何人,包括你我,包括空气,她厌恶这个世界的空气。苏秦没有感受到什么就挂了电话。迟钝总是让人不容易受到伤害。
梅蓝嘘嘘地笑起来。她正在看大街上发的房产地图,她想把这个曾经来过乙肝患者的房子卖了,再买一个从未进入过乙肝患者的新房子。我不能肯定,发给她宣传彩页的那个学生有没有肝病,把彩页分给那个学生的人有没有,运输彩页的人有没有,还有印刷和设计的,还有房产商、建筑商、那些面色蜡黄一瓶啤酒之后就能感叹生活如此美好倒在水泥地板上一分钟内就能呼噜四起的工人们呢,还有那些家具、电器、油漆等等的到新房子之前的所有程序中经过的人员有没有乙肝。乙肝早就无处不在了,空气从百万年前就不再纯净了,空气里,至今还有鼠疫、SAS、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呢。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纯净过。就像面对死亡一样,我们对空气中的成份无力改变,只能视之泰然。所以,梅蓝好像想做一个能改变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人。
我在网上搜索,看这个城市某个学校是不是突发奇想地在学期中间招教师。居然有,我便一个午后躲在卫生间里通知苏秦。他不置可否地听着电话,最后我以多年的友谊做威胁,逼迫他去试试。苏秦是那种无可无不可的人,他几乎从未因什么而受到打击。婚姻、孩子和工作,他从来没有如意过——而现在,梅蓝还想残忍地剥夺他的友谊。 对于一个平凡的人,一生的过往并不比大政治家简略,他仍然是自己生活的国王,他同样需要尊重。他和我类似的地方在于,只要手头还有一分钱,只要能活得下去,就没有什么值得焦头烂额的。活着,用苏秦的话说,只是活下去这样一件再纯粹不过的事情。但自从我爱上梅蓝之后,一切于我都改变了。在没有雷霆震动的平静之下,我却要在友谊与爱情中作出选择。可是,我对苏秦的友谊是可以说出原委的,但对梅蓝的爱情却不行。
几天后,苏秦电话跟我说,他已经把那个学校拿下了。我说,体检呢。他说,通过了。我征询地说,现在乙肝携带者也是可以通过体检的吧。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只是问问。他说,我不是乙肝携带者,体检一切正常,抗体良好,绝对比你良好。他又说,什么时候我们还是聚聚吧,其实,我早厌恶这种虚伪的教书育人的生活了,我不可能是学生的榜样,我没这个资格。如果不是你逼我,我肯定不去。他又在电话那头故意狂放地笑起来说,几年没体检了,想不到一切还正常,生活总是这般捉弄人。我能想象出苏秦在那边摇晃着手中体检报告的样子,轻蔑而略感悲凉。听他的口气,他的生活遭遇似乎只有身体状况恶化才能与之匹配。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很多人,生活一无是处,但他们身体就是健康无比。
梅蓝质问我,你信吗,你为什么不把体检报告要来看看呢。
我信,我不自觉就以一种顶撞的口气说,苏秦从未欺骗我。
梅蓝又沉思了,我真害怕她这种样子,总让一种莫名的恐惧酝酿在我心中,我无法猜测她将要吐出的话是不是像一个尖利的石子,让我所有的幸福和生活之轮改道。其实,我爱梅蓝什么呢。那个多年前的奔跑,和在她身后喘着气看着她洒脱的步伐和飘逸的头发的场景,这些年来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了,我不禁悲哀地感到那几乎成了全部。习惯使然,我对梅蓝的爱情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理由了。可是,在我与梅蓝的婚姻里,我连习惯都找不到。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可是梅蓝是那么喜欢突然消失。
梅蓝说,你确定你妈没有来过。
我说,我确定你爸和我妈都没有来过。
梅蓝说,你确定没有其他人来过。
我也略微沉思了片刻,我皱着眉头的样子只不过想给提问者梅蓝一种尊重感——这是不是源于某种担心。我说,我确定没有。
下篇
梅蓝又走了,但这一次不能说成是消失。梅蓝给我留了个字条,很长,在我的印象里,多年以来,梅蓝都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甚至给我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来,她都没跟我说过这么多话了。我拿着字条,才想起自己跟梅蓝之间的话不知从何时起就少了,好像结婚后,我们就只像拴在一个绳子上的蚂蚱,彼此角力,我们可以把绳子咬断,但是似乎是出乎惯性才没有这么做。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用梅蓝的话说,看成是诸如道德束缚之类的东西也未尝不可。我们似乎确实只是被道德拴在一起的,这样说一点也不悲哀,这才是这个世界上夫妻之间的常态,我们唯一应该悲哀的是,爱情,这种尊贵而华美的不该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从某一刻起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迹象地,就在我们心里死了。我们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不是稳定的三角形。我从梅蓝身上从未看出一个母亲的情绪,而她说,她从我身上都看不到一个丈夫的习性。
梅蓝留了字条,说明她自己也不把这一次当作失踪了,于是虽然同样是远走,但不同在于,这一次并非因于冲动、刺激、无以排解或者其他,我想认为她深思熟虑并不过分。这样似乎和前几次不同,她可能不会再在某一个黄昏,一身疲倦地出现在我面前了。
梅蓝留言的大意是,我该把苏秦的体检报告要过来看的,如果是,她就会认,如果不是,我就得认。我们在活着,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们不能和一个潜在的乙肝患者不明不白的交往。而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我当然一如从前,和苏秦喝酒聊天吹牛。更让她心绪不宁的是,如果苏秦确实正常,那么药到底是谁的,我们现在是活在一种乙肝病毒环伺的环境里。这个人还是一个可以进我们家门的人。她实在无法在这种思想和环境中生存下去,虽然生存对她只有这点难度,但她无法克服。她看着房子,看着床上的一切,她内心很焦渴,总是觉得吐不过气来。
甚至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她一直尽力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而我,却可以一蹲半小时。她看房间里的空气都是扭曲的,现在她回老家乡下去了,并且暂时还没有回来的打算,那里有新鲜的空气,一切都是绿色的。她已经很厌恶这个城市,她始终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黑匣子里,当她徜徉在街道上时,表面上一平如镜的她却总是万分恐惧地感觉周遭的高楼大厦就快要倾覆下来,她时刻都有被淹埋的危险,城市里除掉乙肝病毒和我,还有许多她不想见不愿深想的东西。她想宽阔而空荡荡地活着,什么都不想,就坐在门前发呆似的看着远方,或许,有时候她偶尔也会想起那年秋天的操场。她什么都没带,就带了那个风筝。金鱼送给我。
梅蓝记忆里的那个操场让我感动。在这个深秋的黄昏,我站在室内蒙昧不清的光线里,我发现梅蓝说的不错,空气确实扭曲着纠结在一起,它们还团成灰不溜秋的云状,以颇有力量的姿势毫不流动地悬浮着、潜伏着,伺机攻击什么。梅蓝走了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独处一室感到恐惧,因为我心里再也没有希望,我说过,如果梅蓝不是失踪,那么她的归来就更遥遥无期。我只是不明白,我们的婚姻会因为一盒肝病药而有如此大的转折,而不是因为其他。也许有,我和梅蓝都曾意识到,比如我认为的我们爱情的死亡,但这个不适合讨论,更不适合留上字条。爱情是否死亡了,谁也不能肯定,因为它是否来过是否真的存在我们都无法言明。爱情与死亡,本来都是最为神秘的。
也许是因为恐惧,我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和苏秦泡在一起。我才不会管什么乙肝病毒,在我的眼里,苏秦唯一的身份只是我的朋友。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相约去吃傣妹火锅,我们看着许多来回穿梭的穿着肮脏白衣服不漂亮但年轻的女服务员聊了许多话题,比如小公务员的命运,生活的危机一般会何时来临以及应付之法,怀疑的力量,爱情与性的存在与否,情欲发泄的若干种方式,世界末日会何时来临等。我们大声朝对方喊话,我们的语气都被对方当成日本鬼子,我们否认对方的话语简明扼要并且无从辩驳,那就是“听不懂”。最后,我们争吵四个小时之后,只勉强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怀疑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于此我可以认为,聪明的苏秦已经想明白了梅蓝对他的看法,而且他还借着酒意颇带攻击意味地说,想不到乙肝也能成为你的劫难,你们本是同林鸟呐。
争辩中间,奉天给我来电话,不怀好意地在那头笑着说,听说,梅蓝又走了吧。我的事情总是传得比光速还快。我说,你有屁就放,老子在喝酒。他毫不掩饰轻蔑的语气说,梅蓝走了老子高兴,老子正在等你喝酒呢。我说,那你等着,一把这边这个鸟人斗趴下,我就杀过来。
和苏秦战斗完毕,我就赶往奉天那边,这是我在没有梅蓝的日子里唯一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奉天和他摆了一桌子的啤酒已经在急不可耐地等着我了。我又开始边和奉天喝酒边聊刚才的话题。很奇怪,我们口沫飞溅地争执不休,仍然只得出上述唯一一个类似的结论。奉天是个律师,但他只是一个和李鸿章一样有小智小才善用狡狯手段的不学无术的家伙。跟他喝酒,我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只要我愿意,从来都是我喝醉。我曾直接跟奉天说过,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只要我愿意喝多,他就保证能让我喝多。
这个冬天的凌晨,我侧躺在出租车里,朦胧中意识到奉天在我的身边,我让他赶快滚,他却说怎么也得尽一下最后的责任,和以前那次一样送我回家。以前,奉天曾经送我回家?车窗外,有初雪开始飘落,它们像羞涩的精灵,悄然无声地飞翔而下,倏地就藏匿不见了。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欲望,我想把头伸出窗外,一动不动地挺在雪中,我知道,我仍然会像那个在秋天操场上奔跑的少年一样激动。因为即使醉意迷蒙中,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梅蓝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我曾经给梅蓝的一封情书里写过,只要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属于谁,我都会很幸福。矫情少年的话语,才让我此刻麻木的心灵有所触动。我朦胧中开始觉得,其实爱情并没有远走,只是我不懂得感受它的方式罢了。
梅蓝走后,我决定辞去公务员的工作。没有了梅蓝,任何世俗的努力都毫无意义。我开始自诩地认为,原来我一切世俗的努力都是为了我和梅蓝的婚姻。现在,我完全可以买几箱方便面和矿泉水高码起来,然后闷在家里不知世事。我开始明白,其实,外在的一切,都和我们的婚姻没有关系。我开始收拾房间,打算整理出书房,把它作为我的起居间、写字间、思考间。我宁愿拥有一间屋子而不是一座房子。
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了几张视力表。它明显不是我的,也不是梅蓝的,那么它是谁的。谁曾经潜入我的家里把它放在我不多的书中间。就像那盒肝病药,它不是摆在我们可以视之遗落的客厅的显眼位置,却是那样堂而皇之地静静躺着储物间的药箱里。
许多个黄昏,我坐在昏黑的书房里努力去想,但没有任何头绪。模糊的印象里,经奉天的提醒,我依稀记得好像是有一次在我酒醉之后他送我回家。那天他好像背着一个包。我已经想不起来,他是把我扔在沙发上,一个人在房间里溜达了几圈,看了会电视而且自己烧水泡了杯茶,还是直接在门口就折身而回。
乙肝药盒是不是奉天的。以前在一个傍晚,我给奉天电话,约他出来喝酒,他却说他正在整理资料,要告某家医院。我问及原因,他说下午去某家医院看病,一个左眼快要瞎了的医生信誓旦旦地说没事,他满心幸福地回家静养,痛苦感却越来越强,他便去另外一家医院,医生却说再来晚就有失明危险了。他觉得那个瞎子医生差点履行侩子手的职责残害了他,他在电话里发誓说要告倒那家医院。
奉天到医院看什么病,还有,我知道,他的视力一直是不好的。就在快恍然大悟的时候,我猛然惊醒了。我觉得,梅蓝在千里之外,但她的魂魄似乎已经附到我的身上了。我看着黑暗中似有万千生物蠢蠢欲动的房间,我看到它们都睁着斗大的眼睛在敌视着我。我抱着头,撕心裂肺地喊叫起来。我冲了出去,现在,我必须找个人同往最热闹的大排档上喝酒,那样,我会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