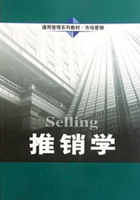李玫再次出现在白乐天面前已是第二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她敲开门,在白乐天复杂的神情中慢慢走进屋内,自然而满怀眷念的样子仿佛她刚出了趟远门历尽艰险终于平安回到家一样。她看上去变化不大,只是头发显得更加稀疏地紧贴在头上,或许因为天热的缘故,她的嘴唇显得更薄,而且线条更加分明。一袭碎花白绿相间的连衣裙使她的步伐轻盈、飘忽,却又给人她疲累得找不着步调的感觉。白乐天注意到,在她的左臂袖口上方,有一块镶嵌上去的黑布。
李玫轻车熟路地洗嗽完毕之后,嘴角露出轻浅的笑意,以一种十足的流浪汉口吻对白乐天说,你还愿意收留我吗?
白乐天随她的视线向整个房间扫视了一遍,摊开双手,既欢迎又故意无奈地说,你看,这里的一切除掉了脏乱,都没有什么变化。
李玫冲上去给了白乐天一个结实却并不热情洋溢的吻,说,那现在,我饿了。
方法已经回乡下老家双抢了,但白乐天知道,那是方法信手拈来专为糊弄他一人的托辞。多年来,六月末开始的暑假,作为装修的高峰期,方法都一直与白乐天一起顶着炎炎烈日奔波在宋城的大街小巷。这次方法随便编造个理由回去的原因只是带了小夭一起,却又不想白乐天也回去。用方法自己的话说,爱情不是一个男人生活的全部,所以他曾洋洋自得以高人一等的语气直言不讳地教导白乐天说,男人,跟哪个女人结婚都是无所谓的。他还不容辩驳地认为,遴选结婚对象会使婚姻无可挽回地成为一场交易,那本该是一件无比纯粹的事情,说白点,就是情欲的宣泄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也绝不会有道德谴责的力量在作祟。白乐天不知道方法的这席话是否原封不动地对小夭讲过,或者只是他们喝酒中间以一种迷蒙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看待世界的信口开河,白乐天更无从想象,小夭听见之后的反应。
但至少,白乐天承认这话也并非全无道理。在小夭恋爱的迷惘期,她还曾经差点上了他的床,如果白乐天不是白乐天,上床必成事实,而许多男人都不是白乐天,因此可以不那么露骨地说,小夭对结婚对象是经过遴选的,只是白乐天不明白,上床对小夭而言,是考察方式还是决定方式。但不管怎样,纯粹总不见得是坏事。除此以外,白乐天想不通的还有两点。一是方法为什么不愿他出现在结婚的现场,如果是因他了解小夭的底细,这至少说明这个男人内心里仍然存有不同于口表的对婚姻的看法。矛盾总是无处不在,又显得那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若真如方法所言,为什么他与李玫更加纯粹的结合却引来方法不留情面的反对。很多事情,不仅非三言两语所能述清,即使想理清头绪,都得假以时日,当事人的日趋成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切期待在他人心中留下困惑的信口开河者再次信口开河。
这天晚饭时,白乐天看着李玫狼吞虎咽的样子,暗自思忖,无论以后自己与这个女人走到何种地步,眼下有两个问题绝不该问。她为什么留的是解放前就已摧毁的地址,又因何远走半载之余杳无音信。白乐天又若有所思地看了那块黑布几眼。
当两人又莫名其妙地重归宁静生活时,在每个夜晚白乐天下班回来,李玫忙完所有家务,一起看电视时,李玫总会不经意提及白乐天的家庭。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李玫在一天夜里两人酣畅淋漓之尾,盛情邀请白乐天父亲来城里做客,白乐天略一沉思,答应了。
白乐天父亲在城里住了三天,就回乡下了。他此行值得一提的只有一件事,给了他认可的未来儿媳妇六千元的见面礼。老人颤颤巍巍地抖动着嘴唇,带着恳求意味地解释说,这些钱他知道确实太少,但也是自己从地里一分一分刨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钱,没要白乐天资助一分。白乐天是个纯朴的孩子,白家虽然穷,但是一个纯朴、正派的人家。待两人亲事定下来,他自然还有更多表示。
如果说此前白乐天尚有两人中某一人是过客的想法,那么现在因为父亲的来访,他就无可选择地把李玫看成自己实质意义上的妻子了。事后方法曾对此做过一番精辟的评析,人们对自己终生幸福的考量大多数情况并非源自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相干的人插入其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对于插入者无足轻重,却经常被当事人放大地臆想其中的联系。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情形将很多人推向了麻木、不知所措甚至凄惨的边缘之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这种认识和情绪,让白乐天最终会以那种方式去寻找李玫。这类说法看似显得牵强,却多么符合人类的心理和这个世界的真相。
而一旦从心理层面将李玫视为自己未来的妻子,白乐天就无从选择地要求自己给李玫的每一个行为都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当时间推移至这年深秋的一个黄昏,两人静静坐在三楼阳台上,在白乐天充满憧憬地畅想他认为势必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而李玫始终一言不发,且并不掩饰自己深锁的眉头时,白乐天终于勇敢地提出了那个令他困惑已久的问题。
为什么,他使劲抿了几次嘴,想吞咽掉语气中无法消除的怯弱,你曾经给我的地址如今只是一片废墟。他并不想丝毫为难身边的这个女人,他自认为自己提问的方式已经有意忽略掉许多东西,至少最重要的——时间,解放前就已消失——他都丝毫不提及,而且李玫的任何一种回答方式,哪怕只是片言只语,甚至只是一声轻叹或“哦”表示她已经听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切就过去了,他就有义务也有能力把这一切相关的疑问、困惑、甚至是怀疑都从内心里连根拔除。直接说,男人有时候和女人一样,不仅需要解释,同样需要欺骗。无论他邀请李玫前来宋城的动机多么纯粹——和一个陌生女人共同寻求刺激,如果她愿意的话,原因多么浅薄——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和她第一次见面时他最想干的与现在想法的极其矛盾之处,还有世俗意义上的他对这个女人了解多少——他完全可以认为,现在自己正在补救性地了解她,这一切的彷徨、犹疑与拷问都完全可以置之度外,毕竟,现在他将她当作未来的妻子。至于,从开始到现在,这种立场的转变有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有无什么玄妙,他一时尚不能理清头绪,也许用一句从古至今永不过时的流行语来解释就最贴切不过了——人总是会被爱情冲昏头脑的。
橙黄的阳光梦幻一般地照着街道上的行人、对面房屋、窗户——玻璃上折射出千万个太阳的影子,那里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还有白乐天面前锈迹斑驳的栏杆以及李玫的手上。李玫的手像两束紧缠一起的橙黄的透明胶。有那么一瞬,白乐天仿佛觉得这样的场景自己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正当他不知所以极力在脑海里搜寻的时候,突然他又灵光一现,对似乎早已经历过的将要发生的场景感到非常的恐惧。
李玫的脸在黄昏的阳光下苍白无比,头发也像紧密缠绕的细铁丝一样覆盖在头上,两片嘴唇似乎只剩下两条并不鲜红的线条。她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喃喃自语地说,我一直在流浪,我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安定下来。那个地方是我的故乡,但我却好像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另一个故乡。
白乐天一等李玫说完,就急不可耐地站起来——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结束了,也理应就此结束。他拉起李玫的手准备一起进屋去,不再暴露于天光之下,黄昏的阳光不仅让人觉得病恹恹的,而且还像是一副让人头晕目眩的迷药,这种不真实的阳光下诞生的所有情绪都是虚幻而虚伪的。不再暴露于天光之下那么一切就不必再如此大费周折地剖露心扉。对夫妻而言,无此必要,甚至对生活也不见得是好事。
李玫却长时间盯视着某一处虚空,毫无表情地说,前阵子,我妈死了。白乐天并没有太多惊讶,他略表同情地捏了捏她的手,安静地等待她继续倾诉,她却又什么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