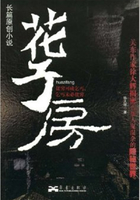楚红仰头看见斜上方的烟筒里喷出那股黑烟后,她探身够了一把,觉得眼前一黑,便啥也不知道了。等她清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身边坐着她的小姑子班娜。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时英钟发出嘀哒的声响。班娜的眼睛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隙,她盯着窗外,身体木雕般地摆放在椅子上。如果不是楚红的手触到她的胳膊,她还不会转过身来。
班娜转身的动作很缓慢,像是被人轻轻地挪移着。等她的眼睛由楚红的大腿漫过她的腹部她的胸前定格在她的脸上后,才僵硬地点点头,说嫂子,你醒了。她的声音很小,听起来倒是很清楚,有点像重体海棉,看着的感觉是棉软的,用手摁起来又很硬实。
楚红抬起手来,想去拉班娜的手。见班娜没有及时呼应,便任由手臂自由地垂落到床下去了。她感觉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她没有力气去做哪怕一会儿的坚持,更没能力去重复同一个动作。她的眼皮如同两块磁铁不同的极,在相互地吸引着,使闭上眼睛成为一种需要和愿望,也成了她区别现实与梦境的标准。她到现在也拒绝承认她丈夫班国义逝去的事实,她认为那应该就是一个恶梦,只不过这个梦比以往的梦做的时间长些,醒后记得清楚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