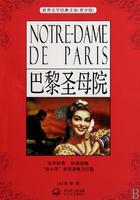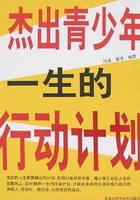公路段有两台轿车和一台面包车。对于这三台车,陈一平是这样跟李立交待的。那台奥迪V6,只供刘书记和他专用;那台桑塔纳,做为中层以上干部办公时用车;那台面包车,做为中层以下人员办公时用车。刘天栋清楚地记得,自从去年春天接回这台奥迪以来,他这个书记仅坐过五次。其中有四次是和陈平一起坐的,只有送他儿子去北京上学,单独使用过一次。那台桑塔纳,最近这半年来,被高美娜频繁地使用着,几乎成了她的专用车。同样是中层以上干部,包括老齐和老邱两个副段长,有事用车时,也得先看看高美娜今天用还是不用。更多的时候,是别人根本就看不到这台车停在院子里。这样一来,那台面包车竟成了中层以上干部的机动用车了,中层以下人员出去办事,不管事情多急多重,也只能骑自己的自行车了。
刘天栋看得出来,开桑塔纳的司机小王很愿意和高美娜出去办事。这并不单单是因为高美娜漂亮。当然了,漂亮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对于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身边坐着一个比自己还年轻,身上飘散着香水味的美女,总比坐着个身上飘散着烟味或汗味的男人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和高美娜一起出门很实际,在公路段机关这个大院里,高美娜是谁,大伙都心知肚明,接近高美娜,就等于接近了段长。
不过高美娜对刘天栋还是满客气的,每次见到他,总是书记长书记短的问候。今年五一节,高美娜去北京旅游,还特意去看刘天栋的儿子,领着他儿子在北京玩了两天,临走时还给他儿子扔下五千块钱。就是因为这五千钱,刘天栋跟陈一平之间闹得很不愉快。高美娜还没从北京回来,刘天栋的儿子就打电话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刘天栋把儿子大骂一通,儿子委屈地说,不是你让我高姨给我捎来的吗?刘天栋说你这大学是怎么念的,这点思考都没有,如果我给你捎钱,五一前我给你打电话时能不告诉你吗?儿子听后问咋办?刘天栋说这钱你不能花,先找个地方存起来,等到暑假回来,你给我一分不少地带回来。
刘天栋和儿子通完电话,就拨高美娜的手机。他问高美娜这五千块钱是咋回事?高美娜先是避而不答,一直在夸奖他儿子如何地懂事,说他们玩得如何地尽兴。最后刘天栋急了,说明天他就从家里拿五千块钱,送到财务科去。高美娜听后,吱唔了几声,这才说是陈段长让她给的,有什么话你明天跟陈段长说去吧。
刘天栋没能等到明天,他当天晚上就拨通陈一平家的电话。陈一平好像是睡下了,说话时还迷迷糊糊的。他说刘哥,你半夜三更的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点破事?刘天栋说是啊。陈一平突然改变口气,他说刘书记,你是不是有点不尽人情了,你要是觉着这钱有问题,明天可以把钱交到纪检委去。陈一平说完,拍地一下把电话挂了。这之后好几天,陈一平见到刘天栋都爱搭不理的,整得刘天栋也不敢再提这事了。这五千块钱,至今还锁在他办公室的铁厨子里。
高美娜的车走后,刘天栋匆匆地返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他拨通了办公室的电话,让李立给他准备一辆车。李立问他要车干啥?刘天栋说他要去医院看病。李立表现出很关切的口气,问他怎么了?哪不舒服?刘天栋说没什么大事,只想着去检查一下。李立说那台奥迪让段长开着去省城办事了,昨天就走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呢。那台桑塔纳让高科长带着去银行提款了,啥时候回来说不准。现在家里只有面包车,你要用,就坐面包车去吧。刘天栋听后只“哦”了一声,他没说用还是不用,就把电话挂了。
刘天栋是骑自行车去医院的。他来到挂号台的一号窗口前,这里的人很多,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十来个人。他看一眼二号和三号窗口,每个窗口前只有两三个人,他想去二号窗口。其实从一号窗口到二号窗口,只是右腿向右跨一步的事。他刚刚抬起右腿,又收回来了。他想排在他前面的几个人为什么不动呢?他们不动自己为啥要动?他们不着急,自己也不着急。他一边用手理了理头发,一边跟着前面的人缓缓地向前蠕动着。
终于移到窗口前,刘天栋拿出两块钱递进去。挂号的小丫头问他叫什么名字?挂哪科?刘天栋说出自己的名字,并告诉那个小丫头,说挂哪科你随便吧。那个小丫头抬头瞅了他一眼,就给他挂了内科门诊。刘天栋拿着挂号单往内科走,他边走边寻思,这个小丫蛋,挺善解人意的,他怎么知道我的毛病出在心里?
到了内科,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在坐诊。刘天栋坐下时,那个女大夫正低着头看一张化验单。她听到有人坐到她跟前,便问,你咋的了?刘天栋听了女大夫的问话,他的火气腾地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在心里说,你还他妈的不如一个小丫头懂事,我要是知道自己咋的了,我来找你?女大夫见他没回答,就抬起头,瞅了刘天栋一眼,马上换了个问法,问他有啥症状?刘天栋说难受,心烦。女大夫问他哪儿难受?刘天栋说浑身上下没有好受的地方。女大夫说你八成是感冒了,这茬子感冒大都是这个症状,浑身难受。人身上一难受,心情肯定不好,没事的,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吃了就好了。说着,女大夫刷刷地开完方子,递给了刘天栋。
刘天栋的屁股刚一离开橙子,就觉着屁股底下就有人钻了进去。他回头瞪了那人一眼,那人正一心一意地瞅着大夫,再瞪一眼,那人还是没看着。没办法,他只好拿着方子走出诊室。他边走边想,这是那门子医生,看的那门子病,也没摸摸,也没听听,甚至都没正眼瞅一下,就凭我说的难受两个字,就给我定个感冒,这多亏是个大夫,这要是法官,这得产生多少冤假错案。
刘天栋越想越来气,就撕了药方。其实他以前也不欣赏西医,为此他多次和他老婆产生过争议。他认为西医就是不如中医,中医除了药不好吃点,剩下哪点都比西医强。人家不用借助啥家伙式,单凭一只手,就能摸出你的毛病来,这才真叫有一手呢。而他老婆总是相信西医,她说中医下药和厨师做菜一样,根据自己的口味下料,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抓,好像只是个大概数,不如西医准确。
刘天栋回到挂号处时,他心里还在核计,自己屁大个工夫就挂两次号,挂号的人会不会认为他有毛病啊?他走到一号窗口前,甚至还有过一瞬间的犹豫,想换个窗口,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不是因为有毛病才上这来的吗?来这里的人哪个没毛病?没毛病来这里干什么?这才理直气壮地又来到刚才的那个窗口上。
刘天栋再次递进两元钱,那个小丫头问他挂哪科?神情和刚才一般无二。刘天栋说这次挂中医吧。那个小丫头接过钱去,又问他叫什么名字?这让刘天栋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这么屁大的工夫,那个刚才他还认为挺善解人意的小丫头,竟把他忘的一干二净了,一点印象都没了。刘天栋只好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那个小丫头连艮都没打一下,就从里边又递出一张挂号单来。刘天栋拿了挂号单,他嘴里小声地叨咕着,这叫什么地方?什么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简直是他妈的一切为了人民币。
刘天栋气冲冲地推开中医诊室的门,坐诊的是一个比刚才那个西医看起来岁数还大的女大夫。刘天栋想这所医院怎么了,坐诊的咋都是一些老太太呢?刘天栋想退出来,再上别的诊室看看,可这个老太太还挺热情,主动跟他搭话了,说你是看病吗?刘天栋在心里说,不看病我上这干啥?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老太太说,来,坐吧。这让刘天栋觉着再走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便坐了过去。老太太没问他咋的了,而是把桌上用来号脉的小白枕头往前推了推,示意他把腕子放上。他照做了,老太太开始把脉,但老太太的眼睛却注视着墙角的镜子,那神情和放射科那些大夫似的,好像她能从这面镜子里透视到刘天栋的五脏六腑,能看到他的毛病所在。
大约五六分钟,老太太把手抬起来,用下巴和眼睛示意他换另一只手。老太太的眼睛还是盯着墙角的镜子。这时,刘天栋的眼睛也跟着不由自主地转向了镜子。他看着镜子中的老太太慈善的眉目,平和的神态,感觉很亲近。他几次想和她说说话,但一时又找不到可说的话题。又过了五六分钟,老太太把手抬起来,转过头,问刘天栋最近没感冒吧?刘天栋摇了摇头。老太太说你最明显的症状是啥?刘天栋说,疲乏,混身难受。老太太点点头,说你去化验一下钙吧,也许就是缺钙。说完给刘天栋开份化验单,推到刘天栋的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