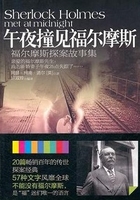刘玉香的家在村子的东头,她要去的那片地在村子的西北边,穿越整个庄子是她的必经之路。
她刚走过三个门口,见老五媳妇正哄着她三岁的儿子在门前玩。
老五媳妇见到她,老远就打招呼,说三嫂子,天这么泞,你干啥去?刘玉香往跟前走了几步,她边走边把自己的打算说了。老五媳妇说,我们家地里的苞米也倒了,我还没去扶呢。跟前拖着这么个小崽子,啥活计也干不成。刘玉香说是啊,女人都从这个时候过来的,我们小东子这么大时,我也是啥活都干不成,连做饭都费劲,天天巴眼望眼地盼着孩子能睡觉,可孩子大瞪着眼睛就是不睡,这一天愁得我是没着没落的。老五媳妇说,我这一天也是这样,家里盆朝天碗朝地的,都顾不得收拾。这不刚吃完饭,孩子非得要出来玩,这阵子孩子从外头玩野了,扒开两个眼就想往外跑,屋子里一会都不呆了。
刘玉香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脑瓜,她说孩子淘点不是啥坏事,淘小子,出好的,淘丫头,出巧的。我们家小东子打小就淘,那时候你还没过门,你是不知道呀,淘得没边海岸的。没有他上不去的地方,也没有他祸害不到的东西。你们这个好歹还在地下玩呢,我们小东子这么大时候,就好上高处玩,哪高他往哪去。有一年冬天,我看他在炕上玩得好好的,我寻思就着这个空儿上趟厕所。刚到房后,一泡尿还没等尿完,就听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我提了起裤子就往回跑,刚转过房檐头,就见孩子在台阶上躺着呢。我上厕所前,还特意看了一眼,见窗户关着呢,不知道他咋推开的,也不知道他咋爬出去的。我跑到跟前一看,见孩子脑袋上摔出鸡蛋那么大一个包来。我抱起孩子来就哭了,比孩子哭得还厉害。一直哭了好几天,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只要是看着孩子脑袋上的疙瘩,我这眼泪就花花的,一直哭到孩子的包消下去。从打那儿之后,我大白天也在屋里放个尿桶,再也不出屋了。我是天天提心掉胆地过日子,也就是这几年孩子大点了,懂事了,我才算是省心了。
老五媳妇望着她儿子,叹了口气,说这当妈的真是不易,生孩子时差点折腾死;拉巴孩子累个臭死;大一点还得往死地操心;长大了若是有出息了,还算行,要是不争气,当妈的还得跟着挨骂。你说说咱们女人,这还有个好吗?老五还打算让我以后再生一个呢,我算是看透了,再生一个就得活活把我累死。
刘玉香把铁锹放下来,戳在胸前,两只手扶着铁锹把,身子往前依靠着,脸凑到老五媳妇跟前,她说我可警告你,这话可不能当着你婆婆面说,你拉巴这一个孩子就觉着死累活的了,你婆婆拉巴五个孩子咋过来的?你老爷们啥活都会干,啥活都替你干了,你还觉着委曲。你婆婆打四十多岁就守寡,一个人拉扯着他们哥五个,要照你这么说,早就累死几百回了,人家不也把五个孩子拽大了。这话要是让你婆婆听着,你纯属是找挨骂那伙的。
老五媳妇呵呵地笑起来,说她听不着,别说咱们这么说话,就是扒在她耳朵上喊,她都听不到。我婆婆现在可聋了呢,今天早上我招呼她吃饭,连喊了三遍,她都没听着,就坐在那儿看着她孙子发呆。最后我推了她一把,她才转过身来。你说说她都这样了,还挺好管闲事的,孩子衣服脏一点都不行,我不洗她还要给洗去呢。
刘玉香说这就叫老不舍心,少不舍力。你婆婆这一辈子可真是不容易,那累受的,用马车去装也得装几马车。她现在跟着你,还真算是对了。你心眼好,不亏待她。那么大岁数的人了,让她享几年福吧。人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你对老人的好,神灵都给你记着呢,到时候会给你回报的。
老五媳妇认真地点着头,她说三嫂子,你说这话我信,我当闺女时,我妈也说过这话。她说这世界上没有啥菩萨,每个家的老人就是这个家的活菩萨。我妈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在家敬父母,不用远烧香”。这一点我妈做得就好,她对我奶奶就像对待我姥姥似的,打我记事后,我就没看过她们娘俩红过脸。你看现在我妈得好报了,我那两个嫂子心眼都好,别人家的媳妇打老骂少的,我们家的媳妇天天眉眼嬉笑的。你看我不和别人家的闺女那样,没事老往娘家跑,我嫂子对我妈比我这个闺女还好,我没啥不放心的。
刘玉香抬起左手,在老五媳妇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这话算让你说着了。咱们女人出了门子,哪儿是家啊?婆家才是真正的家。谁是妈呀?婆婆就是亲妈。你没听人家说吗?出门子的女儿,那是泼出去的水。我从被泼到他们老葛家来,就当自己是老葛家的人了。谁知道你们年青人是咋想的,反正我是没打算挪窝,我就是一块木头,烂也得烂在老葛家这儿。
老五媳妇刚笑几声,便转身往院里跑去。她去撵她儿子,这个小家伙不知啥时候跑到院里去了,正拿着一根小木棍,跟他家的大黄狗比划呢。
刘玉香没再等老五媳妇出来,她向院里打个招呼,说我走了,你好好哄孩子吧,别让他祸害狗,那东西酸脸子,别咬着就好了。
刘玉香走到村子当中,看到葛富两口子在当院抓猪。葛富家的大门是那种钢筋焊成的栅栏门,关着大门也能看到院里的一切。
葛富跟在猪的身后,围着院子一圈圈地撵着,他老婆王红从相反方向拦截。眼看着两个人把猪夹在当中了,葛富往前一扑,猪从王红的裤裆下窜过去了。葛富开始埋怨王红,说你他妈的真笨,你就不会夹住它。王红站在那儿拍着裤子上的泥土,说它身上溜滑的,我能夹住吗?两个人又重新开始,再围着院子一圈圈地撵起来。
刘玉香在门口看了一会,正好王红跑到门口的位置上,刘玉香叫住王红,说你们俩口子这是干啥呢?锻跑步呢?是不是打算过几天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啊?
王红停下来,说猪有点毛病,都两天多没吃食了,抓着给它打一针。
刘玉香说这猪本来就有毛病了,大热的天,你们俩这么撵它,一会累死了,还打个屁针啊?
葛富这时也撵到大门口的位置,他也停下来,拍着手上的泥土说,我以为它两天没吃食,早就跑不动了。没想到它还挺有劲,看样子没啥大毛病,要不就先别打针了,等跑不动时再说吧?
葛富的话应该是说给王红听的,可没等王红有反应,刘玉香先说话了。她说那可不行,等猪跑不动时,那就是快死了,打不打针还有啥用处?你笨蛋不说你笨蛋的,还怪这个怪那个呢?我活四十多岁了,就没看过像你这么抓猪的。
葛富瞅了刘玉香一眼,没吱声,气呼呼地蹲下,从兜里掏出烟来。
王红赶紧说,那咋抓呀?三嫂子你快说说。我们家的猪从来没闹过毛病,我们也没抓过。
刘玉香说你们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走?你没看过别人家咋抓猪吗?
王红摇头,说没看过。
刘玉香又回头问葛富,说她没看过,你也没看过?
葛富想了想,说我看过杀猪匠抓猪,人家是先拿棍子打脑袋,把猪打懵了再抓,咱们咋也不能用这个法子吧?
刘玉香把铁锹戳在大门边上,她说这叫啥法子?这个法子傻子都能想出来。那不和医生给罗锅子治病,用两块木板夹一样吗?人都夹死了,把罗锅治好了还有啥用途?
王红把大门打开,拉住刘玉香,说三嫂子,你快帮我们想个法子吧。要是能救活它,过年杀了肉,我送你一条大腿。
刘玉香嘻嘻地笑起来,说我要你的大腿干啥?你的大腿还是留着夹猪吧。两条腿都夹不住一头猪,剩一条腿更白扯了。
葛富没听明白刘玉香话里的意思,他还跟着附和,说刚才就怨王红,她要是机灵点,就夹住了。
王红过去在葛富的背上打一巴掌,说这个潮B老爷们,三嫂子骂你呢,你还跟着起哄。
葛富听后,他吧嗒两下嘴,小声地嘟囔着,操,你不笨你抓啊。
刘玉香冲着葛富说,你还别不服气,照你这样的抓法,除非把猪撵死,它要是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抓着,不信你就试试。
刘玉香说着也到葛富的背上拍了一巴掌,她说你还在这儿傻愣着干啥?你去给我找根绳子来,要长一点的。说完又转身对王红说,你去给我找一根葵花杆子,也要长一点的。
打发走葛富两口子,刘玉香把大门又重新插上。
葛富从厢房找来一根绳子,他打老远就扔过来,扔到刘玉香的跟前。他站在当院的一根杏树下,老远地看着。
王红从后院扯来一根葵花杆子,递到刘玉香的手上。刘玉香把绳子系成一个活套,用葵花杆子挑起来,形状跟蒙古人用的套马杆子着不多。
刘玉香举着葵花杆子对葛富说,你过来,一个手拿着绳子,一个手拿着杆子,等猪跑过来了,你就套它,一套一个准,我就不信还抓不住这么个小猪羔子。
葛富走过来,接过葵花杆子,他说这个法子灵吗?别把猪勒死就崴了。
刘玉香瞅葛富一眼,说你当它和你那么笨呢,勒疼了,它就不跑了。说着她招呼王红,让王红从东边往西撵,她自己则去西边截着。
这招果然很灵,葛富一下子就把猪套住了。他扯着绳子问刘玉香,说三嫂子,咋办?刘玉香说往手里一点点地导绳子呗,这还用我教你,你真是比绳子那头的东西还笨。
葛富使劲的往怀里导绳子,猪拚命地向后用力。葛富心疼猪,怕把猪勒死,便跟头流星地往猪跟前跑。王红和刘玉香从猪后边包抄过来,这次王红挺机灵,她向前一扑,便扯住猪的一条后腿。这是一头当年的小猪,也就是一百多斤,王红直起腰,便把它的后腿拎起来了。这时刘玉香也赶到跟前,她拎住猪的另一条后腿。猪只剩下两条前腿着地,它不再往前用力,而是开始大声地嚎叫。它的嘴巴对着地面,每叫一声,都能吹起一股地面上的尘土来。
刘玉香告诉葛富快去拿针,葛富跑到屋门口的小墙边,把早就抽好药的大注射器拿过来。他一只手扯着猪的耳朵,朝着猪的脖子扎过去。那狠歹歹的样子,好像他跟这头猪有多大仇恨似的。葛富的这个举动,看得王红和刘玉香都笑起来。刘玉香说,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当护士的料,当瓦匠真是屈了你了。
给猪打完针,王红招呼刘玉香进屋洗把手,喝口水。刘玉香把手往裤子上抹了几下,说不用了,反正一会扶苞米时也得弄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