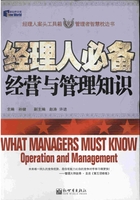每天吃过晚饭,同室的女伴一出去,我就半躺在床头拿着电话号码发呆。两种声音像幽灵一样在我脑海里交战,不打的声音始终占着上风。偶而也有打的声音占上风,甚至有一次拨通了号码,《童话》铃声悠扬地传来,接下来是那个熟悉的充满磁性的声音。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我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像小女孩那样沉不住气,我随便说了一句慌乱地挂了。他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也不会想到我在省城。我看着电话发呆,然后把自己的头很大幅度地摆动无数次,嘴里默默念叨着:不不不,我不要成为一个荡妇,我要做一个贤妻良母,我不要做一个荡妇……
来省城学习的时候,初中同学紫嫣把写着他电话号码的纸条拍在桌上说:去看看倪老师吧,他现在都是黄河大学的博导了,那时候对咱几个多好,代我问个好。
紫嫣当然不知道我的秘密。那个被她称作倪老师的人,我说不清是厌恶还是喜欢,也说不清是排斥还是吸引;我渴望听到他的消息,还会为他的消息或兴奋,或烦恼;我想接近他,又想远离他。
这个我生命中给过我最多折磨的男人,在心里我早就不叫他老师了,我叫他的名字,倪谭。我在心里骂过他无数次,他真是个泥潭,让我陷进去不能自拔。
紫嫣走后我曾经把那个纸条揉成团扔进垃圾篓,可没过多大会我又不顾垃圾篓里肮脏不堪,小心翼翼地把它拨拉出来,最后不光把号码存到手机里,还抄在笔记本上。
真不该要这个号码。我想,因为这个号码,让我六天里寝食不安。一点都不夸张,寝食不安。几天里,那棵冬眠了好久的苗子突然萌动了,它的疯长使我心起波浪,搅得我痛苦不堪。
我气急败坏地把笔记本扔出去好远,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泥潭吧,我不要陷入泥潭!然后打开电视,不停地翻台,却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最后又把遥控器撂到床头柜,双手抱头仰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没有风景,不时闪现的,却是他:棱角分明的国字脸,浓而高挑的眉毛,细长深邃的眼睛,山峰般耸立的鼻梁,两角上翘的嘴巴,平直方正的下巴。
我忽地坐起来,拾起笔记本,拨通了他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他很绅士的普通话,你好,哪位?
我没有叫他老师,淡淡地说,我是梦心怡,我在省城。
02
他说马上来见我。
我没有把见面安排在房间,我约他去宾馆对面的“浪漫”咖啡厅。在房间见面,我担心自己控制不住,会飞蛾扑火般主动投入他的泥潭。不用猜想,我确信,我刹那就会原形毕露,一副荡妇的嘴脸就会呈现在他面前。也许,他是喜欢荡妇的,他会很老练地迎合我;也许,他是不喜欢荡妇的,但他肯定抵不住我的火热,被动地任我摆布(他招架不住的狼狈模样肯定很可爱了?);也许,他会很理智(毕竟四十多岁,不是激情燃烧的年龄了),很优雅地扶我坐起来,然后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别冲动,你会后悔的。
想起他拍我的肩膀,我的肩上有一股热流涌过。二十年前,他的手轻轻地拍在一个十五六岁女孩肩上的时候,他不知道会给一个女孩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我无数次回忆起那个下午,那个炎热的夏季的下午——再有一个星期,我们即将毕业离校,教室里乱哄哄的,有些人心惶惶。我独自一人去他办公室,找跟他同室的数学老师问问题(那时候的我很少找老师问问题)。门半掩着,我打过报告之后,他说进来吧。我推开门,一下子愣住了:数学老师不在,他赤着上身坐在办公桌前看什么书(记不清是什么书了,好像是一本小说吧)。
我本来想走,他扭头看见是我,温和地笑笑,说,梦心怡啊,进来吧。我乖乖地进屋了,还神使鬼差地顺手把门给掩上了。后来我反复想,那天我之所以把门掩上,大概就是不想让人看到他赤裸上身的不雅。十五六岁的我对男性的身体已经有了些抵触,或是向往。
初中三年,因为我的普通和庸常,加之学习成绩平平,我清楚自己在众多老师眼中微不足道。作为班主任的倪谭,也没有怎么关注过我。可那天下午,他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我站在离他两三米远的地方闻见了他浓浓的酒味),竟然把我让到办公室,做出关心的样子。
他站起来,很慈祥地说:怎么样,复习得差不多了吧?你的志愿报得实际,考上高中应该没问题。
接下来,他看到了我的窘迫(因为他赤裸的上身),看到了我不敢看他的怯怯的眼神,自己往自己身上一看,大惊失色,慌乱地穿上白衬衣,尴尬地说,忘了,喝点酒,忘了没穿衣服。
我把头低下来,吃吃地笑了。他上半身的身体我是熟悉的。我无数次看过他穿着短裤、背心在篮球场上打球的英姿,洒脱的动作,高超的技术,高而壮实的身体,让众多学生羡慕不已,尤其是女生,把他当做异性偶像,甚至不亚于电影明星。在球场上,他出汗的时候,就会撩起背心擦汗,上身大部暴露出来。他的皮肤很白,肌肉很结实,看起来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胸前隆起的两块肌肉,有一种雄性美(雄性美是现在的评价,那时候看起来只是感觉很舒服)。但面对他全裸的上身,我还是有些惊慌。他穿上衬衣的时候,我有点失落。后来还想过为什么不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让他不至于发觉,可以多看看他的身体。
我平静下来回答他关于复习的问题时候,他走得离我很近,做出了一个令我出其不意的动作: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他手的温热,透过一层薄薄的针织面料,传递到我的身上。我感觉我的身子一颤,那股热流便在我全身涌动。
拍完我的肩膀,他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心跳:心怡啊,你很踏实,我很喜欢你。
那个动作,那句话,让我激动了很多日子,而且影响了我二十多年。我曾经反复揣度过他说喜欢我的真实含义:是酒后吐真言,真喜欢?是酒后胡言乱语,说过去就算?还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喜欢,为了考前鼓励我?但我确定,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一种让人心动的东西在涌动,我能感觉到那是一个男人对异性的表达。那眼神,现在回忆起来仍然令我温暖。
这句话,让我在毕业前后的几天里发疯般地想他。从此,一棵种子在我心地埋下。
想起一个夏天,当浑浊的雨铺天盖地下的时候,同学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他与我们一块上自习。校门口的大柳树,疯狂地摇摆,黄色的雨在校园里连成一片,天色忽明忽暗,偶尔有轰鸣的雷声,我们共享着教室里的那份宁静与温馨。
你个泥潭,随便的一句话,让我折磨了二十多年。我回忆着往事,坐在咖啡厅里等着那个想起来就会心痛的人。
如今,年过不惑的倪谭,会变老、变丑吗?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感兴趣吗?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和他对我的态度,眼光一直盯着进口,心里竟有些迫不及待。
03
他跨入咖啡厅的那一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竟然穿着红色的夹克,火一样的红夹克。那一团红色飘进门的时候,我一时没有反映过来。确认是他之后,我站了起来,向他摆摆手,喊了一声,在这。
他毅然那么挺拔,体型几乎没变;头发梳得看似很随意,却很有造型;最大的变化在脸上,没有以前光滑、水灵了,似乎有了一些细密的皱纹,尤其明显的,是成熟的气质。感觉,他变得更加有魅力了。
我不由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部与小腹,它们确实太不争气,被儿子残酷吸过近两年的乳房已经没了模样,松软而下垂,尽管托收的胸罩很紧,它们却还是挺不起来;小腹却是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任我天天做五十个仰卧起坐,照样下不去,即使有收腹内裤的束缚,小腹还是有些跃跃欲试往上鼓。三十多岁的女人,真是豆腐渣了。这一刻,自卑不觉汹涌而至,叫我突然有些失落。他会嫌弃我吗?
他笑着向我走来。我真想跑过去扑在他怀里,久久地用抱着他不松开。可我只是想了想,站在那里一动没动。身体里蛰伏的那个苗子,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说,咋来的?够快的。
开车,这会高峰过了,不堵车很快。他说。他看了看大厅,还算清静,他却说,去包间吧,大厅有点乱。
他一边说着跟在服务员后边走向包间,我没客套,乖乖地跟在他身后。那一刻,我想,他愿意与我独处在封闭的空间里,或暧昧,或浪漫,我喜欢。那棵苗子又开始疯长,不觉间,自卑也远遁而去,我浑身有些燥热。
我们相对而坐,中间是一个长方的茶几,上边摆着一个投币星座测算仪,他顺手拿起那个测算仪,一边投进一个硬币,一边说,记得你的生日是12月23日,应该是摩羯座吧,我看看,摩羯座女性,个性保守,比较固执,对再琐碎的事也不会疏忽大意,心地诚实善良……你对异性的好奇心远远超出常人,但内心冷静,无法尝试惯常的恋爱游戏……
我有点感动,他竟然记得我的生日。我打断他,说,一点都不准,我才不会对异性有好奇心呢。
他很绅士地笑笑,问,喝什么,咖啡,还是红茶?晚上了,喝咖啡容易睡不着,我建议喝红茶,这里有一款清秀佳人,感觉挺适合你的。
我点点头,他按下服务灯,又问,吃点啥?晚饭没吃吧?要不给你点份牛排?我喜欢吃他们这的牛肉面,我要碗面。
我说,在宾馆吃过了,我们下课就吃饭,你点吃的吧,我不要了。
他说你不要主食就点份水果拼盘吧。
服务员敲门进来,他看了一眼服务员,说,丫头你刚大学毕业吧?我看挺成熟的。
服务员抿着嘴笑,笑得很雅致,似乎有一些遗憾,说,我有那么成熟吗?我才二十岁,才大三。嘴上虽这么说,却有一丝得意从脸上掠过。
我有点酸溜溜的,当着我的面还讨好小女人,真是色狼本色,秉性难改。曾经,听说过他的一些绯闻,特别是到了省城,他离婚后找了个小他十多岁的学生,当时我对他的看法大打折扣,甚至下决心不再理他。
点完单服务员出去,我说,你真会说话,见了小女人说成熟,见了老女人就该说年轻了吧,娶了个小师母,还这么喜欢四处播撒爱情啊。
他很放肆地大笑起来,说,你这是讨伐我啊?看来我在你心中的形象很不咋样啊。
我心里突然一动,感觉他是那么的优雅与潇洒。那一刻,他真是魅力四射。
二十年前那个傍晚,考试回来的第二天,我去他从学校到家的必经之路的一个破窑里等他,从晚霞绚烂等到夜幕降临。傍晚的清风梳弄着庄稼的秀发,我静静地站在虫鸣如琴的破窑里,从窑门注视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当他的影子出现在我的视野的时候,我却没敢出来。看着他悠闲地骑着车,哼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过去,我却没有勇气跟他说话。我不知道给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找他是为了什么。我悄悄地跟在他后边,用心地听着他哼抒情的小曲,听着他自行车链哗哗的响声,听着庄稼在夜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懵懂的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在冲撞。我现在知道那是青春期的躁动所致。他不经意间在我心里丢下的这粒种子,再次膨胀地疯长,蛮横地向我展示沉默多年的生命力。它在黑暗中蛰伏,即使我有意遏制它,不给它阳光、空气和水,它依然存在,等待着时机破土而出。
敲门声刚落,服务员就拿着红茶进来,她要给我们倒茶,他接过茶壶,说,不麻烦你了,我自己来。他给我倒上茶,那茶颜色红中泛黄,看起来温润而厚重。
这清秀佳人特别适合你,柔情而恬淡,香甜而味醇。他说,这么多年不见,你更加有风韵了。
我都胖得没样了,别忽悠俺了,倪老师。我说着,抛了一个媚眼给他,然后站起来走出房间。
04
我在洗手间的水池前把冷水不住地往脸上撩。脸一直发热,是因为我的血液在沸腾吗?为什么见到他总是这么躁动?不见他的时候,想见他;见了他的时候,却又恐惧他。
应该说,高中三年我是努力的。因此,尽管那粒种子会时不时地在我心里萌动,但始终未成气候。我的努力最终白费,到底没有考上大学。我幸运地参加了父亲厂里的内招,成了一名工人,去了现在我所在的城市——洹滨。
临走,在一个下午我去母校找他。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外边白雪茫茫;他的办公室里却暖意浓浓。刚进屋,我的衣服上还保留着冰雪的痕迹——我特别喜欢闻那种冰冷的味道。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冬天的早晨出去,进到屋里坐在炕上取暖,我都会在她身边缠一会,她的衣服上有一种我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味道,触摸是冰冷的,那种彻骨的寒冷在温暖的炉火旁,有一种在我来说摄魂的香味。记不清那天何以跟他同室的数学老师不在,我和他围着一个圆形的绿铁皮煤球炉,烤着手,说着话。也记不清说了些什么,反正一直到很晚。最后,他掠走了我的初吻。
他看见我的时候,一脸的惊喜。他说,怎么是你?你还记得老师啊。
我木讷地站在他面前,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想来我当时的表情应该是茫然不知所措,或是尴尬不安?我说我没考上大学。他说我知道啊,想着你去复读了。我说我没复读,要去洹滨了。他说那也挺好的,能进城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