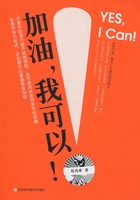陈曦走过来扶着我,皱了皱眉附耳轻语:“这个女人在这里呆的时间不短。”
我点点头,忍不住笑着调侃:“她看你的眼神挺幽怨的,你没什么感言想发表的么?”
“祝她早生贵子。”陈曦撇撇嘴,示意楼下的小林上来,“把她带到地牢审问,没审问点东西出来的话,你们也别回来了。”
“曦少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当初可是你说要……”女人还想尖叫几声,被我厉声打断:“闭嘴!”扬眸盯紧她,一步一步往前走去,“你在这里安心本分地待了这么长时间,却因为这一次失手而暴露不觉得可惜?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次,你有可能丢的是命,有些人,却只是损了一颗无关紧要的棋子而已。”抬手拍着她的肩膀,我转而柔声轻劝:“乖乖地配合,会少点痛苦,你和你的家人,大概都可以稍微平安一些。”
“大小姐!”她一直掩盖住真实神色的那抹惊慌无助蓦然滞住。
我把手收回,按住腰间的薄刃,轻勾起嘴角,淡声警告:“抗拒,从严。”
小林领悟地恭敬询问:“大小姐,需要用刑吗?”
挑挑眉,看了一圈神色各异的人,这之中,说不定就有那个背后的人,我无声点点头,挥手让他们带她下去。
女人总算回过几分神来,吓得连连摆手后退:“别!别!啊——”声音还在延续,人却已经被拖走了。
夜的寂静在女人被带下去后,彻底充斥了整个空间,大厅里是齐整的护卫队,二楼只有我和陈曦。
气氛变得竟比之前更加凝重,我咬着唇看了眼脸色越来越沉的老爹,斟酌了一下想开口说话,陈曦却突然伸手拍着我的脑袋笑了:“傻丫头,没事,去吃饭吧。”
老爹也在这时开口说话了,他看上去有些疲惫,脸上的那道伤疤都显出几分往常不曾有的倦意。
“陈曦,跟我来书房一趟。”
“老爹!不会是陈曦的!”我急声喊着,边大步往楼梯跑去,腰适时地被身后的人一把揽住,吊儿郎当的语声响在头顶:“傻啊你,老爷只是要和我商量点事情,你先去吃饭,等会过来一起讨论。”
他说着就顺势放开我,朝着老爹点点头。
“是,老爷。”
一顿饭,明明山珍海味,我也明明饿到眼睛泛花,但就是没有任何胃口。应该是热闹的一张桌子,现在只是安静地坐着我和箫言,尤其,箫言还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掉,且没有任何想要强调自己的存在感的人。
“不合胃口?”没有存在感的人突然主动开口说话,我愣了愣,摇摇头,拿着筷子戳着米饭,半偏了偏头问:“箫言叔叔,陈曦为什么会来我们家?”
我进来的时候,陈曦已经在了,而且常年只跟箫言混在一起,我甚至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父母亲人是谁。
“他是我在火车站捡的,”箫言无声地夹了块排骨放在我的碗里,回忆了一下继续说,“跟着一群人逃难来的益城,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他讲得很慢,眉宇间也只是偶尔有些淡淡的折痕,看不出任何情绪,却分明是有几分感怀的。
我轻嗯了声,抬手制止他下面的话,夹起排骨低头咬了一口,味道还是一样的可口,但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不舒服得很。
“你呢?”我把筷子放下,双手放在桌上,认真地问他,“你为什么会加进甄盟呢?”
箫言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勾了勾嘴角,原本面无表情的一张脸都跟着生动了不少,也许是他这样突来的柔和叫我心情也放松了些,脑袋也清明了,想了想,知道自己这话问得像是在质疑他的忠诚,我撑了撑额头,无力地放弃追问,转身朝身后的吴妈吩咐:“吴妈,我要吃爆炒虾仁!”
吃过饭后,还是没有见老爹他们出来,我在门外徘徊了许久,终于抬手敲门。
“进来吧。”老爹的声音听不出异样,我暗自吁了口气,知道他们至少没有吵起来,毕竟,即使知道那个女人绝对不可能是陈曦安排的,但是,甄家堡的仆佣的筛选,一向都是经过几道关卡的,箫言是最后的一关,而通常情况下,过了陈曦那关的,箫言如果忙碌了些,也会直接点头同意让人通过。
而那个女人,严格说起来,还是陈曦的疏忽的责任了。
“小竹,过来吧。”老爹把一叠东西放在桌上,抬手让我过去,“这两天,哪儿也不许去,把这些东西都背熟了。”
我还没会过意来,陈曦已经幸灾乐祸地在旁边煽风点火:“好几年没见你背书了,还真是挺怀念的。”
我白了他一眼,走过去接过那厚厚的一沓纸,低头翻了翻,眉心皱紧,不可置信地抬头瞪着老爹!
“为什么我要考检察官!”我知道自己在偏激,而且还一直朝着最极端的方向思考问题,可是!既然是那个叫崔洁的女人首先放弃了我,我难道连拒绝和她再有交集的权利都没有吗?!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算什么?!
“你必须考!”说到态度,老爹这次竟然比我还坚定固执,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甄家堡护了你十七年,不可能护你一辈子!她是你亲生母亲,她可以保护你!”
“你才是我爹!养了我这么久,想撇下就撇下,你问过我的意见没有!甄成功!”
往常,每次我连名带姓地叫他的名字,都会是我自己率先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为老爹的这个姓氏,配上什么都显得格外好笑,还记得当时他很是自得跟我介绍甄盟这个组织时,我趴在床上笑得乐不可支,一个劲儿地想着,甄盟甄盟,真萌呐!
可是,这一次,我连笑都笑不出来,试了几次,嘴角都是僵硬的,许久,却还是我我主动软下声来,第一次这么乖顺地说话:“老爹,我不想离开。但如果是你的要求,我至少会去考。”
陈曦深深地叹了口气,目光看向窗外庞大的夜色,没有接话,老爹则是转开眼看着桌上的相框,那里是我和他,箫言还有陈曦,唯一的一张合照。
这张照片的由来也有一个典故。
那是我满二十周岁时的礼物。
大清早老爹就带着一帮子的人敲锣打鼓地叫醒我,又安排了几个手巧的女人给我盘发穿衣,害我以为自己是要准备嫁人了,结果一到目的地,才发现是来拍艺术照的,而且这么一路声势浩大地来到影楼,差点让人家店长以为是来砸场子的!
我向来自诩自己长得还算能见人,于是果断拉着陈曦的袖子询问:“我们能换个庆祝方式么?”
陈曦笑地跟做贼似的欢乐:“也不是不行,只是老爷昨晚听人家说,女孩子的二十岁很重要,要把这份美好留念下来,不过……”他上下挑剔得看着我,咧嘴轻哼,“你这样子也实在和美好靠不上边了。”
……
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最终还是屈服地拍了一组写真,事后,卸好妆出来时,老爹正靠在椅子上睡觉,陈曦也等得累了,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只有箫言,像是永远是警醒的,站在一边安静地守着他们,身后一排齐整的护卫队,无声地站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