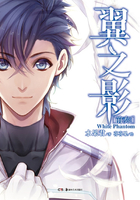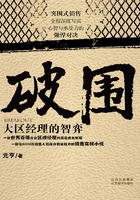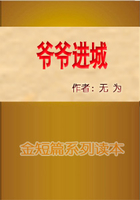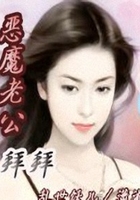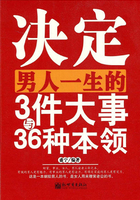院子东边的角落里,四五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或蹲或站。李秉义蹲在中间。想开点,想开点,老头们劝着,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递一支过滤嘴给他,他接了夹在耳后,仍旧抽自己卷的草烟。他也不让旁人,自己掏出烟包,格外仔细地卷着烟卷儿,自己点上,吧吧地发出声音。白烟从鼻孔蓬开,蒙住了一张皱纹如刀刻的脸。他眯着眼睛躲避夕光,夕光照着他一头乱发,如腾腾的火焰。无论旁人说什么,李秉义老人始终无话,起初大家以为他受不住打击,他和老太太向来是村里模范的夫妻。好长时间过去,他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每一支烟都卷得一丝不苟。大家的担心放下了,又有些不高兴,心想,你心肠就这么硬?好歹一张床上滚了一辈子了!几位老人先后留下不同的借口,走了。李秉义独自蹲在墙角,脚前散着十多二十个烟蒂。夕阳只照得到他的一丝头发尖儿,如洪水上浮动的一蓬老草。
终究没人质问主人家老太太是不是上吊自杀的。许多事是不能点破的。悲哀如同黄昏,很快在大多数人身上滑过,接下去是现实的事务,无论如何,丧事需要操办。只有那几位哭泣的老人还沉浸在悲哀里,在她们的哭诉中,悲哀和一辈子的岁月一般漫长。
有人买菜,有人到村里借桌椅板凳,有人去向老人的娘家报丧。忙乱中竟有一些热闹的气氛。回家拿菜刀的妇女在李家门口见到李秉德媳妇,脸上不禁露出几分诧异之色。听说不是病死的?李秉德媳妇拉住宽脸女人,询问道。妇女们那时候都没注意观察她的脸色。宽脸女人说,大妈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呢?话说出口才想到,李秉义和李秉德两家不说话几十年了。就低了声说,大妈,这话只能和你私下说说,是这个死的。说着扬起下巴,用右手虎口掐住脖颈。似乎这样还不够,她又加了一句,说,吊死的!她以为李秉德媳妇会幸灾乐祸,不想她脸色黯下去,低低说,她还比我小一个月呢,怎么就走了这条路。
妇女们走后,李秉德媳妇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她身子向前探着,细细倾听院子里的声音。门口人来人往,看到李秉德媳妇,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不止一个人向她打招呼。大妈,你进去看看?她支吾着,脸上似笑非笑,说不进去了,有什么好看的。
她什么也没做,回去了。她家和李秉义家很近,中间只隔着一户人家,走一段下坡路,拐个弯就是。两家虽然多年不交往,在村里脸碰上脸也不说一句话,对彼此反倒知根知底。不用打听,村里人自会告诉他们对方家里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希望他们两家和好呢,还是希望他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彼此了解,两家人做事都会尽量避开。就说一件事吧,李秉德媳妇从来不和死去的老人同时回娘家。
两位老人结婚前就是一个村的,还是远房堂姐妹,从小玩到大。死去的老人先嫁过来,一年后把小叔子介绍给自己的堂姐,也就是现在的李秉德媳妇。她对堂妹是心存感激的,若不是堂妹撮合,她不可能离开东山嫁到坝区。她们村离得很远,要翻过几座大山才到,起初每次回娘家两姐妹都要同去同回,后来为了分家产,两家大吵一架,两姐妹再不来往,回家都是各走各的。她们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不知如何回答娘家人对另一个人的询问,也因为那么一段路,一个人走心里总有些怕。时间久了,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李秉德媳妇有时就后悔,当初要是不吵那一架多好。两个人走在路上说笑的情形,似乎一时间又回到眼前,不免心里一阵惆怅。又想,不晓得堂妹有没有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