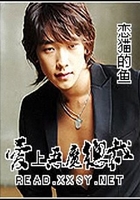我们的故事是从2009年1月26日开始的,也应该在2010年1月26日结束。两个1月份的天气没有多大差异:清晨都是浓雾弥漫,寒意刺骨,淡淡的太阳没有什么温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众人骨子里的寒气略略散去。有钱人家不愁取暖的家什,他们有电暖气片、壁炉、威士忌酒、厚厚的棉被和热水袋。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在路旁度过一夜又一夜,很多人受冻而死,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死亡数字。
2010年一开始就带着悲伤的气氛,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来说都是如此。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场排球比赛正在进行时,一个塔利班分子引爆了一枚炸弹,三十二名观众被炸死,七十多名观众受重伤,凶手也在爆炸中丧命。这种疯狂行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而与此同一天,印度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者比利?阿里安?辛格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二岁。去世前,他一直独自在小木屋里与老虎、豹子和其他野生动物为伴。这些动物都不曾伤害过他,因为他已经成了它们的朋友。辛格是非常奇特的人物,他出生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一个名为卡普塔拉的小城镇,整个家族都信仰基督教。很显然,圣方济各的人生对他影响颇大。辛格向全世界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你真诚地爱护动物,爱护鸟类,它们就会同样地爱你。现在,这个世上并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生活。
在一个寒风刺骨、浓雾笼罩的上午,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来到印度进行官方访问,她在德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她父亲以及其他亲属遭到亲巴基斯坦的暗杀者枪杀后,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几近敌对状态。哈西娜的父亲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亲近的人称他班加?班度,他是孟加拉国的开国之父,孟加拉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印度曾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及自由战士与巴基斯坦军队作战。拉赫曼死后,孟加拉国及其历任统治者都对印度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争端时,都与巴基斯坦站在一边。谢赫?哈西娜的做法则有所不同,她是支持印度的。鉴于此,印度的确很有理由热烈欢迎她来访。
两天后,即1月12日,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这是有史以来破坏性最严重的地震之一。海地人做了什么事,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无所不能的仁慈的造物主又在哪儿?
可能他在大壶节期间去了哈里瓦,浸在冰冷刺骨的恒河圣水里。他是想洗去在海地犯下的罪恶吗?一如既往,有上百万人去庆祝大壶节。不过这次造物主很注意,庆祝的人没有发生践踏事件,没有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因为他也在这些人中间。不管怎样,他还是组织了一次日食,以此来表达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心怀遗憾之意。
1月17日,印度西孟加拉邦前任首席部长乔蒂?巴苏去世。他已卧病很久,这给印度领导人很多机会去关心他的健康。他们成群结队前去看望他,从总理到首席部长,以及其他盼望在他床边拍合影的人。他曾担任首席部长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但并没有为西孟加拉邦做多少事。在担任首席部长期间,他允许工会破坏了很多实业公司,工会组织了大量游行活动,还围堵封锁企业家的住宅。尽管如此,巴苏还是创纪录地在位如此之久。加尔各答人为他开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追悼会结束时,战士们对空鸣枪,同志们紧握拳头,以此向他致意。
浓雾和寒意仍然一天接着一天,24日早晨更是浓雾笼罩,令人担心独立日的盛大游行可能无法照常进行。很多航班和火车都取消了。幸运的是,在独立日那天,早上八点以前浓雾就散了。韩国总统是主要嘉宾,他亲眼见证了印度的实力,明白任何国家都别想对印度不轨。
我们偏离了主题,还是回到正题吧。“日落俱乐部”怎么样了呢?1月1日和2日,俱乐部成员仍然一如既往地碰面,他们讨论了2010年头两天里发生的事情。
1月3日清晨,在贝格之家,每个人都按时起床做晨祷,同时也在等着男主人发出那一声:“噢!安拉!”这是他在伸开双臂打哈欠时大声喊叫的内容,同时也表明,所有人都该从这一刻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然而,这天大家一直没有听到男主人的喊声。莎吉娜夫人着手给大家安排这一天该做的事情:给仆人交代午餐和晚餐的菜单,给他们买牛肉、鸡肉和蔬菜的钱,命令其他仆人做日常的家务。就这样,半小时过去了。
随后,莎吉娜夫人吩咐一个女仆给男主人送茶并叫醒他,女仆便用托盘端着茶杯往贝格的房间走去。大家先是听见托盘和茶杯摔在地板上破裂的声音,紧接着就是女仆的尖叫声:“啊,安拉,噢,上帝,怎么会这样!”莎吉娜夫人和其他仆人都跑向贝格的卧室。贝格的眼睛和嘴巴都半张着,早已没有呼吸了。莎吉娜放声痛哭:“贝格,你怎么会这样啊?把我就这样扔下了!”她不停地捶胸,不住地拍打前额。仆人们也互相拥抱着大声哭泣。迦利布说得很对:
是噪声让房子成为家;
如果不是哀嚎逝去之人的悲声,
那就是婚礼上欢乐的歌声。
过了好一阵子,莎吉娜夫人才控制住情绪,开始安排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她吩咐道:“通知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随后又加了一句:“还有报社。”于是仆人们忙了起来,用家里的两部手机和一部座机给每一个他们能想到的人打电话。
布塔正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房间里暖意融融,椅子面上也衬有棉垫。他已经浏览完六份报纸的新闻标题,正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隔壁房间里的电话响了,布塔从来不接电话,于是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哈巴德去拿起听筒,听了打电话过来的人说的话后,他把无绳电话拿过来给布塔,说道:“是贝格先生家打来的。”
布塔接过无绳电话,另一端的声音问道:“请问您是萨达尔?布塔?辛格吗?”
“我是,”布塔答道,“说话。”
“先生,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贝格先生今天早晨已归于真主。”
“你在说什么?”布塔感到非常迷惑,“昨晚我还和他聊天来着,他看起来很健康。”
“只有安拉知道,”仆人答道,“女仆给他送早茶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女仆尖声大叫‘噢!安拉!’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冲进了他的卧室。莎吉娜夫人叫我告诉您,葬礼在下午三点举行,他将安葬在尼桑木丁的家族墓地。还烦请您通知一下潘迪特?沙玛先生。”仆人声音哽咽着放下电话。
布塔闭上双眼,泪水顺着两颊滑进胡须。他抽泣起来,泪水不住地涌出眼眶。几乎半个小时过后,他才平静下来。布塔觉得自己无法打电话把消息告诉沙玛,于是写了一张便条,叫巴哈德送到沙玛家去。便条上面写着:“刚才接到贝格家来电,他今天凌晨在睡梦中去世。葬礼下午三点举行,两点半左右到我家来接我一起去。布塔。”
下午两点半,沙玛的司机按响了布塔家的门铃。布塔上了沙玛的车后,沙玛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昨晚他还好好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布塔答道,“他家仆人只是说,有个女仆送早茶给他时,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他们都没再说话。贝格之家的大门关着,外面停着很多小车。沙玛和布塔下了车,有人将他们领进家门。房子前面的草坪上已站满人,很多人都戴着号帽,身着宽松裤和袍子,还有些人穿着西装。仆人将沙玛和布塔领到阳台上,莎吉娜夫人正在那里接待前来慰问的女宾。他们两个以前都没有见过贝格的妻子,她看起来肤色白皙,身材丰满,有七十五岁左右。布塔不禁想起一句格言:“废墟宣告纪念碑的庄严。”贝格夫人哭得两眼通红,但她看起来很能克制自己。布塔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流,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力紧握双手,满脸茫然。沙玛简短地说道:“贝格突然离世,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四十年的友谊戛然而止,谁也没想到造物主的安排会是这样。”
莎吉娜答道:“非常感谢你们!每天晚上,他从罗迪公园回来后,都会说起二位。你们不用等着参加葬礼祈祷。谢谢你们到这里来。”
布塔心中充满悲伤,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痛苦的神情让莎吉娜深受感动。
草坪上,众人正排着队,准备参加葬礼祈祷。沙玛和布塔从他们身边走过,上了沙玛的小车。他们一路上默不作声,直接回了家。
接下来的三天,就像达成了默契一样,沙玛和布塔都没有去罗迪公园。没有了贝格,“日落俱乐部”不可能保持原样。布塔在自家公寓套房前面的草坪上兜圈,这里还是像往常那样,看不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只有少男少女在打羽毛球,随着球跑来跳去,他们的狗则跟在后面追着跑。沙玛则绕着可汗市场消磨傍晚的时间,凝视那些灯火明亮的商店橱窗。市场永远都在不停地翻修,一堆堆的砖头四处散放着,让顾客没法在人行道上行走,也没有地方可供停车,所以小车不停地从入口开进来,又从出口开出去。有些地方的人行道已经挖掉,以便拓宽道路,为举办英联邦运动会做准备。
沙玛一不小心就自找麻烦了。2010年1月10日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沙玛被挖得乱糟糟的人行道上一大块铺路石绊倒,倒在公路上,因为髋骨摔裂了,他疼得没办法站起来。帕万稍等了一会儿,费力地把他拖拽到人行道上,等着有人来帮忙。很多店主都跑过来,问是否需要他们提供帮助。沙玛在这一带已经住了很多年,所以大部分商家都认识他。又过了一会儿,沙玛的侄儿开着沙玛的车来了。他和帕万扶着沙玛坐进后座,然后驱车到家里接了苏尼塔,一起前往马尔霍特拉医生的私人疗养院。几个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还照了X光片,决定第二天早上给他动手术。沙玛整夜都疼痛不已,甚至连在床上翻个身都做不到。苏尼塔、帕万和沙玛的侄儿也在疗养院待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沙玛侄儿给布塔打了电话,告诉他沙玛摔伤的事情以及他们现在在哪里。
布塔立刻开车前往疗养院,那时沙玛还在手术室里。一个小时以后,沙玛被送回病房。尽管麻醉剂的作用还没有彻底消失,但他仍在痛苦地呻吟着。布塔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沙玛的妹妹坐在床的另一边,握着他的另一只手。沙玛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他妹妹尖声呵斥道:“谁叫你晚上去绕着可汗市场散步的?看看这后果!”
这时一个医生走进来,问道:“你感觉如何?手术很成功。我们已经把断骨接好了,不过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愈合。”
布塔大声地说:“医生先生,你怎么不给他吃一片止疼药?他痛得这么难受。”
医生冷冷地瞥他一眼:“我正打算给他吃药,我知道怎么做事。”
中午时布塔离开了沙玛的病房:“明天见,你过几天就会康复的。”
接下来两天,布塔都在疗养院里陪沙玛,把几张报纸上的新闻读给他听。他把性丑闻方面的新闻说得特别详细,让沙玛听得很兴奋。沙玛的疼痛感似乎减轻了,身体也显然在好转。只有布塔一个人在病房时,沙玛微笑着说:“布塔,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你可能不信我说的话。那个拉克希米,你还记得她吗?就是那个想嫁给我的女人?她今早来了。她结了,有两个小孩。当时病房里只有她和我,她坐在床边,吻了我的嘴唇,然后又脱掉上衣,说:‘吻我这里。’你简直难以相信吧!
“你这个幸运的家伙。”布塔笑骂道。
医生进来查房时,布塔尽力用礼貌的口气问道:“医生先生,您什么时候可以让沙玛先生出院呢?
“我们认为他适合回家的时候,”医生简短地答道。
“简直没礼貌!”医生一离开,布塔就咕噜起来,“我非常礼貌地提问,可他就像狗一样叫着回答我。”
“别介意他的态度,他很忙。希望他把我治疗得不错。”沙玛安慰道。
第二天下午沙玛就出院回家了。那个医生承诺过几天就去回访他,看看他是否恢复得很正常。布塔没有到沙玛家去看望他,因为那里挤满了沙玛的亲戚和朋友。
2010年1月15日下午,布塔没出门。他坐在扶手椅上,正犹豫着是到前面的草坪去走一圈,还是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溜达几圈,这时,沙玛的外甥女走进来,坐在他椅子旁边的凳子上,拿起他一只手握住。“出什么事了?”布塔问道。
“我想我得自己来告诉您。舅舅几个小时以前去世了。”
布塔痛苦地呻吟道:“不!不,不!”然后就抽泣起来。他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痛苦,只是在抽泣的时候绝望地绞着双手。沙玛的外甥女按住他的手,陪他一起坐了十分钟,然后静静地离开了。
布塔没有参加沙玛的葬礼,只是整天坐着,凝视着前方摆放了书架的墙壁。他就这样呆坐着,持续了一个星期。他在不同的报纸上阅读沙玛去世的讣告,总理和其他领导都称赞了沙玛。报纸上还有一则启事,宣布在佑福厅举行一次祷告会。布塔决定不去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去那儿,肯定会出丑的,因为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
布塔思绪万千,心情难以平静。他终于必须面对生活的真实面目,必须面对死亡了。贝格和沙玛都很了得,比大部分印度人都活得长久。自己和他们年龄差不多,很快也要抵达生命的终点。具体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他打开自己的电话簿,从A到Z,按照字母顺序一个个翻看着人名。每隔一个或两个名字,就有一个的下面画了一条线,线下写着:死,1981;死,1985;死,1987,等等。他又翻回到B,在贝格的名字下画了一条线,写上:死,2010.1.3。然后又翻到S,在沙玛的名字下画了一条线,写上:死,2010.1.15。他自己的名字也写在电话薄上,这并不是因为他老糊涂了,而是有人问他电话时方便搜寻。他在自己名字的旁边补充写道:
死,
日期?
月份?
年份?
布塔努力从消沉的心境中走了出来。现在已是2010年独立日的上午,他观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庆祝游行,这次的游行与去年的基本上一样,和前年的也差不多。
下午,布塔去了罗迪公园,有很多人在公园里野餐。老人凳空着,他坐上去,凝视着对面的大圆顶。一个园丁走过来打招呼,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先生,您有些日子没来了。您的朋友呢?”
“上去了。”布塔答道,朝天空举起双手。
园丁明白了他的手势:“两个都去了?真让人难过。”
布塔又举起一只手,说道:“唉,谁能知道造物主的安排呢?”
园丁认同他的说法:“嗯,神的意愿谁也不知。”
布塔转过头来,继续凝视着大圆顶,它的确和年轻女子丰满的胸部很相似。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