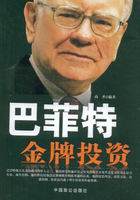我要讲的故事从2009年1月26日下午开始。那天是星期一,是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十九年的纪念日。尽管印度是1947年8月15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但印度共和国的众位领导很英明,认为8月中旬过于炎热和潮湿,不适合举行户外庆祝活动,而1月下旬则是个好时候,更适合用来庆祝共和国成立,于是他们便选择1950年1月26日签署印度共和国的新宪法。他们宣布这一天为全民假日,命名为共和日。
每年1月底,寒冬的凛冽渐渐减弱,日出之际,浓雾弥漫的黎明转化为阳光灿烂的早晨,鲜花盛开、巨嘴鸟啼叫的时节即将来临。
共和日是印度日历上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印度举国欢庆的唯一一个节日。在印度,无论一个人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还是印度祆教,都会庆祝这个节日。这一天,每一个邦的首府都会举行升旗仪式。此外,部队、警察和学生也会上街游行。
不过,这一天,印度庆祝场面最宏大的地方在首都,这里会展示印度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多样性。坦克、装甲车、火箭发射载具驶过大街;礼炮声隆隆;海陆空三军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行进,斜挎着随身佩剑做出敬礼动作;骑兵乘着骆驼和马匹,身后的队伍来自各个邦,集中展示自己取得的各项成就,队伍周围,民族舞蹈演员在表演歌舞。大家在拂晓时就开始集合,沿着国王大道两侧排成长队。这条宽阔的大道从位于芮希那小山上的总统府开始,沿着斜坡向下延伸,斜坡两侧有两组宏伟的政府大楼,即北区和南区,大道末端通往庄严的战争纪念拱门——印度门。印度门上刻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第三次阿富汗始英战争以及1971年与邻国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失去生命的印度阵亡将士的姓名。在印度门的中间燃着圣火陈,常年不息,纪念这些为祖国献出宝贵生命的军人。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印度作为圣雄甘地的祖国,一向崇尚非暴力运动,以自己是和平使者为傲,为何会展示这么多致命武器和战斗力量来欢度国庆节。真相是这样的:我们印度人内心充满了矛盾。我们向世界宣传和平,同时也在为战争做准备;我们宣扬心灵的纯净、贞洁和禁欲,同时我们也沉迷于情欲。这让我们变得很滑稽。不过,我们的确也因此对这种庸俗的武器展示做了一些补偿——在朝着政府大楼群的胜利广场举行了一场阅兵仪式。在这里,人数众多的陆、海、空三军乐队不携带任何武器,只带着小号、长笛、单簧管、爵士鼓和风笛,在广场上往来穿梭表演。这场盛大的集会最后伴着钟鸣声。响起圣雄甘地最喜欢圣铃“与我在一起”。一天后,也就是1月30日,是甘地纪念日。这一天,印度领导人聚集在新德里的甘地陵,把鲜花撒在黑色的大理石平台上,这里是甘地遗体火葬成灰之所。你看,我们就是这种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很滑稽。
还是让我回到正题中来吧。大约中午时分,国王大道的游行结束了,人群开始逐渐四散开去。有些人前往附近的老堡垒,他们或在草坪上野餐,或在阳光下打着小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也能为大家提供休憩放松的空间,环境同样宁静,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离国王大道不远的罗迪公园。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飞鸟以及老式建筑。这里风景优美,可能是印度最具历史意义的公园了。这一带以前是海尔布尔村庄的一部分,散布着众多的墓地和纪念碑。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迁走这里的村民,以便保护墓地和纪念碑。
后来,印度总督威灵顿伯爵的夫人异想天开地想让自己青史留名,于是把分散的纪念碑用围墙圈了起来,在北面立了一道大门,供人出入,门上的题字为“威灵顿夫人公园”。她还建了一条煤渣跑道,以供殖民地时期的那些大人及随从骑马行进。不过,这一切都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任何人再称这个公园为威灵顿夫人公园,煤渣跑道也已经改造成鹅卵石铺成的人行道。这座公园也改称为洛提公园,因为其中大部分纪念碑是在罗迪王朝时期建成的。现在公园增加了三道入口,第二道入口仍然在北面,入口外还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进门以后,游客们必须得先走过一道叫做“八墩”的古老石桥,石桥位于一条护城河上。这条河当时是用来保护由围墙围着的塞干达尔?罗迪陵墓,这座陵墓建成于1518年。然后,再穿过两侧栽种着西班牙樱桃树的林荫大道,就到了公园中心。公园东面,靠近印度国际中心还有一道入口。另外的一道入口则在公园南面,入口外面不远处就是一条大道,两边栽满棕榈树。这条大道通往公园里最古老的陵墓,即建于1450年的穆罕默德?沙哈?赛义德陵。
罗迪公园里有一座很重要的清真寺,建于1494年,称为迦米清真寺。清真寺南面有一处极为宽阔的草坪,是公园里人们最喜欢待的地方。清真寺吸引人的原因是它的凸圆屋顶,看起来就像年轻女性的乳房,十分逼真,有乳晕,还有乳头。大部分清真寺和陵墓都有圆屋顶,但屋顶上面都有金属尖塔,毫无女性的妩媚可言。不过这个大圆屋顶则截然不同。你可以目不转睛地望着它,连续看上几个小时,惊讶于它与处女乳房的相似度。你会注意到,那些躺卧在草坪上的男人,都面朝着它,而他们的女眷则都背对着它。还有一条长凳也面朝这座清真寺,常来这座公园的人叫它老人凳,因为很多年里,有三位老人在步履蹒跚地绕着公园散步之后,就会一直坐在这条凳子上。他们闲聊时,目光就一直凝视着那个大圆顶。会英语的印度人说,这几个老人组成了“日落俱乐部”,因为每天的日落时分,他们都会看见这三位老人坐在老人凳上,而他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已处于生命的日落时分。
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日落俱乐部”的几位成员。首先我想介绍潘迪特?普里坦姆?沙玛,因为他在这三个人中最为年长。沙玛出身于旁遮普邦的婆罗门家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担任印度驻伦敦和巴黎的文化参赞;退休前,已是印度教育部的一号人物。他保养得不错,前半个脑袋虽然谢顶了,但后半部的白发从头顶倾泻而下,在双肩上卷起,这让他看起来有一副学者派头。沙玛身体很健康,只不过看书需带老花镜,听人说话需带助听器,吃饭需戴假牙而已。他相信阿育吠陀医学和顺势疗法。沙玛一生中有过很多女人,有外国的,也有印度本土的,但他十分侥幸地躲开了她们,没有迎娶其中任何一人。他一直和自己的老处女妹妹苏尼塔住在一起。苏尼塔比沙玛年轻几乎二十岁,在一个民间组织里工作。他俩在靠近可汗市场的公寓楼里有一套房子,位于一楼,包含两间卧室,两间浴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大客厅,一间书房,还有两个阳台。
客厅有一面墙壁靠着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那些书沙玛没有读过,也没打算读,这样摆设只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其他几面墙上挂着一些画,都是沙玛退休后自己画的,除了他本人,谁也看不懂那些画想传达什么意义,不过这些画作的确能让人觉得沙玛是个文化人。他还写诗,都是长长的素体诗,他到可汗市场找人把诗都印了出来,一旦有客来访,就免费赠送。由于他做官已做到教育部长一职,他也就水到渠成地成为很多文化机构、社会机构和学校董事会的主席。他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主席,能讲出很多深刻的道理,诸如“文化没有边界;一切宗教都在教导大家真理和爱的信念”等等。他没有敌人,无论男女,所有相识之人都颇为喜爱他。他有几条做伴的狗,分别取名为达布一号、达布二号和达布三号。沙玛还拥有一辆小车,有一个司机,这是某所学校配给他的,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会主席。每天小车载着他及仆人帕万和某条达布一起来到罗迪公园北门停下,接下来他身后跟着帕万和达布,一起绕公园一周,最后他在老人凳上就座,仆人和狗则坐在他身后的草坪上。
“日落俱乐部”的第二位成员是穆斯林显贵纳瓦布?巴拉卡图拉?贝格。他是伊斯兰逊尼派教徒,祖先是阿富汗人,早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前就已在德里安居乐业。贝格的祖先把做军人和销售希腊药物结合得很好。他们当初分到的土地靠近现在新德里的尼桑木丁,贝格的父亲在老城创建了好多家希腊药物连锁店,但老人更喜欢住在自己位于尼桑木丁的大房子里。那是一座宽敞的别墅,叫做“贝格之家”。别墅有很多房间,数个阳台,前面有一座大花园,后面则是家仆的住所。贝格不喜欢积攒书籍,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与书本无缘了。他收藏了几本乌尔都语诗人写的诗集,此外他也收藏了不少工艺品,令人印象颇为深刻,因为那些都是古印度莫卧儿王朝时代的物品,贝格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贝格身高六英尺,体格魁伟,头发花白,嘴唇上方留着八字胡,下巴那儿蓄着修得短短的山羊须。
与出身富裕家庭的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也就读于印度北方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在父亲去世后,又继承了房产。他娶了表妹莎吉娜,生了一大群孩子。他在年轻的时候偶尔会去妓院找找乐子,也会与妻子的女仆上上床。不过,若不考虑这些,他一直算得上忠诚的丈夫。1947年,英属印度分裂,他留在印度,加入了国大党,是尼赫鲁-甘地王朝的支持者。四十多年来,他一直每天定期到罗迪公园里散步。司机开着奔驰车将他送到公园南门那儿,他进入公园,绕着那些纪念碑漫步,身后跟着一个仆人,仆人推着一把轮椅。接下来,他会来到面朝大圆顶的长凳子那儿,在凳子上就座。即使已年过八旬,贝格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不用老花镜,不戴助听器,也没安假牙,只是偶尔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第三位成员是萨达尔?布塔?辛格。他是锡克教徒,身体矮壮结实,挺着个大肚子,从未剪过的头发已是雪白颜色。他头上没有围上那种六英尺长的头巾,而是总喜欢戴一顶棉帽或羊毛帽。他已经有八十六岁,但因为络腮胡子是染黑了的,所以看起来年纪没那么大。他饱受多种疾病的折磨:长期便秘,早期糖尿病,血压不稳,前列腺肥大,周期性发作的痛风。他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戴着眼镜;下牙都已掉光,现在下颚上全是假牙;助听器也用了好些年。布塔是个耽于奢侈逸乐之徒,自称信奉不可知论,可他每天在凌晨四点起床之际,都会为自己的健康祈祷,无数次诵念神灵的名字,还祈求印度教智慧之母保佑,最后还会唱一段锡克语圣歌,其主旨是祈祷远离不幸:
愿疾病之风不要吹到我,主是我的保护神。
罗摩画了一面墙,就在四周保护我;
兄弟,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真正的古鲁,把宇宙融合,
他告诉我牢记罗摩的姓名,这是对付一切疾病的灵药;
冥想他,只冥想他。
他拯救那些值得拯救的人;消除一切疑虑。
那纳克说,主慈悲为怀,是我的救星。
布塔是享乐主义者,同时也是不可知论者,但他还是会祈祷各方神灵保佑他。针对自身这种矛盾行为,他解释说:“谁知道呢!他们说祈祷可以创造奇迹,试一试总没什么害处。”
祈祷基本没有帮到他什么,于是祈祷之外,从黎明到黄昏,他继续吃各种各样的药片进行补救。
布塔在英国接受的高等教育,曾在伦敦和巴黎为印度政府服务。后来回到德里,开始为报纸撰文。他住在一套公寓里,离沙玛的住处不远。布塔家客厅里,几面墙边都安放着书架,上面摆放的书籍有小说、诗集、传记,也有被列为禁书的色情作品。他最喜欢的图书是文摘和诗选,乌尔都语和英语的都喜欢。他熟读大量诗歌并储存在脑海里,一有机会就脱口而出。人们都认为他很有学问,但他知道自己有点儿欺世盗名。
布塔是个鳏夫,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已经移民去了加拿大;女儿的丈夫已去世,现在和她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离布塔家很近。布塔虽然鳏居,但从未感到过孤单。在晚上只要他打开门,就有女士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极其健谈,是个话痨。布塔善讲荤故事,征服了这些听众,让她们很是着迷。他说起脏话来极为自然,好像说脏话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等到他感到厌倦,不想有人做伴了,就简单来一句:“现在都给我滚吧。”如果他不喜欢哪个人,就用旁遮普语骂其为狗杂种。其实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男女欢好后的产物。每天傍晚他都开车到印度国际中心,在那里待上个把小时,品一品咖啡,然后从东门进入罗迪公园。他也是先在公园里走上几圈,然后再来与另外二人汇合,坐在面朝大圆顶的长凳上。
要说这三个人是如何组成“日落俱乐部”的,那就话长了。沙玛和布塔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待过,那时他俩就认识了。碰巧二人又同时派驻伦敦,然后是巴黎。回到德里后,每天晚上他俩都在罗迪公园碰上。沙玛很喜欢与重要人物交往,布塔则醉心于树木和飞鸟。贝格最初既不认识沙玛,也不认识布塔。有很多年,他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陌生人看待。过了一段时期,他们遇到时开始举手示意,表示认出了对方。再后来,他们发现不知不觉中大家坐在了同一条凳子上,于是便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三人便成了朋友,于是,“日落俱乐部”就此诞生。
2009年1月26日下午,罗迪公园里熙熙攘攘,人流远胜其他日子。公园里那些大片的草坪上,都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众男女。每一群人周围都是一堆废纸盘和废纸杯,还有一些流浪狗摇着尾巴,乞求能吃上点儿残羹剩炙。
“日落俱乐部”三位成员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先后在老人凳上就座。每个人都轮流伸出双手,掌心摊开,好像在推什么东西似的。这是所有印度人都会做的动作,意在询问是不是一切都没问题。在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说了问候语以后,沙玛先用锡克语又用英语答道:“上帝慈悲为怀。”贝格则先用乌尔都语再用英语说:“真主应该受到称赞。”布塔先用旁遮普语又用英语说:“生命不息。”然后贝格用旁遮普语开启了话头:“庆祝独立日!”沙玛则用乌尔都语再说了一遍:“庆祝独立日!”布塔用尖酸的口吻打击他们:“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谋杀,屠杀,强奸,贪污,还有抢劫,前所未见。我们真是丢脸。”
贝格转移了话题:“你们看了电视上播放的庆祝游行没有?我每年都不会错过。”
“我也是,”沙玛说道,“场面真是盛大,让人觉得做一个印度人真自豪。”
“每年都是一模一样,把多少千万的卢比都倒进了亚穆纳河。”布塔怒骂道。
“并不是每年都一模一样,”贝格抗议道,“今年我们的总理第一次没能出席这种场面,因为他做了心脏手术,还待在医院里。今年哈萨克斯坦总统成为我们的贵宾,这可也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