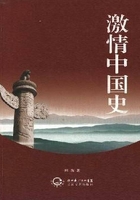生命只是一种偶然,万千景象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苏轼二十岁那年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赴京城汴梁应举,经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曾寄宿在一座寺庙中,老僧奉闲殷勤招待,兄弟俩在寺壁上题了诗。过了三年,苏轼去陕西任地方官,重又路过渑池,他和苏辙为此作诗唱和,苏轼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成为诗史上的名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一种很深的感慨首先是触景而生的:不过几年时间,殷勤好客的老和尚已经死了,埋在了一座塔下。他的笑颜、他的声音好像还在眼前吧,可眼前只有一堆埋骨的土。寺庙也已经破败,看不到兄弟俩当年题在墙壁上的诗。那些诗句还记得很清晰吧,可眼前只有颓败的土墙。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什么既定目标,因为外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受人的意志控制;人生到处会留下一些痕迹,但那些痕迹很快都会消失掉。也许,“伟人”会留下许多供人追忆的东西,譬如他的故居,他坐过的椅子,但那也只是做纪念活动的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维持某种陈设,通过这种陈设来解释某一段历史,它和被纪念的人倒是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呢?苏轼在想:就像鸿雁飞在茫茫的天空中,偶然在雪地上停息,留下一些印迹,而后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生命只是一种偶然吗?走过的路上那些模糊的印痕,星星点点,似断似连,又能够说明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呢?年轻的苏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感喟。
但不管怎样,人总还是要辛勤地努力吧!当年父子三人走在崤山道上,风雪交加,路途崎岖,蹇驴在颠簸中发出长长的嘶喊。
这就是路。如今兄弟俩都考上了进士,从小官做起,跟各样的人打交道,疲惫、厌倦总是难免,但总还要努力走下去,这就是路。
差不多和苏轼同时代,有一位天衣义怀禅师说过一段上堂语(开讲时所说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意思大致是:大雁从天上飞过,影子投在清澄的水池上。但大雁并不是有意要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池也无意留住它的影子。雁飞影过,如此而已。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这样去做事,才能行走于万类纷繁的人间。
苏轼诗与天衣义怀的禅语有非常相近之处,有人认为诗意是演绎禅语而成的。但他们的生活年代实在是很相近,而且天衣义怀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苏轼那时还没有到过江南,所以很难说苏轼写诗时受到他的影响。两者的近似,更大可能是“不约而同”吧;况且,两者的视角,也还是有些差异。
天衣义怀的话,根源是在《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说六祖慧能未出家时于市中贩柴为生,偶然经过一家客舍,听人诵读《金刚经》,听到这一句忽然醒悟,顿萌出家之志。
怎么叫“无所住”呢?简单说就是不执著,不受外界变化的支配。你在“异类”(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中行,有人夸你,你就兴高采烈;有人骂你,你就怒气冲冲;今天流行黄色你就一身黄,明天流行黑色你就一身黑……很快你就神魂颠倒、莫名其妙了。
如何又要“生其心”呢?佛教讲万事无常,本心清净,但并不赞成执著于空无——执著于空无也是有所“住”。南宋祖心宝觉禅师的偈诗说:“不知心境本如如,触目遇缘无障碍。”清净的本心不仅对于外界仍然有恰当的反应,有自然的喜怒哀乐,这种反应甚至是更为自如而美妙的。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情与之谐,心与之舞,飘逸之中,欣喜自生。更有“利乐众生,慈悲为怀”,也是一种“生其心”——实际上慈悲心构成了佛教非常重要的价值基础。
有僧人问赵州老和尚:“像你这样的圣人,死后会到何处?”赵州说:“老僧在汝众人之前入地狱。”问的人感到十分震惊,说:“这如何可能?”赵州毫不迟疑地说:“我若不入地狱,谁在那里等着救度汝等众人?”这就是佛的慈悲,禅者的宏愿。
在苏轼的诗中,“飞鸿雪爪”的比喻从情感上说带有惆怅的意味,不像“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那样表现得洒脱。但在哲理上,它也体现着佛禅的无常观。人世无常,虽然也可以导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若是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在这首诗里,两种情绪同时存在。
正像前面说过的,无奈也罢,旷达也罢,对苏轼来说,这些都不妨碍在人生道路上总须有所努力的积极态度。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一方面喜好老庄与佛禅,能够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世事的变幻,但作为一个官员,他却始终是正直和富于责任感的。他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堤,大水围城数十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住在城墙上的小棚子里,有家不回,以安定民心,终于率士民顶住了洪水的侵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任杭州太守时,他为了兴修水利而疏浚西湖,留下了一条风光绮丽的苏公堤。他绝不会把自己“空”成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意义的虚壳。
苏轼的另一首名作《题西林壁》,也可以放在这里比照着来读:
清·蒲华·山晴水明图以“无所住”的态度去应对无常,也可以引导出超越的旷达。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是苏轼在元丰七年(1084年)游庐山时题写于西林寺墙壁上的。当时陪同他游庐山的有东林寺住持常总禅师以及庐山的其他僧人,还有从黄州一起过来的老友、诗僧道潜(法号参寥),所以写诗说禅,正合当下的气氛。
作为诗来说,光是能够表现某种哲理未必就是好诗。
在这次游览过程中,苏轼还另外写了一首《赠东林总长老》:“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示人。”这首诗讲禅宗“无情说法”的道理,意思说自然就是佛性,溪声便在说法,一夜听来,有无限美妙的道理,只是不能告诉别人。
作为一首禅偈,这首诗也有它的好处,但从诗的艺术性来要求,因为完全是在说理,则未免显得枯燥了些。而《题西林壁》
则不同。这首诗字面上只是描写眼前景象、抒发游览的感受,并不直接说道理,让人感觉比较亲切。所以纪昀在《纪批苏文忠公诗》中说它“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其实,就是从说理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也比《赠东林总长老》来得深刻。因为它是启发性的,所以有更丰富的内涵。
禅本来不可说,以诗说禅,妙处在说与不说之间,说多了、说白了就不好。
庐山景象万千,移步换形,横看、竖看,远看、近看,从高处和低处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才是“庐山真面目”呢?在庐山中是看不到的,因为人的视角总是会受到当下所在地位的限制。要是你认为你看到的就是庐山,别人看到的都不对,就形成了偏执,而偏执使你无法认识庐山。
这不仅是说庐山。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世事总是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要想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生陷落在世俗的境遇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时空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佛法修持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破执,而破执首先是破“我执”。人心里梗着一个粗重无比的“我”,贪婪、自大、自卑,永远放不下自己,哪怕有再多的聪明,也免不了一叶障目。而一旦破除我执,潜在的真如智慧就得以显现,万象纷呈,因缘分明,心境自如,不受迷惑。
所以天衣义怀禅师说:“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