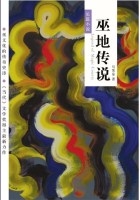麦基先生面容苍白,有点娘娘腔,就住在楼下。他显然刚刮了胡子,因为脸颊上有点白色的肥皂泡沫;他毕恭毕敬地和客厅里每个人打招呼。他跟我说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得知他是摄影师,挂在墙上那幅模糊的放大照片就是他的作品,那阴气沉沉的老太婆原来是威尔逊太太的母亲。他的妻子声音很尖,无精打采,相貌倒挺美,但很讨厌。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婚后给她拍摄了一百二十七次照片。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衣服,现在穿着样式复杂的白色雪纺裙,上层社会的女性在午后正式会客时穿的那种,长长的裙脚拖在地上。每当她像扫帚般在客厅里走动时,裙子就会不停地沙沙响。在这套裙子的影响之下,她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在汽修厂里她显得很有活力,现在活生生一副法国贵妇人的神气。她的笑声、姿势和言语渐渐地矫揉造作起来;随着她越来越膨胀,客厅显得越来越小,在醉眼的我看来,她似乎附在一根吱嘎作响的木轴上,吵闹地转个不停。
“亲爱的,”她声嘶力竭地告诉她妹妹,“现在很多人都是骗子。他们只惦记着钱。上星期我请一个女人来看我的脚,你要是看到她开的账单,肯定会以为她是帮我做阑尾切割手术了。”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麦基太太问。
“她姓艾伯哈特。她是上门替人家看脚的。”
“我喜欢你的裙子,”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很漂亮。”
威尔逊太太拒绝了这次恭维,她不以为然地扬了扬眉毛。
“这只是一件过时货啦,”她说,“我是随便穿穿的。”
“可是它在你身上显得很漂亮,你懂我的意思吗?”麦基太太固执己见地说,“如果你肯摆那个姿势,我想切斯特能够拍出一张好照片。”
我们大家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伸手掠开眼前一绺头发,笑逐颜开地看看我们。麦基先生歪过头,专注地盯着她,然后把手伸到脸前,慢慢地来回比划。
“我应该改变光线,”他沉吟片刻之后说,“我想突出五官的轮廓。我会尝试把背后的头发都拍进去。”
“我觉得光线正正好,”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的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又朝被拍摄者望去。这时布坎南大声地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麦基,你们俩喝点什么?”他说,“梅朵,再去弄点冰块和矿泉水来,否则大家都要睡着啦。”
“我跟那开电梯的小子说过要冰块的,”梅朵扬起眉毛,对下等阶级的靠不住表示很绝望,“这些人啊!你不老盯着他们还不行。”
她看了看我,莫名其妙地笑起来,突然又蹦蹦跳跳地走到小狗跟前,兴高采烈地亲了亲它,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厨房,仿佛那里有十几个大厨正在等她发号施令。
“我在长岛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言之凿凿地说。
汤姆茫然地看着他。
“有两张就挂在楼下我家里。”
“两张什么?”汤姆问。
“两张作品啊。其中一张叫‘蒙塔克[28]海角之群鸥’,另一张叫‘蒙塔克海角之汪洋’。”
凯瑟琳挨着我坐到沙发上。
“你也住在长岛吗?”她问。
“我住在西卵。”
“真的啊?个把月前,我去那边参加了宴会。在一个叫盖茨比的人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他隔壁。”
“嗯,大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29]的侄儿或者表弟。所以他才那么有钱。”
“真的吗?”
她点点头。
“我挺怕他的。我可不想被他抓住什么把柄。”
这份有关我邻居的新奇情报被麦基太太打断了,她突然指着凯瑟琳。
“切斯特,我觉得你可以替她拍些照片耶,”她脱口而出,但麦基先生只是爱答不理地点点头,然后扭头看着汤姆。
“我希望在长岛揽更多的活,可惜不得其门而入。要是有人帮忙介绍就好啦。”
“找梅朵啊,”汤姆失笑说,这时威尔逊太太正端着托盘走进客厅。“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对吧,梅朵?”
“干什么呀?”她意外地问。
“请你写信介绍麦基给你丈夫啊,这样麦基就能给他拍照啦。”他略作沉吟,跟着说,“‘加油站之乔治·威尔逊’,诸如此类的。”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他们俩都受不了自己的配偶。”
“不会吧?”
“真受不了他们,”她看看梅朵和汤姆说,“我是说,他们既然受不了,为什么还要勉强过下去呢?照我说,他们应该离婚,再彼此结为夫妻。”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来自梅朵,她偷听到了问题,满嘴脏话地给出了回答。
“你明白了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接着她又压低声音,“其实从中作梗的是他老婆。他老婆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人是不能离婚的。”
黛熙并非天主教徒,这个精心设计的谎言让我有点震惊。
“等到他们真的结婚,”凯瑟琳继续说,“他们会先到西部避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
“去欧洲更保险吧。”
“你喜欢欧洲啊?”她惊奇地大叫,“我刚从蒙特卡罗[30]回来呢。”
“真的啊?”
“就是去年的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啦,我们只是去了蒙特卡罗就回来。我们取道马赛[31]去的。出发时我们带了一千两百块钱,可是不到两天就在赌场的包房被骗光了。实话对你说,我们回来路上吃了很多苦头。天哪,我特别讨厌那个城市!”
我朝窗外望去,但见黄昏的天空蔚蓝得恍如地中海——然后麦基太太刺耳的声音又让我回到客厅。
“我也曾差点犯了错误,”她兴奋地说,“当年我差点嫁给一个矮个子犹太佬,他追了我好多年。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不停地对我说:‘露西尔,那人比你差远啦。’但假如我没遇到切斯特,那他肯定会得逞。”
“是的,但是你算走运的了,”梅朵·威尔逊不停地点着头说,“至少你没有嫁给他。”
“我知道。”
“可是我嫁给他了,”梅朵含混地说,“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你干吗嫁给他呢,梅朵?”凯瑟琳责备地说,“没有人强迫你啊。”
梅朵陷入了深思。
“我嫁给他,是因为我原本觉得他是个绅士,”隔了良久,她终于说,“我以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但他其实连替我舔鞋子都不配。”
“你当时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胡说八道!”梅朵仿佛遭了冤屈,大声辩白说,“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说我爱过他,还不如说我爱过这个人呢。”
她突然朝我指来,于是每个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我只好努力装出一副从未指望有人爱我的表情。
“我唯一发疯的事是嫁给他。我立刻知道我犯错了。他结婚的礼服都是跟别人借的,而且从来没跟我提起。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个人来要回去。‘哦,这礼服是你的啊?’我说,‘我以前倒是没听说过嘛。’但我把礼服给他了,过后我躺在床上,伤心欲绝地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真的应该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起话来,“他们在汽修厂楼上生活了十一年。汤姆是她第一个情人。”
大家纷纷拿起那瓶威士忌——第二瓶——往杯子里倒,只有凯瑟琳除外,她“觉得不喝酒也很高兴”。汤姆按铃把门房喊来,派他去买些驰名的三明治回来当晚饭吃。我很想出去,在柔和的暮色中朝东向中央公园走去;可是每当想要告辞,我就会被七嘴八舌的挽留缠住,这片刺耳的声音像绳子般把我拉回座位。然而我们这排位于城市高空的黄色窗户,在昏暗街道的偶然过客看来,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人生的秘密;我也看见他了,他抬头仰望,若有所思。我既在里面又在外面,对这变幻无常的人生,我同时感到心醉神迷和恶心不已。
梅朵把她的椅子拉到我跟前,突然间她暖烘烘的鼻息扑面而来,对我说起来她和汤姆初次相遇的故事。
“火车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小位子,总是没人愿意坐,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那天我来纽约探望我妹妹,准备在这里过夜。他西装革履的,我忍不住老看着他,但每次他看我时,我就假装欣赏他头顶上方的广告。下车时他紧挨着我走,穿着雪白衬衣的前胸贴着我的手臂,所以我说我要喊警察来,但他知道我是在说谎。我神魂颠倒地跟他上了出租车,甚至不知道我坐的并不是地铁。我心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想:‘人生苦短,人生苦短。’”
她扭头看着麦基太太,客厅里响起了她虚伪的笑声。
“亲爱的,”她大声说,“这条裙子我等会就脱下来送给你。我打算明天再去买一条。我准备把要做的事都记下来。要按摩,做头发,给小狗买个颈圈,买个那种带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我妈妈的坟墓买个有黑丝带的假花圈,可以摆整个夏天的那种。我得把这些事统统记下来,免得全都忘了。”
这时已经九点了——过了片刻我再看表,转眼间已是十点。麦基先生坐在椅子上打盹,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活像一幅黑社会打手的照片。我取出手帕,擦掉他脸上那点让我难受了整个下午的、已经干掉的肥皂泡。
小狗坐在餐桌上,在烟雾迷蒙的空气中茫然四顾,时不时发出微弱的吠声。大家消失了又出现,合计着要去哪里,然后又找不到对方,于是到处找,却发现对方原来近在眼前。快到午夜时分,汤姆·布坎南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地站着,激烈地争吵威尔逊太太是否有权利喊黛熙的名字。
“黛熙!黛熙!黛熙!”威尔逊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想喊就喊!黛熙!黛……”
汤姆·布坎南非常迅捷地甩了她一个耳光,打得她鼻血直流。
然后许多血红的毛巾出现在浴室的地板上,阵阵女人的指责声在房间里回荡,而盖过这片混乱的,是一长串时断时续的、痛苦的哀嚎。麦基先生被惊醒了,开始迷迷糊糊地向门口走去。走到半路,他转过身来,望着眼前的景象:他的妻子和凯瑟琳又是痛骂又是安慰,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来回寻找药品,有个伤心欲绝的人躺在沙发上,血流如注,却还试图铺开一份《城市杂谈》,遮住沙发套上的凡尔赛风景画。然后麦基先生转头继续向门外走去。我从衣架上拿起帽子,跟在他后面。
“改天一起吃午饭吧,”电梯吱吱嘎嘎地往下降时,他对我说。
“到哪吃?”
“哪都可以。”
“手别碰升降杆,”那管电梯的男孩不客气地说。
“你别乱说,”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哪里碰到了?”
“好啊,”我说,“我很愿意的。”
……我站在他的床边,而他坐在被窝里,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
“美女与野兽……寂寞……拉货的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然后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寒冷的地下候车室里,直盯着早晨刚出版的《纽约论坛报》[32]出神,呆呆地等待那班四点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