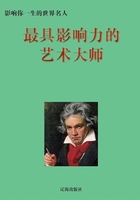我彻夜难眠,海湾里有个雾号[89]不停地悲鸣,我生病似的在怪诞的现实和狰狞的梦境之间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我听见有辆出租车开上盖茨比的车道,便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开始穿上衣服——我觉得我有话要告诉他,要赶紧提醒他某些事情,等到天亮就太晚了。
穿过他的草坪时,我看到他的前门依然敞开着,他靠着门厅里的桌子站着,表情很沉重,可能是因为情绪低落,或者整晚没睡。
“没有什么事,”他凄楚地说,“我等到差不多四点,她走到窗边,站了片刻,然后把电灯关掉了。”
我们摸黑在许多宽敞的房间里搜罗香烟,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大。我们掀起许多大帐篷似的窗帘,在黑暗中摸着无数英尺长的墙壁去找电灯开关——有一次我差点摔倒,幸好扶住了一架幽灵般的钢琴。到处的灰尘多得不可思议,而且那些房间都很闷,好像很多天没有透过气。最后我在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找到烟盒,里面有两根干瘪的香烟。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开,坐在黑暗中抽了起来。
“你应该离开这里,”我说,“他们肯定会查出来那是你的车。”
“现在离开这里,老兄?”
“去大西城[90]住几天吧,或者到北边的蒙特利尔。”
他不肯走。在不知道黛熙接下来要怎么做之前,他是不可能离开的。他这是抓住最后的希望不放,我也不忍心劝他松手。
正是在那天晚上,他跟我说起来他年轻时追随达恩·科迪的奇闻轶事——他会告诉我,是因为在汤姆的恶意打击之下,“杰伊·盖茨比”这个形象已经像玻璃般碎裂,这出长久以来引人注目的大戏终于落幕。我以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往事和盘托出,但他只想聊聊黛熙。
黛熙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大家闺秀”。他从前也曾多次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况下接触过这类人,但和她们之间总是隔着无形的铁丝网。他发现黛熙正是他的梦中情人。他常常登门拜访,起初是和泰勒军营其他军官结伴,后来是独自去的。黛熙的家让他惊奇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豪宅。但它之所以有那种令人屏声息气的紧张气氛,却是因为黛熙住在这里——尽管在她看来这地方平淡无奇,就像他看军营外的帐篷那样。他总觉得这座房子很神秘,似乎楼上的卧室是他前所未见的豪华与凉爽,而走廊里总有许多欢乐而美好的活动,还有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不是早已是陈年旧事的那种,而是鲜活的、清新的、芬芳的,像闪亮的新款汽车,像舞会上永不凋谢的花朵。他也因为有许多男人爱过黛熙而兴奋——黛熙在他眼里因此而变得更有价值。他觉得她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那些感情的痕迹和回声。
但他知道,他能走进黛熙家里纯属偶然。无论杰伊·盖茨比的前途有多么光明,他目前只是个身无分文、家世贫贱的年轻人,而那套军装给他带来的无形魅力也随时可能消退。所以他尽可能地利用他和黛熙相处的时间。他贪得无厌地、毫无原则地攫取所有他能得到的东西——终于,在某个安静的十月之夜,他迫不及待地占有了黛熙,占有了她的身体,因为他其实连跟她拉手的资格都没有。
他可能会瞧不起自己,因为他肯定是用欺骗的手段占有她的。我倒不是说他假装成百万富翁,而是说他刻意给黛熙营造一种安全感,让黛熙相信他的家世也是那么显赫——他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照顾好。事实上,他没有这些能力——他和黛熙门不当户不对,而且毫无人性的政府随时可能将他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但他没有瞧不起自己,事情的发展也跟他想象的不同。他起初可能只是逢场作戏——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弄假成真。他原本也知道黛熙不落俗套,但没想到一位“大家闺秀”竟然是如此的不落俗套。她若无其事地回到她那富裕的家,那富裕的生活,彻底消失了,留给盖茨比的是——失落的心情。他觉得离不开她了,这就是全部的结果。
再次相遇已是两日之后,当时盖茨比患得患失,好像他反倒吃亏了似的。现成的灿烂星光照亮了她家的阳台,在柳条长椅悦耳的吱嘎声中,她转身面对他,他情不自禁地吻上那美妙的嘴唇。她早先染了风寒,声音变得比平时更加嘶哑,也更加动人,盖茨比深深地体会到,惊人的财富能够锁住和保留青春与神秘,华美的衣服能够让人面貌焕然一新,而像白银般光彩照人的黛熙安逸而骄傲,人间的困苦挣扎完全与她无缘。
“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时发现爱上她之后我有多么吃惊,老兄。我甚至曾经希望她会甩掉我,可是她没有,因为她也爱上我了。她以为我的知识很渊博,因为我懂的东西和她完全不同……唉,我就这样忘掉了所有的雄心壮志,在爱河中越陷越深,而且突然间我并不在乎。既然跟她畅想未来能让我得到更大的快乐,去做那些伟大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在他奔赴海外之前最后那个下午,他抱着黛熙,两人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那是个寒冷的秋日,房间里生着火,她脸颊红扑扑的。她偶尔挪动身体,他随之稍微调整手臂的位置,中间还亲了她乌黑发亮的秀发。那个下午让他们得到了短暂的安宁,似乎是为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以便面对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久分离。在相恋的那个月里,他们从未如此亲密无间,也从未如此心心相印:她沉默的嘴唇轻轻地摩擦着他穿着外套的肩膀,而他则轻轻地触碰她的指尖,仿佛当她已经睡着似的。
战争期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在上前线之前,他已经是上尉军衔,阿贡森林战役之后,又得以升任少校,负责指挥师部的机枪连。战争结束,他心急如焚地想要回国,但由于某些意外的情况或者误解,他被派去了牛津大学。这时他很担心——黛熙在信里表示对他非常失望。黛熙不明白他为何不能回去。她感到外界的压力,她想见到他,想有他陪伴在身边,让她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是正确的。
因为黛熙是个妙龄少女,而她所处的又是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势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轻歌曼舞尽日不息,声色犬马终年无休。萨克斯管彻夜吹奏着如泣如诉的“毕尔街蓝调”[91],上百双金色、银色的舞鞋踢起闪亮的灰尘。到了茶歇时间,这首低沉而甜蜜的热门歌曲依旧不断地回荡着,而许多新鲜的面孔宛如被那些铜管吹落在地面的玫瑰花瓣,在舞厅里到处飘来飘去。
在这个暧昧的宇宙里,黛熙又开始抛头露面;突然间她又每天和五六个男人约会,天快亮时才昏沉沉睡去,而缀着珠子的雪纺纱晚礼服连同干枯的兰花,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床边的地板上。她内心一直迫切地想要做出决定。她想要现在就解决她的终身大事,马上就解决;而帮她做出决定的力量——是爱情也好,是金钱也好——必须是非常现实而且近在眼前的。
那股力量终于在孟春时节由于汤姆·布坎南的到来而出现了。他相貌堂堂,家世显赫,这让黛熙觉得非常有面子。她毫无疑问是纠结过,但后来又感到如释重负。收到她的信时,盖茨比还在牛津。
长岛天已亮了,我们打开楼下其他的窗户,让客厅里充满渐渐变成白色、又渐渐变成金色的光芒。有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伸在露珠之上,幽灵般的鸟儿开始在墨绿色的树叶里歌唱。空气缓缓地、令人愉悦地流动着,也算不上是风,预示着今天将是个凉爽而美好的日子。
“我不认为她爱过他,”站在窗边的盖茨比转过身来,带着自信满满的眼神看着我,“你要知道,老兄,她今天下午太激动了。他说的那些话让她有点害怕——让她觉得我好像是个无耻的骗子。结果弄得她语无伦次的。”
他苦闷地坐下来。
“当然,她也可能短暂地爱过他,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哪怕在那个时候,她也是更爱我,你明白吗?”
突然间,他说出一句很奇怪的话。
“反正,”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你觉得这句话除了表明他对这场恋爱投入了无法估量的感情和想象,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他从法国回来时,汤姆和黛熙仍在度蜜月,他情不自禁地用所剩无几的军饷,踏上了前往路易斯维尔的伤心之旅。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踏遍那些他们曾在十一月的夜晚并肩走过的街道,重游了他们曾开着她的白色跑车去过的旧地。就像黛熙家的房子在他看来比其他房子更加神秘和美好那样,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弥漫着伤感之美,尽管她已经远走高飞。
离开时他隐隐觉得,如果再努力一点,他也许能找到她——而现在是他把她抛弃了。硬座车厢——他已经身无分文——很热。他走到火车末端敞开的地方,找了张折叠椅坐下,车站渐渐远去,许多陌生建筑的背面在两边移动。然后火车开进春日的田野,有辆黄色的电车并排行驶了片刻,车里的乘客也许曾在街上偶然见到她那张苍白而充满魅力的脸。
铁轨拐了个弯,这时火车背对着太阳向东前进。太阳渐渐西沉,漫天的余晖似乎正在祝福她生活过的这座正在消失的城市。他绝望地伸出双手,仿佛只是为了抓住些许空气留作纪念,以便记住这个因为有她而变得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模糊的泪眼中,一切消失得太快,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那最鲜活、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地失去了。
九点时我们吃完早餐,走到外面的门廊上。气候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空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那个园丁,盖茨比原来那批仆人中仅剩的一个,走到台阶下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干,盖茨比先生。树叶很快就会落下来,它们会把水管塞住的。”
“今天先别放,”盖茨比回答说。他扭头看着我,略带歉意地说:“你知道的,老兄,我整个夏天都没用过游泳池。”
我看看手表,站了起来。
“我那班车十二分钟后开。”
我并不想到城里去。那天我根本没有心情上班,但还有别的原因——我不想离开盖茨比。我错过了那班火车,接着又错过了一班,终于还是走了。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最后说。
“一定要打,老兄。”
“我中午打给你。”
我们慢慢走下台阶。
“我想黛熙也会打过来,”他紧张地看着我,似乎是指望我会证实他的话。
“我想也是。”
“好吧,再见。”
握手之后,我就走开了。就快走到篱笆时,我想起某件事,于是转过身去。
“他们都是烂人,”我隔着草坪大声说,“那帮混蛋全部加起来也没你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