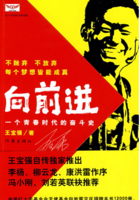那天晚上回到西卵时,我差点以为我的房子着火了。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半岛末端散发出通红的光芒,似真似幻地照耀着灌木丛,路边的电线也被照成几道细长的射线。拐弯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盖茨比的房子,从塔楼到地窖灯火通明。
起初我以为他又在大摆宴席,大家余兴未尽,干脆把整座房子的灯光都打开,玩起了“捉迷藏”或者“活捉沙丁鱼”的游戏。但四下里悄无声息。只有风儿吹动树木,而树木则拉动电线,使得许多电灯忽明忽暗,仿佛这座房子正在黑暗中眨眼。出租车“突突”开走时,我看见盖茨比从他的草坪向我走过来。
“你家好像在开世博会嘛,”我说。
“是吗?”他转过头,心不在焉地望了一眼,“我刚才在查看几个房间呢。我们去康尼岛[62]走走吧,老兄,坐我的车去。”
“太晚了。”
“那好吧,或许我们可以到游泳池玩水?今年夏天我还没用过它呢。”
“我要去睡啦。”
“好吧。”
他忍不住急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开口。
“我跟贝克小姐聊过了,”沉默片刻之后,我说,“我准备明天就给黛熙打电话,请她来喝茶。”
“哦,那倒不必了,”他若无其事地说,“我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
“你觉得哪天比较合适?”
“看你哪天方便啊,”他马上纠正我说,“我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你知道的。”
“后天怎么样?”
他考虑了半晌,然后不太情愿地说:“我得先让人把草坪修剪整齐。”
我们不约而同地低头看着周围的草地——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我的这边零乱不堪,光线较暗处是他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我猜他要找人修剪的是我的草。
“还有件小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说。
“你希望再往后推几天吗?”我问。
“不是啦,跟这个没关系。至少……”他结结巴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哎,我在想……喂,老兄,你赚的钱不是很多,对吧?”
“是不多。”
这句话似乎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他较为镇定地说下去。
“我想也是,如果你不介意我……你也知道的,我在那边有门小生意,算是某种副业吧,你能明白的。我在想,既然你赚的钱不是很多……你是销售债券的,对吧,老兄?”
“我还在学。”
“嗯,这件事你会有兴趣的。它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可以赚很大一笔钱。这件事说起来倒是十分机密的。”
现在我已经明白,要是发生在别的场合,这次对话很可能会让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转变。但他显然是因为要我帮忙而直截了当地想给我好处,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拦住他的话头。
“我已经够忙的,”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但不能再接更多的活了。”
“做这门生意你不用跟沃夫希姆打交道的。”他显然以为我耻于搭上午饭时提到的“关系”,但我告诉他不是这个原因。他又等了片刻,希望我会开口说话,但我已经很困,想不起来有什么好说的,于是他怏怏不乐地回家去了。
上半夜的约会让我很快乐,整个人感到轻飘飘的;我记得踏进家门之后,我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我不知道盖茨比到底有没有去康尼岛,或者他花了多少个小时在灯火通明中“查看几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给黛熙打了电话,约她到我家喝茶。
“别带上汤姆,”我提醒她。
“什么?”
“别带上汤姆。”
“‘汤姆’是谁呀?”她故作天真地问。
约好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到了十一点,有个人穿着雨衣,拖着割草机,跑来敲我的前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来替我剪草。这倒提醒我了,我忘记让那个芬兰女佣过来,于是我驱车前往西卵村,在几条湿漉漉的灰白巷子中找到她,又买了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鲜花白买了,因为下午两点时,盖茨比家送来各种奇花异草,还有无数个花瓶。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门紧张地打开,盖茨比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西装和银色的衬衣,系着金色的领带,匆匆走进来。他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显然昨晚是彻夜无眠了。
“全都准备好了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你说的是草坪吗?看上去很整齐。”
“什么草坪?”他茫然地问,“哦,你家的草坪。”他向窗外望去,但从他的表情判断,我相信他什么也没看到。
“看上去非常好,”他含糊其辞地说,“报纸上说这雨四点钟左右会停。应该是《纽约晚报》[63]上说的。喝……喝茶需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把他带进厨房,他看见那个芬兰女佣,好像有点不满。我们一起视察了从外卖店买回来的十二个柠檬蛋糕。
“这些还可以吧?”我问。
“当然,当然!看上去很好!”他言不由衷地补上一句,“……老兄。”
三点半过后,大雨渐渐停了,变成潮湿的浓雾,偶尔飘洒着几滴露珠似的小雨。盖茨比两眼无神地看着一本克莱[64]写的《经济学》,每次芬兰女佣的脚步踩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时不时向雾蒙蒙的窗户望去,仿佛外面有一系列肉眼看不见但怵目惊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最后他站起来,犹豫地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为什么?”
“没有人会来喝茶。太晚啦!”他看看手表,仿佛他在别的地方还有紧要事,“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了,这会还有两分钟才到四点。”
他哭丧着脸坐下,仿佛我强迫了他,就在这时,我家的小径上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音。我们俩立刻站起来,连我也有点紧张。我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院子里几株没有花的丁香树正在滴水,一辆巨大的敞篷车开到树下的车道。它停了下来。黛熙的脸庞在薰衣草色的三角帽之下斜翘着,带着明艳的微笑,欣喜地看着我。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我最亲爱的表哥?”
她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令人精神振奋,在细雨中格外动听。我的耳朵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话音高高低低地起伏,隔了片刻才领会到她说的话。她的脸颊上贴着一绺被雨水打湿的秀发,像是一笔浓墨重彩似的,我伸手扶她下车时,发现她的手湿漉漉的在滴水。
“你是爱上我了吧,”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否则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呀?”
“这是拉克伦特城堡[65]的秘密。你吩咐司机走吧,让他去消磨一个小时。”
“费迪,你过一个小时再来。”然后严肃地低声说,“他的名字叫费迪。”
“汽油影响到他的鼻子吗?”
“没有吧,”她天真地问,“干吗这么问?”
我们走进去。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客厅里居然没有人。
“咦,这下好玩了,”我惊奇地说。
“什么好玩了?”
她转过头,因为有人在轻轻地敲响了前门。我走出去,把门打开。盖茨比脸如死灰,双手沉重地插进上衣的口袋,站在一滩水里,凄然地盯着我的双眼。
他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三步并作两步从我旁边跨进门厅,然后踩钢丝似的突然转了个身,走进客厅消失了。这一点都不好玩。我自己的心怦怦地猛跳着,掩起前门,把又逐渐下大的雨水挡在门外。
大概有半分钟时间,四下里悄无声息。然后我听见客厅传来一阵哽噎的诉说和几下笑声,接着是黛熙的声音,故意很响亮地说:“再次见到你,我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啦。”
又是一阵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在门厅里无事可做,于是走进客厅。
盖茨比两只手还在口袋里,背靠壁炉架站着,勉强装出一副完全放松的样子,甚至显得有点无精打采。他的头靠得很后,都碰到壁炉架上那台失灵的时钟了。他就摆着这个姿势,眼神迷乱地俯视着黛熙,而黛熙则慌张但优雅地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缘。
“我们以前认识,”盖茨比喃喃地说。他朝我瞥了一眼,嘴唇咧开,想笑但又笑不出来。这时幸亏那台时钟被他的头压得摇摇欲坠,他赶紧转过去,用发抖的手指抓住它,把它摆回原处。然后他动作僵硬地坐下来,手肘撑在沙发的扶手上,手心抬着下巴。
“很抱歉碰到你的时钟,”他说。
我自己的脸现在涨得通红,脑子里有上千句客气的话,但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台时钟很旧了,”我白痴似的告诉他们。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像那台时钟已经在地上摔得粉碎似的。
“我们很多年没见了,”黛熙说,她尽可能装得不动声色。
“到十一月就五年整了。”
盖茨比这机械式的回答让我们至少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到厨房帮我准备下午茶,于是他们都站起来,但这时那个幽灵般的芬兰女佣端着茶盘走进来了。
手忙脚乱地倒茶切蛋糕之后,大家总算恢复了常态。盖茨比躲到角落里听我跟黛熙聊天,他那双紧张而闷闷不乐的眼神来回地看着我们两人。然而平静的局面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找个机会说了声抱歉就站起来。
“你要去哪里?”盖茨比立刻警惕地问。
“我很快就回来。”
“先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慌忙跟着我走进厨房,把门关上,低声说:“天啊!”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
“怎么回事?”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不停地摇着头说,“非常可怕的错误。”
“你只是觉得不好意思,仅此而已,”我劝解他说,“黛熙也有点不好意思。”
“她有点不好意思?”他将信将疑地重复了我的话。
“她跟你彼此彼此啦。”
“别说得那么大声。”
“你表现得像个小男孩,”我不耐烦地说,“你不仅很幼稚,还很没礼貌。黛熙一个人坐在那里呢。”
他抬手不让我说下去,用令人难忘的责备眼神瞪了我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重新回到了客厅。
我从后门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是从这里出去,神经兮兮地绕到前门走进来——走到一棵黑色的大树下面。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枝繁叶茂,替我挡住了雨水。这时雨又倾盆而下,我这不规则的草坪虽然经过盖茨比家园丁的修剪,但到处坑坑洼洼的,看上去像是洪荒年代的沼泽地。在这棵大树下面没什么好看的,除了盖茨比那座巨大的房子,于是我像康德[66]凝视教堂的尖顶那样,盯着它看了足足半小时。这座房子是一个啤酒商在十年前那股复古热潮[67]初期建造的,据说他愿意替周边所有寒酸的房子支付五年的税金,只要这些房东肯在屋顶上铺一层稻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伤了他那颗成家立业的心——他很快就一病不起了。哀悼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等不及地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当农奴,但却永远不甘心做乡巴佬。
半小时过去,太阳又出来了,杂货店的汽车开上盖茨比家的车道,给他的仆人送来了晚餐所需的生鲜食材——我敢肯定他今晚一口也吃不下。有个女仆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每打开一扇就会短暂地露面,然后从宽大的中央阳台探出身子,似有深意地朝花园里吐了口痰。我该回去了。刚才滴滴答答的雨声听起来像是他们的窃窃私语,时不时随着感情的波动而高低起伏。但现在外面一片寂静,我觉得屋子里应该也已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