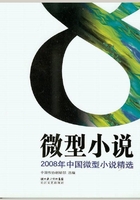村子不大,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迪赛尔,意思是新寨,可连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也说不上从啥时候起就有了这个村子。走出迪赛尔村,往左一拐就上了一座山,这山坡度不大,平缓地上升着。沿着山脊往上走,不用弓腰,不必喘气,轻轻松松就到了山顶。再从山顶往下走,依然是那种平缓的坡度,不费什么劲儿就到山的另一边了。和迪赛尔村相比,这边又是一番新天地:空旷、辽远,没有了缺衣少食的烦恼,远离了家长里短的闲话,一片宁静致远的景致。从山下再走百十米,是一座馒头一样没棱没角的小山丘,孤零零地耸立着。在迪赛尔人的心目中,这山丘有一份重重的份量。听听这山丘的名字,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寺院!在“寺院”的另一头,一座坡度依然很平缓的山平静地延伸而去,和迪赛尔村边的那座山如出一辙。如果从空中鸟瞰。两座绵延的山之间是个小小的山丘,令人立马就能想到一个词:二龙喜珠。的确,迪赛尔人从来认为他们这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两条龙一只珠,他们的村子是那龙身上的一块鳞片。
那座叫寺院的山丘上有些残墙断壁,村里的老人们说那里曾经有过一座寺院。看来,寺院这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
次琼就生在这个小村里。
宗教政策刚刚开放那阵子,村里就开始议论在“寺院”的残墙断壁上,再修一座寺院的事儿,起初是几个头面人物之间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勾当,到后来就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地到各家募捐钱物。刚刚当选上村长的达日杰到次琼家来要“尕透”,次琼的阿爸多郎把村长拦在门口,死活不愿意捐钱捐物。达日杰村长把村里已经捐了钱物的人家都记在一个油渍渍的小学生算术作业本上,看着多郎一毛不拔的样子,便把那个作业本拿出来说:“其他人家都捐了,你多少也得有个意思吧!”
“其他人家捐了是其他人家的事,我不是其他人家!”“多郎大叔,你这不对吧。就连靠国家救济养活的五保户老人洛洛都给了5块钱呢!”说着又把那本儿上登记的几户人家捐钱捐物的情况随口念了起来。
“巴日布家捐献牦牛一头,绵羊两只;才仁杰家捐献人民币50元,粮票50斤;达达家捐献绵羊两只……。”
“好啦,别念了!反正我一没钱二没物。这‘尕透’我出不起!”多郎没让达日杰再念下去,没好气地挥了挥手,转头就往屋里走。
次琼站在阿爸一侧,对阿爸的所做所为很不满意,便狠狠地瞪了阿爸一眼。次琼的阿爸曾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文革”期间,也悄悄在家里点灯供佛。只因为一个曾经是阿卡,“文革”中又还了俗的人告了密,有一次多郎正在一排酥油灯前念念有词时,村里的红卫兵冲进来,砸了他的佛龛,并把他绑起来批斗、游行。后来他就变得脾气火爆,对佛爷不恭不敬了。
多郎就要进门时,看见身旁的儿子,便随口对村长达日杰说:“如果你要人的话,我倒可以捐一个,把我这儿子带走。”说着,头也不回地进了屋,把村长达日杰晾在了门口。
村长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对次琼说:“你阿爸把你捐给寺院啦,你去不?”
“去!”次琼坚定地说。
“寺院”顶上的寺院神速地修建了起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寺院修得很华丽,经堂金碧辉煌,佛殿庄严凝重,前后左右还有护法神殿、藏经楼、佛塔、僧舍……
寺院正在修建时,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去看稀奇,唯独多郎家因为没捐“尕透”没去看,多郎还坚决不让次琼去看。次琼在小伙伴们“吝啬鬼的儿子”、“小吝啬鬼”的叫骂声中,默默躲在家里流着泪。次琼家邻居有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叫米琼,小巧玲珑的样子。只有她对次琼表示同情,到次琼家探望他。有一天,次琼父母都不在家,米琼便到次琼家,两人像大人一样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
“我知道是你阿爸不让你去看寺院的。”米琼说。
“他不让我去,长大了我自己也能去。”
“你什么时候长大?”
“……”次琼显然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过太多的考虑,“反正,我长大了,到寺院里去就不回来。”
“不回来?你不回来就住到寺院里吗?”
“我就当阿卡!”次琼坚决地说。
“当阿卡?”米琼一脸的惊讶,“那可是不能结婚的呀!”
……寺院建成不久,冬天就到了。藏族有句谚语:慈母般的夏天是不知不觉到来的,老虎样的冬天是诈诈唬唬到来的。那年冬天的到来,的确使迪赛尔的人们措手不及。那一年,迪赛尔村刚刚把牛羊作价分给了各家各户,欢呼雀跃了几天之后,都为你家的羊多啃了几棵草,他家的牛少喝了一口水的事儿争吵不休。次琼的阿爸多郎本来就倔强古怪,那几天,几乎天天可以看到他站在村口,在冬日寒冷的风雪中破口大骂。
有一天,次琼家的一头花白牦牛不慎丢失了,阿爸气呼呼地带着次琼去找那头丢失的牦牛。呼啸不止的寒风中,阿爸不断回头怒骂次琼。
“你这个败家仔,就知道玩,连一头牛都看不住!”
次琼大气不敢出地跟在阿爸身后。在阿爸的怒骂声中,他们走上了村子左侧的那座山,凄冷的寒风中,他们一前一后到了山顶。山顶的风很大,阿爸只好暂时停止了怒骂,斜着身子弓着腰走路,年小体弱的次琼刚刚走到山顶,就被风吹得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
“孬种!”阿爸恶狠狠地骂着,伸手撕住他的领口,把他拉了起来。
四野荒芜空寂,星星点点的残雪无奈地躲在石缝草丛中;枯黄的芨芨草一声声发出凄惨的悲鸣。就在这时候,次琼看见一个身着袈裟的阿卡正从那座馒头一样的山丘上走来,在荒凉得没有一点生气的原野上,他那绛红色的袈裟在风的抖动下,一如猎猎飘舞的旗帜,把次琼的眼睛一下子点亮了。
次琼的屁股刚才摔得生疼,但那绛红色的袈裟却使他忘记了一时的疼痛,他目转睛地盯着那个阿卡,让那团红色像一簇火焰一样在他的眼睛里燃烧。那火焰先是从他的眼角燃烧起来的,接着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充满了他的眼睛。由眼睛又扩散到他的脸上,使他的脸一片绯红,好像是害羞或者喝了酒一样。
“你这呆子,你看什么哪你?”
次琼似乎没有听见阿爸的话,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
此刻,次琼只觉得呼啸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寒风倾刻间停止了,芨芨草的低泣如美妙的天簌令人赏心悦耳。斑斑驳驳躲藏在石缝草丛中的残雪变成了一朵朵圣洁纯白的鲜花。
阿卡已经走到了次琼和他阿爸跟前,甚至还朝着次琼笑了笑。
就在阿卡和次琼擦肩而过时,次琼忽然泪流满面。俗话说,水火不相溶,他眼中的泪水一下子浇灭了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一切又回复了,风还是那么冷,芨芨草的悲鸣依然那么凄凉。
“呆子,你不去找牛啦?”阿爸朝次琼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次琼又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残雪躲不过寒风的一再骚扰,反过来为“风”作怅,夹杂在寒风中游荡着。雪片打在次琼的脸上一阵阵刺痛。这时他才发现脸上的泪痕已经冻成了薄薄的冰壳,风一吹,便像打碎的玻璃一样哗啦啦掉了下来。
次琼如梦初醒。
那个绛红色的背影在他的身后渐渐地远去了。
“我喜欢袈裟,红红的,好看!”次琼从地上爬起来,没头没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