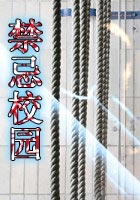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有一段又一段温和的声音。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有这样声音的中年男人,我想应该不是个坏人。他最后一句问我能否赏光,我没有拒绝的力量。我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他就是带蛤蟆镜的女人的男人。听说他有很高的职位,有很多的钱。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时候她也在旁边。他又想要跟我见面,这次没有她,不过我想还跟她有关。
他要跟我说什么,他知道了什么,他不应该知道的。
我打电话告诉她,你的男人要见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她说连她怀孕的事他都不知道。她也很疑惑。而且他竟然知道我的电话。挂了电话,我开始紧张,额头上老沁汗。
我紧张了一阵儿,丁当打来电话说她又不回来了。我问她老忙,到底忙什么。她让我别问了,反正是好事,到时候给我个惊喜。她连个再见都不说就挂了电话,她老这样,三年了我还没有习惯,总觉得话没说完,等见到她又没话可说。
我牵着那条狗在楼下晃悠。自从那天我看到了狗眼里的深刻,就给它穿上了衣服。衣服有些大,在狗肚子上垂着,倒看出几分大气来。它在前面小跑,我在后面跟着,我拼命想那个男人要与我见面的理由,他刚才说只是为了叙叙旧,谈谈她。我总结的理由如下:
第一, 就像他说的,叙叙旧谈谈她。
第二, 约我出去臭揍一顿,然后警告我,让我离他们远点。
第三, 酝酿一场阴谋。
第一个理由很浪漫,第二个理由有点下三滥,唯有第三个理由合情合理。我手里还攥着牵狗的缰绳,手心里全是汗。
我在去赴约的路上开始想阴谋。想着想着,满脑子都是关乎阴谋的电影,而且搞阴谋的人下场都很惨。
我到了。我看到了他。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手大而温暖,我还能记起三年前的感觉。他的脸非常干净,头顶上还有几根头发倒在一边。他冲我笑,很谨慎,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嘴角又抖了抖,显着不安。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我老以为出场的时候会头顶光环身披祥云,没想到会这样。
他开始说话了。话说得很慢,说话前总要想一想。说话的内容与她无关,与我也无关。他在谈茶。
我不懂,我洗耳恭听。我蹲在茶馆的包厢里听他谈了半个小时的茶道。我的耳根好像清净了。他确实在讲经论道,可一点也不像,倒有几分跟我商量事儿的样子。
不知道在哪个节骨眼上,话锋一转,他问我,你还爱她吗。我怔了怔。说了这么多,才开始谈她。
我说我有老婆了。他说,你在逃避我的问题。他又问,你还爱她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爱。他搓了搓手,许久没有说话。我说,这个问题对我们俩都没有意义。他说,对我有意义。我问他。他继续说他可以成全我们。
我又说我有老婆了。他温和地笑笑说,我也有老婆。
他掏出一盒烟来,问我介意他抽烟吗,我说也给我一只吧。我们俩分别点上,他吐出一口烟,我也吐出一口烟,两口烟在我们之间相互交融又四散开去。
他说,你老婆叫丁当吧。我说,你真是神通广大,什么都知道。他回答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都藏不住秘密。他继续说,我见过她,人很漂亮,身材更好,她现在为我做事。他看了看我僵掉的脑袋,接着说,你不用紧张,她在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剧团兼职,她舞跳得很棒,你眼光不错。他说话一句一顿,听得人心急。他把话接下去,剧团的团长她也当得了,我看她有这个能力。
我才知道丁当都在忙什么,原来还有第二份工作,连这也不告诉我。
他又冒出一句,你跟她是不是见过面。他看了一眼我发直的眼睛,说,不用紧张,老朋友见个面很正常,我不会怪你。
我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熄了烟说,我要你去追求她。
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放在桌在上。手指落在卡上,敲得咔哒响。他说,她要跟你走,这就是你的。他把卡往我这边推了推。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想甩了她,她有点让我烦。
我说,丁当怎么办。他说,那就看你的了。我横了横脖子,晃了晃肩膀,我告诉他绝对不行。他笑了笑,我越来越不喜欢他的笑。他说,你跟她一样,不喜欢思考。
他顿了顿,指着我说,我选择了你,你别无选择。他又喝了一口茶。我说我不怕威胁。他说,我只是在为你想个办法,当然归根结底是在为我自己想办法。他又说了一句,你不想鱼死网破吧,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他语速开始快起来,他说,小帅哥,我要是想鱼死网破,也就不找她的小情人了,你说是不是呀。
我说我的心里有点乱。他说,那你回去考虑两天。他又推了推那张卡,接着说,卡你先拿上,下次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密码。
我走了出去,站在街角就给那个女人打电话,我说我要见她。她说不方便,他要来。我跟她说了中年男人告诉我的话,她沉默了一阵说让我等她的消息。挂了电话,我看了看表,还不到九点,我不想回家。我在街上走着。
手机又响了,黄莉莉打来的电话。我一接电话就听到那边的抽泣,她边哭边说,老师,快点救救我。我说怎么了,她说那小子在她宿舍楼下喊了两个小时了。我说我马上到。挂了电话,抬头发现电线杆矗立在我的面前,近在咫尺高高在上,发出嗡嗡的电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