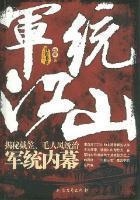很久没下雨了,沙武身后跟着一路烟尘。路天天都是这条路,街天天都是这条街,从这边到那边,从街西到街东,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座高楼。这是镇子上最高的楼,爬到楼顶可以看到沙武学狼叫的拗口。南北大街在这里把我们的路分成了两段,街东和街西。所以,这高楼就成了镇子的中央,我们都叫它百货大楼,其实它只有四层,比后山矮多了。
后山比原来也矮多了,有一次,突然就矮了很大一截。我是站在我家的院门口发现的。我站在那个路灯底下,目光越过百货大楼往后山顶上看,后山顶就那样突然矮了一截。当时,爸爸拉着我的手,我拼命摇晃,爸爸看了看,说要死人了。后来,镇子上就有了很多很多的哭声,我才知道那群街东的孩子都没有爸爸了。他们被埋在了后山里。
明星也去了那里,要拍挖煤的戏,演一个被埋在后山里的矿工,也就是要演其中一个街东的孩子的爸爸。他们的爸爸满脸煤灰,一脸坏笑,乱摸酒馆里的女人。他那么酷,怎么演那些脏人。依我看来,至少要演个矿长,穿件白衬衫,站在拗口不停地指指点点。不过,我再也见不到我们的矿长了,煤一挖完,他就消失了。爸爸说,他坐着飞机去了外国。他一定有很多很多钱。
我的他,就在那个山坞里,要想见到他,不得不穿过那个拗口。沙武喜欢对着拗口学狼叫。我只有穿过那个拗口才能见到她,不过听沙武说,拗口有很多人把守,就怕我们进去,连记者都不让进。
我问沙武,记者都不让进,你怎么带我进去。沙武说,我认识云母。我问云母是谁。沙武说守拗口的人。我跟沙武上了山。在那棵歪脖树下,沙武说,脱吧。阳光穿过枯掉的枝干,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眼睛里。我脱掉了裤子,风吹了进来,像有人抽我的屁股。我问沙武,你会娶我吗?我说,你爹让你娶我。他不说话,趴了过来,想看得仔细。他的脸涨得通红,要过来亲我的嘴。
我一脚把他踹开了。我的大腿在太阳下泛着灼灼的光芒。如果我的他不要我了,也许我会考虑嫁给沙武。我要见我的他,还要洞房花烛,我想我的脸已臊得通红。沙武说,你的脸红了。我说,你的脸也红了。说完我就穿上了裤子,拽沙武下山。沙武下山的时候像只猴子。他在路上说,我一定让你见到明星。说的时候还冲我攥了攥拳头。
沙武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相信他。
我们见到了云母,站在他面前像犯了什么错误。沙武还给云母递了根烟,云母看了下烟嘴,说不抽。
他长了一对老鼠眼,滴流乱转。摩托车停在他的屁股下面。云母说,要想此路过,就得留下买路钱。沙武说,我们有交情。云母说,买卖是买卖,交情是交情,不要混在一块谈。沙武说,没这么多钱。云母说,那就算了。又说,凑够了钱,我在拗口等你。摩托车嘟嘟响了两声。屁股后面喷出一股烟。
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大声说,傻妞,越长越好看了,像一根水葱。
沙武看了我一眼。
周围全是汽油燃烧的味道,很好闻。沙武说,凑钱。我说我没钱。他说想办法。我们就分开了。我从街东回到街西,从百货大楼旁边走过,一块接着一块的大玻璃像一面又一面的镜子,我看到一个穿着烟熏红外套的女孩缓慢走过。我停下脚步,想看看她是玻璃里面的,还是镜子里面的。她也停下来了,望着我,葱白样的小脸。原来是我。我真的像一根水葱。
我的家里空无一人。爸爸去了学校,他是一个数学老师,站在讲台上,写一黑板的方程式。我就是因为不会做方程式,才退了学。沙武会做方程式,爸爸说他是个比我聪明的人。可是他的爸爸老去亲寡妇的嘴,常常被寡妇的儿子揍得满脸是血。沙武说丢人的很,直不起来腰了。他就退了学。
他开始跟踪他的爸爸。
空荡荡的几间屋子,响彻着我的歌声。我在家里边跳边唱,像我的他一样。唱着唱着,太阳从那扇窗口消失不见了,留了一团光,映在衣柜上方的白墙上。那团光晃悠着,让我感觉越来越悲凉。我停了下来。
爸爸是没钱的,如今还欠着铁墨的钱。我怎么能张口要他的钱呢。只能靠沙武了。沙武要是想亲我的嘴怎么办呢。沙武就喜欢亲女人的嘴,据说他亲过理发店里的老女人的嘴。
他是个不要脸的人。
外面响起一阵尖利的口哨声。沙武来了,院门哐当一下被他推开了。他一耸一耸地走进了我的家里,二话不说就坐在我的床上。我的床很干净,他的裤子却脏的要命,我让他从床上滚下来,别脏了我的床。他还是不说话,走到那面镜子面前,看着那张明星撩头发的宣传画。他说,我一定让你见到他。我说,我也一定要见到她,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
沙武说,有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他说,夜里八点,我来找你。
他又一耸一耸地走出去了。他的背影确实很像他爹,他根本不是野种。院门又哐当了一下,他尖利的口哨声渐渐远去,屋子安静了下来。
夜里八点,我家的座钟还没有敲响。沙武的口哨声就来了,听起来像来自很远的地方。爸爸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早点回来。我对着将要打开的屋门说了一声,知道了。
我问沙武,要去哪?沙武说跟我走。他不停地搓着手,又把手上的关节按得生响,像镇上的男人要打架之前的模样。那条路上光里有雾,雾里有光,谁家的钟又在响。街上开始有了人,我没有听到最后一声钟鸣。百货大楼到了,沙武说,我们到了。我跟他进去了。他要干什么,我也懒得想。我只是在那块玻璃面前整了整耳朵后面的头发。
百货大楼里的人少得可怜。长长的玻璃柜台里面站着高高的导购小姐,她们看了沙武一眼,又把目光飘向我,也不问我们要买什么。我们从一楼爬上了二楼,又从二楼爬上了三楼,一个楼层一种气味。三楼卖着布匹,我闻到了棉花的味道。沙武说,进厕所。我说,那是男厕。他说,快点进来。我无奈,看了下四周,没人,我就跟他溜进了男厕。
他把门锁了。我说,你要干什么。
他搂住我的肩,把我推向那扇窗户。我又说,你要干什么。他把窗户拉开,我们两个脑袋就挤在了窗口。他说,凌晨两点,你就在下面等我。他又说,你盯着那个路口,如果没人,你就打三个响指。我打了个响指,问他是不是这样。
他说是。
他问我懂了吗。我说懂。他把我推了出去。他说,你回家吧,一点半从你家出发。我说,我家的钟表走得不准。沙武说,那你就听广播。我说好。我从男厕里走了出来,周围空无一人,我快速下了楼。下楼的时候,差点撞着一对中年夫妇,男人说,臭丫头,没长眼睛吗。我用普通话扭头告诉他,长了,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