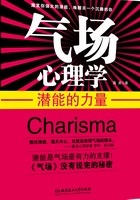阿雪他们在香港开了一家麻将馆,没养孩子,倒是养了几条狗,香港人太老了,床上不行,但手劲还行,经常把阿雪拧得像青花瓷。明海哥,阿雪现在胖得像一只酒瓮子,你见了肯定认不出来,阿标说。阿标说这些话时表情平静,好像在谈论一个与自己全不相干的面团。
阿标说,知道不,小田哥出事了,上星期三刚给双规。小田哥很奇怪,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给我姐写情书,还说我姐是天上的月亮,我阿标是他的小太阳。我姐不理他,我们是近亲啊,开什么玩笑。我姐说他人品不好,我觉得不会啊,他经常买糖果饼干给我吃,从来没跟我要钱。小田哥能干,两年就把县城整得完全变了样,天天有人来参观。小田哥说,谁影响本县一天,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气魄很大,很给田厝湾的人长面子。可小田哥运气不好,实在不好――隔壁村有三个做假烟的,因为怕出事,于是合资三百万,作为活动资金,不想真的出事了,被抓了两个,各判了四年,一天牢也没少坐。出来一问,三百万都用了,经手人是小田哥,大怒,告,告到天上去,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一查,小田哥浑身都是事情,什么低价拍卖土地,什么私挖稀土资源,都有他的份。再一查,他身后竟然也养了一串的女人,其中两个是血亲,一个同辈,一个小一辈,更好玩的是有一个竟然是男的,长得跟我们粉仔一样缘投。
缘投就是好看。
粉仔确实缘投。粉仔才喝两杯啤酒就面如桃花,美得恍惚,迷离。高明海忍不住晃了几下头,他以为自己眼睛出了毛病。
粉仔要报考影视传媒大学,去年考一次了,没考上。粉仔要做大明星,和陈坤、张国荣一样大。粉仔说,他们的片子,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回上省城来,就是想找个好的辅导老师,明海哥见过世面,肯定找得到。粉仔对自己的前途很有信心,粉仔的偶像是张国荣、陈坤和浦巴甲,粉仔有信心超越他们。的确,单从外形上看,粉仔比他们任何一位都更具有观赏性,就是少年时期的梅兰芳也不如他养眼。
粉仔头晕了,想睡。睡哪里?明海说,你和小宝一起睡吧,小宝睡的是双人床。小宝很懂事,吃完饭写了作业自己洗洗就上床看杂书去了。小宝房内开着空调,凉爽宜人,这会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
雨说停就停了,没头没脑的。厅里闷,热,呼吸有点困难。明海起身把窗户全推开了,风扇开到最高档,吹得厅里都是风。几只一次性纸杯不小心就飞到窗外去了,似乎砸到了某只野狗的小腰,楼下传来几声狗吠,好像很不服气。明海提提运动短裤的裤管:“喝,接着喝。”
又几杯啤酒下胃,阿标的话越来越多。
――老家港深水阔,可以停巨型货轮,外商要建世界最大的农药厂,地征光了,连木麻黄也买走了,一家补贴几十万。天上掉馅饼啊,大家都高兴。污染肯定是会有的,不过不要紧啊,受不了可以搬家啊,搬远了,污染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主要是养殖大户,可他们毕竟是少数,再说他们挣钱也没给过大家半个子,平日里脸色也不好,眼睛朝着天净用眼白瞅人,粗声大气,好像钱可以撑死人。倒霉的是对岸岛上的,就隔了几百米,他们靠海过日子,如今城里人都不肯买他们的鱼和虾了,可是,厂子又不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们不高兴也没有用啊。
刚发钱那几天,大伙把桌子拉到街面上,没日没夜地打麻将。以前警察经常下来出成绩,大家在桌面铺好前都会记得顺手把大门闩结实,而且下赌的都是男人。如今不管这些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赌,赌注尽可以下得大一点。嗨,从来没过过如此舒心的日子,打起架来动作也放得开,反正赔得起。
小田哥头脑灵活点子多,决定举办麻将文化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扩大招商引资规模。据小田哥组织的田厝湾麻将文化考查领导小组考证,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船上没啥娱乐设施,船上的将士只能以投掷骰子赌博作为消遣。在长时间的航海中,将士们厌倦了,想家了,甚至有试图谋反的,郑和杀了他们。为了稳定军心,郑和发明了一种娱乐工具。郑和发明的娱乐工具就是麻将,但刚发明出来时不叫麻将,什么都不叫。
第一次玩的是郑和、副帅、大将军和郑和的夫人四个人。郑和是太监,但谁说太监不可以有老婆,过过手瘾嘛,香港人都可以娶阿雪。哦,说岔了。确定了游戏规则后,全船都开始玩这游戏。船上有个姓麻的将军,玩这个得心应手,老赢,于是郑和将这游戏命名为“麻大将军牌”,后来嫌烦,干脆就叫“麻将”。
那时田厝湾的祖上一百零八个叔伯兄弟就在船上,回来后见到我们村那个海湾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就住了下来,发展繁衍,很快变成了一个旺族,旺到不姓田的人家都搬得远远的,后来,这个海湾就改叫田厝湾了。为了缅怀郑和的丰功伟绩,田厝人业余时间经常围在一起打麻将,极大地丰富了业余生活,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麻将文化。
阿标说,要不是小田哥出了事麻将节下个月就开了,我也可以上去露一手。
明海插话:“小田太可惜了,他脑子挺好使的,本来可以做好许多事。”
他说的是真心话。
阿标的兴趣不在小田身上,在麻将。阿标两眼放光,根本就刹不住嘴。
――通常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爱赌,尤其是三人麻将,我可以从日落打到日出,虽然会很累人,不过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再说爱打麻将的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最起码在麻将桌上我们可以暂时把所有的烦恼放在一旁。昨天我就跟朋友聚在一起搓到鸡叫。玩麻将一定要全神贯注地看着麻将牌,重要的是不要把输赢看得很重。在麻将桌上很多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是怎样,他是一个容易不耐烦的人吗?还是一个可以沉住气的人?或者是个输不起的人?这些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在麻将桌上看出来。
阿标说,他和龙尾这次是到省城来进货的,要进一大批的自动麻将桌,准备将全村的麻将桌进行更新换代,提高文明程度,让全村的业余生活再上一个档次,与时俱进。
麻将让明海肚子里的啤酒很反感,一直想冲到外面讨个说法。明海又闻到一股猫屎的臭味了。不行,得转个话题:“田柴板还是校长吗?”
阿标一听,眼睛亮起来:“啊哈,还是还是,过两年才退休呢。县里想调他去当教育局长都不去,他要为家乡的高考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近十来年我们中学的高考成绩非常突出,每年本科上线率几乎都是百分百,上清华北大的年年都有十来个,家长们都很感激。要不是田校长想尽各种办法让大家放开了抄,哪能有如此皆大欢喜的场面!我要不是年纪太大了,真想也去考个全国重点。”
明海问:“难道没人去告吗?”
阿标说,怎么没有!可田校长聪明,在全市大会现场放声大哭,哭得满胸口都是鼻涕,边哭边喊:“嫉妒!嫉妒……”声音都喊哑了,把上级领导也感动了,于是不了了之。
明海想说,去年他们学校就有一个田厝湾的女孩子跳楼自杀了,因为学校为加强管理安了监控,考试不许作弊,作弊被抓到挂科,不许补考,不许补考就拿不到毕业证书。那女孩子读的是数学系,硬梆梆的数学系,一学年下来挂了四科,怎么看镜子里的自己都不顺眼,干脆,爬到中文系宿舍的十一楼楼顶,展开双臂飞了下来,一张脸摔得跟一朵红牡丹没啥两样。明海听到消息飞奔到现场时,孩子的灵魂已经到天上去了。有人看到明海,恍然大悟似的嚷嚷:“高医生,这孩子是你老乡啊!可惜了,水灵灵的。”
明海忍了忍,把话吞进胃里去,和啤酒搅和在一起。
这时,一直埋头喝酒的龙尾眉眼大动,一张黑里泛红的脸活了。龙尾说,田校长管理学校很有一套。他从不处分男生,谁要是调皮捣蛋就会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掏出鸡鸡来,让他掐,轻重由他亲自拿捏,一般原则是犯的错越严重掐得越狠,事后绝不再追究,男生们没有不服气的。龙尾说,有次我砸碎了老师办公室的窗玻璃,还没撒腿跑开就被田柴板一把拎到校长办公室,关上门,叫我脱下裤子,仔细瞅了半天后,手突然一闪就扣住了我的卵泡,狠狠一拧,我当时就疼得晕了过去,后来,肿了一个多月!不过他很讲义气,没有开除我,连记过也没有。
明海腰间一凉,两膝盖下意识地往里一收。他回头望了一眼儿子卧室的门:“田柴板没把粉仔怎样吧?”
阿标、龙尾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了一眼,挤眉弄眼地笑。龙尾刚要张嘴,阿标抬手甩了一下他的大腿,笑嘻嘻的:“田校长对粉仔最好了,怎么会掐他!田校长经常叫粉仔到他办公室里一起午睡,知道粉仔家经济条件不好还给粉仔钱呢,让他买文具和新衣服。粉仔和田校长一样,也喜欢和小男孩一起……”
明海浑身一激灵,头发根根竖起。他跳起来,冲向儿子的卧室,把门撞开了。他跳起时动作过猛,差点把桌子带翻了,害得阿标、龙尾手脚一阵忙乱。
儿子睡得正香呢。儿子窝在粉仔的怀里。
明海的眼睛大了,差点把眼眶胀破。他揪住粉仔的胸口,一把提起来。
明海咬着牙齿;“你摸没摸他?!”
粉仔眼睛大大的,都是眼白。
明海举起拳头:“你摸没摸小宝鸡鸡?!在他睡前摸还是睡后摸?!”
粉仔吓坏了,抖得像片树叶:“在,在他睡后,忍不住,摸了一下,就一下。我再不敢了,不敢了。”
明海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拳头放下了。高明海说,走,你不能在这里睡,你得离开这里。
粉仔进了卫生间,旅行袋也拖了进去。
半小时后,卫生间的门开了,粉仔不见了,出来一个姑娘,吊带短裙,咬了唇红,香肩全裸,胸口雪白。她长发披肩,看得出是假的,但比真的还动人。噢,不,是粉仔,粉仔哭得两眼通红,不敢看明海,低着头双手绞在两腿之间,怯怯地向门口挪去,仿佛一枝乱风拂过的柳条。经过明海身边时,他低眉轻轻一甩长发,香水味把明海的鼻子醉了一下。
见他身姿柔软,明海想都没想就抓过行李袋。急匆匆来到楼下,天,天黑得找不着自己的五个手指头。明海突然发现粉仔住哪里是个问题。小区周围都是大学,大学边上没有旅馆,倒是有许多钟点房,那是专门为大学生服务的。你想啊,现在的大学除了收钱和往学生脑子里灌屎,其它该有的功能一概没有,再不允许他们随便交尾,岂不太不人道了,世界同此凉热,动物如今也讲福利啊。
明海掏出手机来:“你打的回去,到城里去住宾馆!”
找到的士专线的号码,打,占线,再打,还是占线。
空气湿润,明海的呼吸渐渐平缓下来,眼睛也渐渐习惯了黑暗,他看到了几粒星星,看到了一棵大榕树的影子,他看到了粉仔的轮廓。粉仔就在自己身边一步开外,绞手指,脚尖踩着脚尖。明海闻到了一股软绵绵的香味,心忽然一软。
前面围墙边有一盏路灯,孤零零的一盏路灯,灯光软绵绵的,只照亮了一块笸箩大的地方。明海把粉仔带到围墙边,说,你看着行李袋,就站这里,路灯下,别走远,等我。自己穿过黑暗摸到国道边,想试看看能不能拦到过路的士。
国道上车辆稀少,脚都站麻了,还是没拦到。看来,得想别的办法。低着头往回走,边走边在脑子里过电影,电影里都是床铺,干净的能躺人的床铺。
咦,动静不对。气味也不对,一股劣质的白酒味。抬眼一看,两个壮男赤着上身把粉仔挤到了墙上,一个将粉仔的两手掌紧紧压在头顶上,正努着力想用自己的T恤捆住粉仔的双手,另一个蹲下身使了吃奶的力气往下撕扯粉仔的内裤,忙手乱脚的。粉仔两条大腿夹作一条,身子左右扭摆,宛若一尾落网的大鲤鱼,哼哼唧唧。粉仔的裙摆已被剥到了胸口。噢,我的天啊。明海大怒,也不嗻声,咬着牙扑上去揪着一个挥拳就打。
两个壮男很团结,很男人,他们不用板砖,而是一齐转过身来,一个摆开架势和明海对拳,另一个猫腰往前一扑,抱住明海的腿。明海火了,闭上眼随便薅着一个的头发一拳一拳往肉里擀。这时,粉仔清醒过来了,挥起坤包想抽人,不料被抱着明海大腿的壮男回头一吼,吓得尖叫一声闪进了黑里。高明海打啊,打啊,拳头肿了,木了。手里的那袋肌肉终于瘫软下去。明海累了,没心思再对付第二个了,心里说声:“对不住了!”顺手捞起一块木板,把腿上的那位也拍晕了。
左看右望,没有粉仔。撑着膝盖喘了一会儿气后,直起腰,摇摇晃晃的四处找粉仔。半天,没找着。竖起耳朵仔细一听,有虫叫,还有抽抽嗒嗒的声音,踩着声音走进黑里去,果然,粉仔蹲在榕树根头的暗地里哭。一见明海,粉仔长嚎一声扑入他的怀中,紧紧箍住了明海的腰。
明海心一乱,肩膀一松,忍不住搂住。明海轻轻拍着粉仔的背:不怕,不怕,有我在,不怕。粉仔哭着哭着,肩膀渐渐平稳下来。粉仔的头抵在高明海的下巴上,粉仔的头发里有股淡淡的清香,那里头,夹着一丝轻飘飘的海盐味,若有若无。明海忍不住埋下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明海猛然想起了海水声里的木麻黄,想起了木麻黄背后躲躲闪闪的月亮,想起了阿雪。明海心中一惊,赶紧松开双手想推开粉仔,不想被抱得更紧了。明海叹了一口气,搂住粉仔微微颤抖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