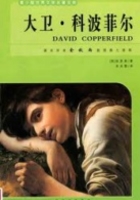我坐在我家门槛上,高音喇叭骑在院门边的苦楝树顶,高音喇叭是个女的,声音又尖又响,讲起话来撞得鼓膜嗡嗡嗡直抖:“……全大队的革命干部社员群众同志们,这趟咱们要昂扬起革命的斗志,坚决彻底地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们住的房子严格讲不能算是我们的家,它是生产队租给我们的,叫队间,它的屋顶耸作人字,黑、高,洞洞一个挨着一个,夜里,我经常坐在厅里一张只剩三条腿的破凳上透过那些洞洞观测天上的星座,效果相当好,真的,方位感特别强。因为我们入住前它叫鸭仔铺,专门用来为生产队孵小鸭,鸭子喜水,所以外面落大雨时屋里噼里啪啦就下中雨。这时,十几束阳光打屋顶扎下来,光斑撒得满地都是,地上怎么看都像铺了一床大花被,黄灿灿的花儿一漾一漾的。
弟弟踩着那些冰得啃脚的光斑跑了出来,他抬头望着树上的喇叭:“割资本主义尾巴?阿兄,资本主义大还是牛大?”
屁大孩子,懂个屁!我才懒得理他呢:“差不多吧。”
弟弟不识趣,唠唠叨叨的:资本主义有尾巴,肯定四条腿,可为什么要割尾巴?没人敢割队里那些牛的尾巴啊!是不是这资什么的做了啥坏事情?
烦死人了!我大了声:“牛犁地,可你见过资本主义犁地吗?!”
弟弟吓了一跳,赶紧飞到院里去,由于动作过于匆忙,差点把晒在日光里的鸡笼踢翻了,惊得鸡笼“咕噜噜”一阵怪叫。
鸡笼里有两只半大的鸡,一只公,一只母。
我才懒得管他呢,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反正他从来不做什么正经事。一个五岁大的毛孩会一边走路一边挥着拳头喊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说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妈妈出门前是交代过,别让他走丢了,我一贯听大人的话,当然会负责任。他会丢了?瞎说,我们家的孩子从来没人迷过路。不信,你喊一声“快来吃——”试试,他不立马飞到你面前我中午就不吃稀饭。
我在等一个人,一个大人,他会一边敲着一片小铜锣一边吊嗓子:“买鸡毛肉骨——”他总是把“骨”拖得长长的,让你听了满口都是水。
他来了,老远就听到他的喊声了:“买鸡毛肉骨——!”
我们都叫他“鸡毛肉骨”,他经常四处乱走,专门收买鸡毛鸭毛肉骨头,或者鸡胗皮废旧牙膏壳。
我赶紧把藏在草垛后边的大簸箕端了出来,好沉!里面满满的都是鸡毛,因为怕盛不下,我把鸡毛全扎成一捆一捆的。
我喊:“哎!鸡毛肉骨!”
他过来了。可他一眼都没看,酒糟鼻子嗅嗅空气就说:“嗯——不要!”
我急了:“不要?!你看,上好的鸡毛!”
他斜了一眼打他身边摇过的月英,说:
“我不买鸡毛!现在遍地是鸡毛!你家有鸭毛吗?有鸡骨鸭骨肉骨吗?”
月英那年十八岁,屁股相当大,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发现,很多大人都喜欢看她的屁股。
“我便宜点卖你行不?”
他不理我,推着自行车就走了,拐过屋角时车后的大竹筐在墙上挂了一下,差点趴在了地上。刚才,月英的屁股就扭到屋角后面去了,连汗酸味也扭过去了。
我生气了!一使劲把簸箕甩进了垃圾堆。
我狠狠踢了两脚苦楝树。苦楝树没什么反应,只不过掉了两片枯叶子,我的脚却疼起来。还能干什么?赶紧到垃圾堆里把簸箕捡回来。奶奶说过了,乱丢东西的是败家子,吃奶屑!虽然奶奶夏天就死了,可我们家的孩子怎么能不听她的话呢!